
在这篇来自《巴黎评论》2008 年春季号的访谈中,新晋诺奖得主石黑一雄讲起他的创作经历。年轻时候未被采用的关于斗鸡眼恋人的广播剧、学生时代对侦探小说和摇滚乐的着迷、在美国公路旅行的疯狂经历……原来,诺奖光环笼罩之下的一代文学大家,也有着与你我相似的养成经历。

(以下内容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八十四期,二○○八年春季号,此处为节选,译者:陶立夏,中文版将很快由 99 读书人出版。)
用精准的英国管家式口吻写就《长日留痕》的作者本人也彬彬有礼。在其位于伦敦戈德格林的寓所门口迎接我之后,他立即表示要为我沏茶,尽管从他在橱柜前面对诸多选择时缺乏决断的样子判断,他并不是在下午四时享用阿萨姆的老茶客。当我第二次到访,茶具已在风格随意的书斋中摆开。他耐心地重新审视生命中那些细节,总是对年少时的自己,尤其是对那个弹着吉他、用支离破碎的断句写大学论文的嬉皮,带着忍俊不禁的包容。“教授们鼓励这么做,”他回忆道,“除了一位非常保守的非洲讲师。但他很有礼貌。他会说,石黑先生,你的文风有点问题。如果你在考试时也这么写,我不得不给你打不及格。”
石黑一雄一九五四年生于长崎,五岁时随家人迁往英格兰南部小城吉尔福德。他有二十九年未曾重回日本。(他说,他的日文“糟透了”。)二十七岁时发表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1982),主要以长崎为背景,获得一致好评。他的第二部小说《浮世画家》(1986)获得了英国著名的惠特布莱德奖。而他的第三部小说《长日留痕》(1986)奠定了他的国际声望。该书在英国的销量超过一百万册,荣获布克奖,并被麦钱特-艾沃里公司拍成了电影,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鲁丝·普罗厄·贾布瓦拉担任编剧。(初期剧本由哈罗德·品特操刀,石黑回忆道,有“许多山珍野味在砧板上切来切去的镜头”。)石黑获得过一枚大英帝国勋章,有段时间,他的画像悬挂于唐宁街十号。他拒绝被神化,下一部小说《无法慰藉》(1995)让读者大为意外,五百多页看来全是意识流。一些困惑的书评人对其口诛笔伐,詹姆斯·伍德写道:“它创造出了专属的糟糕门类。”但其他人则激情澎湃地为之辩护,其中包括安妮塔·布鲁克纳,她消除自己最初的疑虑后,称其“几乎可以肯定是篇杰作”。作为另两部广受好评的作品——《上海孤儿》(2000)和《别让我走》(2005)——的作者,石黑一雄还写过电影和电视剧剧本,他也作词,最近与爵士女歌手史黛西·肯特合作的爵士专辑《早安,幸福》畅销法国。

▲曾与石黑一雄合作的爵士女歌手
史黛西·肯特
石黑与十六岁的女儿内奥米、妻子罗拉一同住在白色泥灰墙的舒适居所内,罗拉曾是一名社工。屋内有三把闪闪发光的电吉他和一套最顶级的音响设备。楼上供石黑写作的小办公室从地板到天花板定制成浅淡的木色,按颜色分类的文件夹整齐堆放在文件架中。他被译成波兰语、意大利语、马来西亚语和其他语种的作品排放在一面墙上。另一面墙上是供研究用的书——例如,托尼·朱特的《战后:1954 年以来的欧洲史》与艾迪斯通· C·内贝尔三世的《更有效地管理酒店》。
——苏珊娜·哈尼维尔,二○○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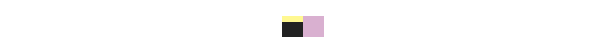
《巴黎评论》:你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很成功——但你年少时期的作品有无未能发表的?
石黑一雄:大学毕业后,我在伦敦西区与无家可归者一同工作时,写过半小时长的广播剧并寄给了 BBC 。剧本虽被枪毙但我得到了鼓励的回复。它的趣味有些糟糕,但却是我第一篇不介意拿来示人的习作。剧本名为《土豆与爱人》。交剧本的时候,我拼错了土豆的复数形式,写成了 potatos 。故事说的是两个在炸鱼薯条店打工的年轻人。他俩的斗鸡眼都很严重,而且两人坠入了爱河,但他们从未捅破彼此都是斗鸡眼的事实。两人对此讳莫如深。故事的结尾,在叙述者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后,他们决定不要结婚。梦中,叙述者看见防波堤上有一家人朝他走来。父母亲是斗鸡眼,孩子们是斗鸡眼,狗也是斗鸡眼,于是他说:行啦,我们不会结婚。
石黑一雄:那时我开始考虑将来的职业。成为音乐家已经无望。我向录音公司 A & R的人约见了好多次。两秒钟后,他们就说:没戏,朋友。所以我想该试一下写广播剧。
后来,几乎在无意之间,我看到一则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在东英吉利大学教授创意写作硕士班的小广告。如今这门课已名闻遐迩,但那时它还是个笑柄,刺目的美国作派。随后我还发现,上一年因为没有足够多的申请人所以并未开班。有人告诉我伊恩·麦克尤恩十年前曾上过这课程。我觉得他是那时候最激动人心的年轻作家。但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能重回校园一年,政府支付全额费用,况且我只需要交一篇三十页的小说。我把广播剧本和申请表一同寄给了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

▲英国作家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
当我被录取时感到些许诧异,因为它突然就成真了。我还以为,那些作家会审查我的作品,过程将令人羞愧难当。有人告诉我在康沃尔某片荒僻之地上有座小屋出租,它曾被用作瘾君子的康复所。我打电话过去说,我需要找个地方住一个月,因为我想自学写作。这就是我在一九七九年那个夏天做的事。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思考短篇故事的构架。我花费数年才想明白诸如视角、如果讲述故事之类的问题。最后我有两个故事可以拿出手,所以感觉底气更足了。
《巴黎评论》:你首次写有关日本的文字是在东英吉利大学那年吗?
石黑一雄:是的。我发现自己一旦无视此刻包围我的这个世界,想象力就会鲜活起来。如果我试图这样开始一个故事:“当我走出坎登镇地铁站进入麦当劳时,遇到了大学时代结识的朋友哈利”,我就想不出接下来该写什么。然而当我写到日本,有些什么会豁然开朗。我给班上同学看的故事中,有一篇以原子弹投放长崎为背景,故事以一个年轻女子的视角讲述。我从同学们那里收获了爆棚的自信心。他们都说:这些关于日本的事实在振奋人心,你前程远大。接着我就收到费伯出版社的来信,将我的三篇作品收录入“推介系列”,销售业绩很不错。我知道汤姆·斯托帕和泰德·休斯就是这样被发现的。
石黑一雄:是的,费伯出版社的罗伯特·麦克拉姆给了我第一笔预付金,我才得以完成此书。我本来已经开始写一个以康沃尔小镇为背景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和她智障的孩子,她的背景暗昧不明。我脑子里一直想着,这女人在两种说法间摇摆:我要为这孩子奉献一切,以及,我已爱上这个男人而孩子是个累赘。我和无家可归者共事时曾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但当我的日本短篇故事在同学那里获得热烈反响之后,我重新审视这个以康沃尔为背景的故事。我意识到,如果以日本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所有看来狭隘琐碎的事物都将激发共鸣。

▲《远山淡影》
《巴黎评论》:五岁之后你就再未回过日本,那你的父母亲又是多典型的日本人呢?
石黑一雄:我母亲是她那一代人中非常典型的日本女性。她讲究特定的礼仪——以今时今日的标准来看属于“女性主义前派”。当我看日本老电影时,发现很多女人的言行举止和我母亲完全一样。传统中,日本女性使用与男性稍许不同的正式语言,现今两者则要混淆得多。当我母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去日本的时候,她说她震惊地发现年轻女孩子在使用男性语言。
投放原子弹时我母亲在长崎。她即将度过少年时代。她家的房子有些扭曲,直到下雨他们才意识到损害程度。屋顶开始四处开裂,就像受到龙卷风袭击。事情发生时,母亲是全家人中——四个孩子与双亲——唯一在投放炸弹时受伤的人。一块飞舞的碎片击中了她。当其余家庭成员去城市其他地方救难时,她独自在家养伤。但她说,当她想起战争,原子弹不是最让她惧怕的东西。她记得躲在她工厂的地下掩体。他们列队站在黑暗中而炸弹就在他们头顶上方落地。他们以为大家都会死。
我父亲不是典型的日本人,因为他在上海长大。他有中式性格:当坏事发生,微笑以对。
石黑一雄:那原本只是场短期旅行。我父亲是个海洋学家,英国国家海洋学院的负责人邀请他前来推广他的一项发明,与风暴时的浪涌运动有关。我从未搞明白那是什么。国家海洋学院创立于冷战时期,弥漫着密不可宣的气息。我父亲加入了那个建在密林中的单位。我只去过那里一次。
石黑一雄:写。我上当地的公立小学,学校正在试验现代教学方法。那是六十年代中期,而我的学校为没有严格界定的课程而洋洋自得。你可以玩手动计算器,也可以用陶土做头奶牛,你还可以写文章。这项目很受欢迎因为它有利于交际。你写上一点,然后阅读彼此的东西,你可以大声读出来。
我虚构了一个叫席涅先生的人物,这是我朋友的童子军团长的名字。我觉得给间谍起这个名字很酷。那时我对福尔摩斯中毒太深。我会模仿着写维多利亚时期的侦探故事,开头当事人会上门然后讲个漫长的故事。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把我们的书装饰成书店里的平装书上——在封面上画弹孔并在背面贴报章的推荐语:“才华横溢,紧张刺激。”——《每日镜报》。
《巴黎评论》:侦探故事之后,下一个让你入迷的是什么?
石黑一雄:摇滚乐。福尔摩斯之后,我停止了阅读,直到二十多岁。但从五岁开始我就弹钢琴。十五岁时开始弹吉他,大约十一岁时开始听流行唱片——非常糟糕的流行唱片。当时觉得它们很棒。我喜欢的第一张专辑是汤姆·琼斯演唱的《家乡的绿草地》。汤姆·琼斯是威尔士人,但《家乡的绿草地》是首牛仔歌曲。他唱的是我从电视上了解到的牛仔世界。
我有台父亲从日本带给我的微型卷盘录音机,我可以从收音机的扬声器直接录音,一种早期的音乐下载方式。我会试图从带噪音的糟糕录音中听出歌词。到我十三岁时,我买了《约翰·韦斯利·哈丁》,我的第一张鲍勃·迪伦唱片,一上市就买了。
石黑一雄:歌词。我当即就知道,鲍勃·迪伦是个伟大的词作者。有两样东西我很有自信,即便是在那时候:什么是好的歌词,什么又是好的牛仔电影。通过迪伦,我想我第一次接触意识流或者说超现实歌词。我还发现了莱昂纳德·科恩,他以文学的方式演绎歌词。他已经发表过两本小说和一些诗集。作为一个犹太人来说,他的意象很具天主教风格。很多的圣徒和圣母。他就像个法国香颂歌手。我喜欢这个想法:音乐家可以全然自给自足。你自己写歌,自己唱,自己编曲。我觉得这很诱人,于是我开始写歌。

▲石黑一雄的偶像,加拿大音乐人莱昂纳德
·
科恩
石黑一雄:我想我曾是,起码表面上是。长发,蓄须,吉他,帆布背包。讽刺的是,我们都觉得自己很独特。我搭车走太平洋沿海公路,穿过洛杉矶、旧金山,以及整个北部加州。
石黑一雄:它大大超过我的预期。有些部分惊心动魄。我搭运货列车从华盛顿穿越爱达荷州去蒙大拿。和我一起的是个明尼苏达州来的家伙,那一晚我们过得像完成特殊使命。那是个污秽不堪的地方。你必须在门口脱光衣服,和那些酒鬼一同进入淋浴间。踮着脚尖经过黑色的水坑,在另一头,他们给你洗过的睡衣,你在铺位上睡觉。第二天早晨,我们和这些老式的无业游民们去货运站。他们和搭车文化毫无关系,这文化几乎全是由中产阶级学生和逃亡者组成。这些人则搭火车旅行,他们浪迹于不同城市的贫民区。他们靠献血维生。他们是酒精中毒者。他们穷困潦倒且疾病缠身,而且他们看起来糟糕透了。他们和浪漫半丁点关系都没有。但他们会提供很多好建议。他们告诉我们,火车行驶过程中不要试图跳车,因为你会丢了性命。如果有人想上你的车厢,尽管把他们扔下去。如果你觉得这会要了他的命,也没关系。他们会想偷你的东西,停车之前你都得和他们困在一起。如果你睡着了,你会仅仅因为身揣五十美金而被抛出车外。
石黑一雄:我一直写日记,类似那种仿凯鲁亚克体。每天我都写下发生了什么:第三十六天。遇到了什么人。我们做了什么。我回家后,拿出这些厚厚的日记,坐下来写了两个片段,深入地写,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一篇写的是关于我在旧金山被偷了吉他。那是我第一次开始留意结构。但我将这种奇怪的翻译腔融入了我的叙事风格,因为我不是美国人,所以它读起来矫揉造作。
《巴黎评论》:似乎你的整个青年时期都有个模式:你盲目崇拜某些东西然后模仿。先是福尔摩斯,接着是莱昂纳德·科恩,然后是凯鲁亚克。
石黑一雄:当你处于青春期,这就是你学习的方式。其实写歌是我喜欢的领域,因为我必须做的不仅仅是模仿。如果我的朋友和我经过某个吉他弹得像鲍勃·迪伦的人,我们会对他不屑一顾。关键是要找到你自己的声音。我的朋友和我很清楚我们都是英国人,我们无法写出原汁原味的美式歌曲。当你说“在路上”,你会想象61号公路,而不是M6。挑战在于,要找到相对应的有说服力的英语。蒙蒙细雨中被困寂寞的路途,但得是在苏格兰边界的灰色环路上,浓雾正漫起,而不是坐着凯迪拉克行驶于美国的传奇公路。
石黑一雄:我在肯特大学学习英语与哲学。我发现相较于那些通过包装婴儿用品将我从皇室家族带往运货列车的年月,大学很无趣。一年后,我决定再休学一年。我去了一个叫兰福瑞的地方,离格拉斯哥不远,其中六个月在居民区担任社区义工。最初抵达时我完全找不到北。我在英格兰南部很典型的中产家庭长大,而那里是苏格兰内陆工业区内成片的破落工厂。这些典型的小居民区,规模都不超过两条街,划分成敌对阵营彼此憎恨。第三代居民和其他被驱逐后突然来到这里的家庭之间关系紧张。那里的政治局势很活跃,但却是货真价实的政治。与学生的政治世界天差地别,这与之后你是否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运动有些相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