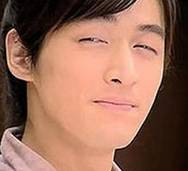主要观点总结
本文介绍了“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视觉艺术项目《虚构的贸易:拒绝以物换物的故事复写》在EKA天物535艺术中心的呈现情况。文章详细描述了展览的内容、艺术形式以及所探讨的主题。特别是两位策展人与嘉宾的对谈,围绕物质性、民族志影像中的视觉议题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此次展览通过多样的形式重审“物”的活力,探索交换过程中物与物质性的变化,并试图构建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新型生态伦理。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展览介绍
介绍了“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视觉艺术项目《虚构的贸易:拒绝以物换物的故事复写》的展览内容、形式及主题。
关键观点2: 策展人与嘉宾对谈
策展人与嘉宾围绕物质性、民族志影像中的视觉议题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涉及物质在交换过程中的意义变迁、形态转化以及主体意图的流动等话题。
关键观点3: 展览意义
此次展览通过多样的形式重审“物”的活力,探索交换过程中物与物质性的变化,复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交流的可能,并试图构建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新型生态伦理。
正文
2024年10月29日至11月17日,“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视觉艺术项目《虚构的贸易:拒绝以物换物的故事复写》在EKA天物535艺术中心呈现。这是青年策展人陈伶俐和吕东昆的首次联合策展,展览从卡尔维诺笔下《看不见的城市》中的贸易之城“欧菲米亚”出发,想象出一场虚构的贸易,他们拒绝以物换物,只交换故事、记忆、音乐与遥远的想象。
本次展览共展出了六位艺术家的十三件作品,媒介涵盖装置、影像、人声、综合材料等,展览通过多样的形式重审“物”的活力,探索交换过程中物与物质性的变化,复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交流的可能。
围绕“变形”与“交流”的主题,两位策展人邀请多位嘉宾分别于11月2日与11月16日展开对谈。第一场对谈聚焦物质性,策展人特别邀请青年艺术家徐子奕分享其作品《化石宴》及作品背后的创作思路。第二场对谈聚焦民族志影像中的视觉议题,参展艺术家毛晨雨、学者张晖,纪录片研究者谭植元共同探讨了民族志中的拍摄伦理,及影像的能动性问题。
通过展览与对谈,策展人和嘉宾从不同研究视角与创作实践出发,拓展了贸易所蕴含的博物志与民族志空间,并试图构建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新型生态伦理。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可能:
变形,间主体性,与未来物种
11月2日下午,策展人吕东昆、陈伶俐与艺术家徐子奕围绕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创作视角展开对谈。对谈从具体作品出发,聚焦物质的变化,延展出对超越人类生命形态的思考。
对谈从徐子奕的作品《化石宴》出发。艺术家介绍称,他的创作灵感源于化石标本的采集过程。作为化石爱好者,他发现化石只能呈现古生物的部分信息,大部分信息都不可及,古生物原有的色彩、气味及生命状态因时间流逝而消逝,形成了一种叙事上的缺失。因此,他选择将化石做成菜肴,用烹饪的方式还原出菊石、马来鳄、海胆、珊瑚等化石的生命样态,试图重构出一种能触发联想的感官语境。
本次群展特别聚焦于物质在交换过程中的意义变迁、形态转化,以及主体意图的流动。吕东昆指出,挖掘化石的过程是一种身体性体验,这种体验与蒂姆·英格尔德(Tim Ingold)的“材料对抗物质性”(material against materiality)理论相呼应,即人类与物的互动并非将主观意识强加于物质,而是通过接触感受到物质内在的变化,使自身融入材料的海洋。这种人与物的流动关系或许正是徐子奕在化石中感受到的独特体验。
“变形”是本次群展的关键词之一。陈伶俐提出,徐子奕的创作呼应了“变形”一词,由化石变为菜肴再变为观众参与的艺术,构成了一次直观的变形过程。徐子奕表示,“变形”不仅指形态的变化,也是感知关系的变化。从生物有机物到化石无机物,再到可被食用、吸收的有机物,人类感知在这一过程中重新与物质建立起连接。他希望在理性推导之外找到一种更具感官维度的复原方式,从而在变形的过程中理解物质的内涵。
通过此次对谈,策展人与艺术家讨论了艺术创作中人与物质、时间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品引导观众从不同时间维度和物质属性出发,重新审视人类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激发对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层思考。
11月16日下午,策展人吕东昆、陈伶俐,与参展艺术家毛晨雨、民族志影像学者张晖、纪录片研究者谭植元,围绕纪录片民族志的拍摄伦理及影像的能动性展开对谈。借由人类学家唐·库里克(Don Kulick)的文章以及艺术家程新皓的两件展览作品作为切入点,五位嘉宾深入探讨了影像所包含的视觉议题,以及镜头内外不同主体建立交流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