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31日,浙江大学第十七期“紫领·问政讲堂”特邀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原巴东县委书记、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兼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陈行甲老师,与大家共话了“公益的力量”
。
陈行甲
(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兼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陈行甲,清华大学管理学硕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历任湖北省兴山县水月寺镇镇长、兴山县委常委、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宜昌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宜都市人民政府市长、巴东县委书记。2015年6月,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2016年1月16日,在巴东创造的精准扶贫经验被央视《新闻联播》以六分零三秒的时长推介。2016年6月30日,在巴东创造的农民办事不出村和农村信息赶集的乡村治理经验被庆祝建党95周年专题片《筑梦路上》专题推介。个人文章曾四次登上人民日报。
2016年底,在县委书记任职届满之后辞去公职,专职从事公益。2017年2月来到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任研究员,2017年5月创立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2017年6月起兼任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和中国传奇公益人物刘正琛联合发起联爱工程,通过“儿童癌症综合控制”公益社会实践,探索因病致贫这个社会问题的规律性解决办法。

以下是陈行甲老师的演讲全文,文章有点长,但爱的力量延续的更绵长。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感谢阮老师和忻皓的邀请,让我来浙大的紫领问政讲堂演讲。这是第
17
期。我查了一下前十六期的演讲嘉宾阵容,吓了一跳,里面有老省长、现任厅长、大企业家、大学者,让我这个后来者很有压力。稍感庆幸的是,上这个讲堂的公益人,我是第一个。我希望我能讲得有点不同,让大家有一点启发。
我曾经是一个官员,是一个自认为合格的官员。这个衡量的标准,一是我服务过的老百姓绝大多数对我的认可,曾有朋友说互联网上老百姓对我那么多一边倒的匿名评价,是许多人花钱雇水军都买不到的效果;二是党曾经给我的巨大荣誉。人民群众认可,党认可,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人生上半场的行政生涯是成功的。
我人生下半场选择辞职从事公益,当时曾经引起过一些猜测和讨论。其实没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现在,我可以轻松快乐地跟大家说,那只不过是我的青春记忆的一次复苏而已。
今天面对同学们青春的面庞,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过往人生中三次难忘的成长体验。希望我的这些体验能对你们未来的人生选择有所裨益。
曾经看到过这么一句话,
如果一个人足够幸运的话,其一生中会有三次成长。
第一次,是发现世界不以自己为中心;第二次,是发现有些事自己无能为力;第三次,是明知道无能为力还去做。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这三次成长的故事。
第一次成长的体验
走出自我,对我来说是来得比较早的
我在农村出生长大,从小跟着妈妈一双脚板山里来山里去。妈妈是我的人生中第一个导师,也是最重要的导师。妈妈只念过两年书,没给我讲过什么深刻的道理,但是她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我。
童年记忆中我们家门外的阶坎是过路的背脚夫必须要歇靠的地方。一是我们家门外总是扫得干干净净的,二是每个背脚夫都会在我家讨到水喝。我们那个村子很偏远,很穷。
村子里有一户很特殊的人家,男主人姓潘,我叫潘伯伯,女主人姓王,我叫王伯娘,他们家有七个孩子。记忆中潘伯伯一家在村子里不受人待见。潘伯伯常年佝偻着腰,拿着个烟袋,走到哪咳到哪,吐到哪;王伯娘似乎永远没梳过头,总是蓬头垢面,因为潘伯伯动不动打她,她总爱哭,眼里总有眼屎。就是这家人,经常会到我家借盐吃。我很少看到他们还过。大抵因为面子的缘故,他们时常换不同的孩子来借。
但是,我妈妈从来没让他们空手回去过。少不更事的我曾经问过妈妈,他们总说借,总不还,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借?还记得当时妈妈拉下脸呵斥我:
人不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怎么会借盐吃?我们不给他们借,他们就没地方借了,以后不准你说这种话!
还有一次,夜晚妈妈给我洗完脚,准备招呼我睡了。这时窗外传来断断续续的哭泣声,打开门一看,是王伯娘。原来是她家三女子有媒人上门提亲了,可是没有一件穿得出去的衣服。王伯娘大致也是无路可走了,又到唯一的求救处来哭泣。
那一晚,我亲眼看见妈妈把她出嫁时穿的白色带暗红格子的确良衣服,送给了三女子。从我童年到少年的过程中,我亲眼见到或者听到潘伯伯家老少一个一个死去,到最后只剩下大儿子一人,坐牢回来继续在村里生活着。他们家多数是病死的,也有到外地卖血感染艾滋病死的,还有在外地做小偷被人追到地里打死的,比余华的《活着》讲述的徐福贵一家人还要特别。他们家因为太穷,葬礼都很寒酸。记得童年的一个清晨,得知王伯娘夜里去世了,我远远地看见妈妈赶过去帮助料理王伯娘的遗体时痛哭失声。回想起来,我妈妈虽然也穷,但是她就像村里的菩萨,悲天悯人。她在用她不大的力量,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比她更弱的人活着的尊严。
童年和妈妈在一起的生活,虽然穷,但是我们不缺少人世间最宝贵的东西——爱。爱是人世间最具发散性的物质,不以自己为中心,体恤他人的感受,才是爱的本质。
妈妈亲切的笑容,温暖得可以融化冰雪,是我人生力量的源泉。妈妈离开多年,我辗转过很多地方,但是无论我走到哪里,一直带着妈妈的遗像,在她的笑容中感念她留在世间的温暖。
妈妈给我的爱,给比她更弱的人的爱,像一颗种子深埋在儿子的心底。
童年和家人在一起
在我前半场的人生中,无论是求学生涯还是工作经历中,与人为善,愿意为他人着想,是我周围的人给我的标签。大学时曾有一个平时交往并不多的隔壁寝室同学,毕业前大家一起聊天时说:
如果将来我临终前有一件放心不下的事要托付一个人,我托付给陈行甲。
我至今
把他的那句话记着,视为我的一个极高的荣誉。
我后来当了官,妈妈留在我心底的种子慢慢地生根发芽,开枝散叶,让我怀着和妈妈一样的悲悯态度来对待弱者,让我耻于在穷困的土地上锦衣玉食从而坚守干净的从政底线。
我曾经做过五年多县委书记。有人说县委书记是中国权力最实的官。我在这个平台上,以我服务的老百姓为中心痛痛快快地做了一些事情。面对当地曾经浑浊的政治生态,我借党中央强力反腐的东风,下重手扭转风气。曾经一年多时间里,我亲自签字或者亲自部署抓捕的工程老板和官员就达
87
人;为了逼着官员眼睛朝下,我打造了一个创新的平台,让全县老百姓公开评价干部;在那个几乎全省最穷最边远的山区县,顶着大家不看好,甚至时任县长都不支持的压力,通过信息化实现了农民办事不出村,办起了农村信息赶集;为了省钱并考虑宣传效果给当地旅游代言,我亲自出镜唱歌录
MV
,手持旅游宣传旗帜直播
3000
米高空跳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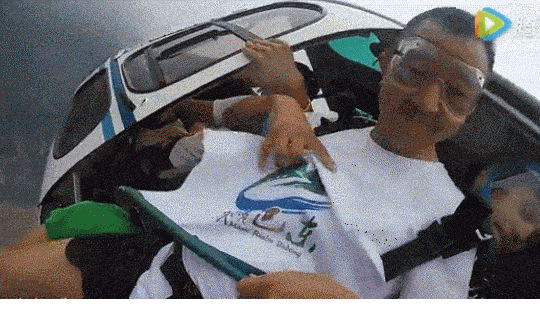
陈行甲巴东3000米跳伞
虽然我为官时的“特立独行”曾带来一些质疑和掣肘,个别我的主要领导坚定地认为我是在出风头搏政治前途,但是我不以为意。只要不违背组织原则,我会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别人怎么看不是我考虑的重点。
任职期满后我被省委提拔公示了,但是我最终决定辞职从事公益。在这里我也想澄清一下,我辞官从善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从政有什么不好。从政在中国文化中一直都是主流的效率最高的为民服务的方式之一,现在也是如此。很多我非常敬佩的人都在各级岗位上从政为民,他们的奉献值得尊敬。只不过那个时间点上,综合我的处境、我的理想,以及时代提供的机会,我认真思考后认定辞职从善对我来说是一种更好的人生选择。
在外人眼中,我放弃明显的仕途前景,一定经历了内心的波澜壮阔。其实对我来说只不过是顺水行舟而已。以前我说想为老百姓做些事,没想当大官,那些人说我是在装。现在,我用行动证明,一个不以自己为中心的人,功名利禄真的没那么重要。他可以听从自己的内心,只分对错、不论输赢。有些时候,生活的逻辑是你越是不论输赢,你赢的概率反而越大。
我不当官了并不是输了。我赢得了内心,赢得了尊严,赢得了在公益领域继续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机会,这是更大的赢。
我辞职后网上曾出现很多写我的让人动容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前途多艰,甲哥保重》,文章最后一句话就是:“单就老百姓都喜欢他这一点,他已经赢了!”。

和百姓在一起
第二次成长
转场公益的最初,面对几乎远在天边的理想,那种深深的无力感
我在决定转场公益之时,理想就是做这个时代的晏阳初,去做乡村平民教育,我甚至在给当时省委主要领导的辞职信中附上了我的晏阳初计划。但是,就在我辞职后的第二天,爆发了一个全国热点——罗尔事件。以前在我工作的县里发生的好几起儿童白血病导致倾家荡产的例子曾触痛过我,罗尔事件让我更深更细地关注到这个社会痛点。
上网深翻,发现早在
2011
年
3
月
4
日,当时的国家卫生部就曾表态从当年起全国的急性儿童白血病要推行免费治疗,可是罗尔事件表明这个政策并没有落实。这激起了我的热情,我想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儿童白血病免费治疗这件事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否则当时的国家卫生部不会表态;二是这件事很难,否则不会这么多年没落实。再深入研究发现,这件事难就难在底数不清、路径不明。
所以,我反复考虑之后决定先搁置我的晏阳初计划,这个可以留到以后再做,我先着手从公益的角度来尝试为推动儿童白血病免费治疗探底、探路。
开始之后才发现这谈何容易!可以说,当初的我除了理想和热忱,几乎一无所有。一是没有一丁点儿白血病专业医学知识,二是没有任何公益从业经验,三是没有钱。我和家人讨论想法,和他们一起画树状图分析该怎么做。他们客气地听着,也从价值观方向的角度说几句鼓励的话。但是,不光是他们都不看好,我有那么一刻也在反思自己是不是想蹬着自行车上月球,太自不量力了。
一开始去拜访自认为潜在的资助人的时候,也吃过闭门羹或变相的逐客令。有时联系曾经对我很亲热的朋友,要么微信不回复,要么回复时那种疏远和冷淡隔着屏幕都能让你感觉到;有时我充满热情地给介绍我的想法,得到的却是慵懒的呵欠或者刻意转走话题的尴尬。不止一次,从别人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脚步比进去的时候沉重很多。最初的几个月,时常伴随着深深的无力感。那个时候经常在内心里跟自己说,要象曾国藩说的那样打碎牙齿和血吞,使笨力气坚持住。
第三次成长
明知道无能为力,还是决定去做
彼得圣吉老师曾经对我的激励在那个阶段成了我精神上的支撑。
如果看清了方向,就坚定地往前走吧,让未来那个更好的自己,在途中遇到你。
我自己觉得,这个方向我是看清楚了的。就像远在天边的微弱星光,但是我确定那微弱的光亮不是幻觉,是真实的,它在召唤着我。哪怕脚下的路漆黑一片,看不清楚,我也决定迈开步子向那个光的方向走去。我们面对不确定性时,通常选择“因为看见,所以相信”,这一次,我选择“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当所有的客观力量都暂时没有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力量,那就是信念的力量。
我开始埋头学习,搜索一切相关的知识点,在电脑前一遍一遍地写项目计划书到深夜;我开始彻底打开天线雷达,扫描我的新旧朋友圈,寻找可能的链接点;我继续跟所有我觉得可能对此有兴趣的人讲述我的理想,寻找可能的支持……
很快,柳暗花明又一村,奇迹一个一个出现。在跟好朋友一诺深聊时,一诺告诉我,国内做白血病救助公益做得最好的传奇公益人物刘正琛,是她的公众号奴隶社会的作者——
正琛因病成医,因病从善,是疾病救助的专业大神和公益慈善的精神标杆,她现场拉群,介绍我们认识。
我和正琛在第一次通话后决定要合作,第一次见面后就决定要深度合作,合作两个月后他就决定让出理事长的职位邀请我和他一起给我们的团队领头;
在和一个大爱大情怀的企业家深聊时,他慷慨地表态拿出一千万来支持我起步,而且不要任何名分的回报;在和深圳文科园林创始人从文爬山深聊时,意外地直接链接上公益实验意向地点河源的主要领导,并很快取得他的认可和支持;在偶然得到拜见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老前辈的机会时,半小时的汇报后侯总现场表态,中兴通讯深度支持我的公益探索;在向国家权威医保专家郑功成教授汇报后,得到他的热情鼓励和加持;上门拜访北大公卫学院、复旦公卫学院、山大医药卫生管理学院领导,得到他们热情欢迎进而深度合作;在广泛的扫描中,又拉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健康研究所研究员陈秋霖、美国诺华制药著名青年科学家李治中这两个超级专业大牛做公益合伙人……
有了这些基础,我们一起尝试在广东省河源市开始儿童白血病的综合试点。河源市的各级领导非常欢迎我们,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
第一步,我们为社保基金提供支持,将儿童白血病的医保目录内报销比例增加到
90%
,这个工作从
2017
年8月
15
日启动,到现在已经面向
54
个河源地区的儿童白血病患者展开了服务。第二步是邀请两个国家卫计委重点实验室,对这个公益医保补充基金政策和临床已在广泛使用但不在医保报销目录内的新药做
“
医疗技术评估
”
,本月已经完成了基础的评估工作。第三步是邀请医保的决策部门来审核我们委托做出来的医疗技术评估报告,预计将在
2018
年
6
月底完成。通过这样的流程,我们希望医保的决策部门可以逐步委托独立第三方来做医疗技术评估报告,从客观中立的角度来评估药物,以合理的价格纳入医保。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对医生的支持,帮助河源消灭儿童白血病治疗能力的空白,帮助他们建立儿童血液科,并启动了对河源当地医生的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