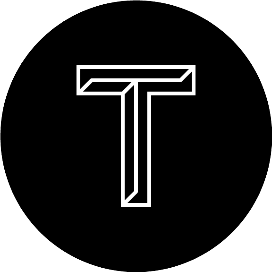如何客观地评价一部电影?票房、专业影评和电影节「战绩」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一部电影的口碑。这其中,电影节
(Film Festival)
或许
最能体现「为电影而来」者的综合意志,它的人造属性也恰巧应证了电影节的本意:一个属于电影的节日。
为扩大声量,每一个电影节都在不断强调自身的属性 ——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注重艺术性,柏林国际电影节偏爱先锋意识及政治表达,戛纳国际电影节则看重现实价值。当然,这其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刻板印象,但正如刻板印象的产生是基于一种持续的输出,这样的属性分类,也恰好印证了它们的耐久度:每年都不会缺席。
无论如何,电影节离不开让人「看到」电影,失去观看的权利,也就失去了荣誉的意义。伴随媒介形态的转换,「观影体验」正成为不同电影节主办方的共同课题 —— 用什么方式,在什么空间看电影,电影才「最好看」?疫情过后,海内外规模不一的电影节纷纷对这一命题提交答卷,运作两年的海浪电影周也在其中。
9 月 6 日傍晚,2024 海浪电影周的露天放映场之一 —— 酒神剧场 —— 中,一块巨大的银幕亮起,产业单元「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短片首映礼在此启动,为期不足一个月的极限创作即将开出盲盒。然而,前排手机屏幕的光线,招呼迟到友人的起落身影,自下而上的烟缕和赶来制止的保安,又让这种揭晓前的兴奋多了几分躁动,或者说,「人气」。
海浪电影周首席执行官李穗此刻也在观众席中,但他并不想拿起红外线笔维持所谓的观影秩序。生活本就不输银幕热闹,眼前的景象恰恰构成了海浪电影周的重要注脚。
第一部亮相的短片《大寒》改编自短篇小说《经济型越冬计划》,导演李玥正蹲守在放映室旁,为未能到场的摄影师直播现场情况。北京电影学院出身的她曾格外注重放映过程中的技术标准和作业流程,在意每一帧色彩和声音的呈现度。但如今被问及希望自己的影片在哪里放映时,她给出了和从前截然不同的答案,「大家看电影的时候还是应该松弛一点。」
改变来自几年前。她携短片作品《清明梦》前往芬兰参加电影节。试想,在坦佩雷的街头咖啡馆,一位路人恰巧经过,被银幕上的东方面孔吸引,最终愉快地看完剩余片段 —— 即使他并非迷影,来此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观影,但身为导演的李玥仍为这样的相遇感到开心:「我认为『一个人路过,想看两眼电影』这件事情非常珍贵,大家不必过于紧张。」

这和李穗的观点不谋而合。海浪电影周创立之初,他就明确要做一个「去电影化」的电影节,「户外放映」的设想也起源于那一阶段。
哪个阶段?是观影方式便利化,影院硬件配置丰富化的阶段,是人们意识到观影本身也事关体验感的阶段
。一言以蔽之,「看电影」不难,难的是「开始」看一部电影 —— 无数次打开流媒体平台,手指快速向下翻动,浏览见底却也找不到任何观看的欲望 —— 这在李穗看来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在影像资源并不稀缺的当下,重要的不只是影片本身,而是作为整体的观看体验。」策展人一舒说。作为本届海浪电影周放映片单的展映团队「趣放」的联合创立人,她喜欢更因地制宜的策划。在她看来,海浪电影周独特的落地环境是它区别于其他电影节展的重要因素,它无需背负「评奖式挖掘」的使命感,而是重新强调了「观看即体验」。
于是有了泳池皮划艇上的《爱乐之城》,空旷草坪上的午夜恐怖片,被荧光棒点亮的《马戏之王》合唱现场 ——「在一个严肃的电影节,你很难轻松愉快地放这些片子,因为没有由头。」一舒说。
此前在海外策展时,格拉斯电影节艺术总监的一句话让一舒印象深刻,「希望大家在此尽情享受电影的乐趣。」
(We are a festival not afraid to have fun.)
海浪电影周的策略同样如此,「好看」作为李穗明确下达的指示,被策展团队贯穿始终 —— 并非小众的迷影狂欢,而是每一个普通观众汇聚的快乐。
观影通票玩法是相较于去年的最大调整。手揣门票进场,你便进入了海浪电影乐园,边走边看,仿佛回到了只能线下购票的年代。李穗认为,看电影本该如此:不带目的地漫步至影院,不必掐算沿途距离或是提前查阅影片口碑,人们有大把时间逗留在售票处,直到慢悠悠地看完所有预告再做决定,饿了就先去吃饭,反正电影随时都有。
没有抢到票也无需遗憾,海边银幕为所有人敞开。观影区域外,从沙滩沿岸到餐厅露台 —— 凡可落脚处皆为临时观众席。《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放映吸引了许多路人的注意,出于对售票规则的尊重,李穗克制住了自己多次想给场外观众散发 3D 眼镜的冲动。人们像回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围坐在邻居院子里观看集体电影的夜晚 —— 电影不再被追逐,而是你我并肩而坐的理由。
「毕竟没有人看到海边的巨型银幕不会停下脚步,对吧?」身着印制海浪电影周官方图案 T 恤的李穗笑着望向驻足沙滩沿岸的观众。一天中,他最喜欢海边傍晚,等待天光渐暗,银幕亮起的时刻。幕与天渐渐融合,商铺也一一配合着关闭灯光。三,二,一,天黑了,请睁眼。

时间倒退 24 小时,一天前的酒神剧场,海浪电影周的荣誉单元放映略显冷清。有意空缺的故事背景、循环往复的时间线、绵长固定的镜头、冷漠疏离的表演,这些常规观影经验以外的元素挑战着观众有限的注意力。放映中途,陆续离场了几波人 。
不同于院线大片动辄上亿的票房收益,艺术电影有时只能以近乎一对一的方式收获观众,两极之中,许多创作者正在寻找作品和观众间的桥梁。「会有观众跟我说他们看不懂。」导演朱云逸说,带着一丝腼腆。他的短片《另一面镜子里的梦中之梦》从国际 A 类奖项来到海浪电影周,影像上延续了他的前作风格 —— 实验、诗意、非线形、反叙事。
「但正因为不理解,我们才需要沟通。
」朱云逸补充道。艺术最吸引他的正是其中的差异性和多义性,人们能够通过这扇窗看到不同个体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他对国内艺术短片放映空间之狭窄感到遗憾,不过依然庆幸有海浪电影周作为补充。

举办产业酒会的餐厅离沙滩很近,酒精、爵士乐还有松软的沙发聚合起电影人及泛文化同行,单读市场总监彭倩媛从酒会中跻身室外,「我觉得作品就是得拍给观众看的,如果不考虑观众和市场,这个链条就不太通。
」2020 年冬季,她与李穗联合了发起「文学实验室」,面向华语文学,广泛征集兼具影视改编可能与视觉想象空间的文学文本。
4 年前,李穗还在其他电影节任职。他观察到,创投中的提案类型逐渐趋同,仿佛只能书写「悬疑」「爱情」「家庭」「犯罪」等三两热门标签内的故事。僧多粥少的行业现状让创作者产生了时不我与的紧迫感,原本有限的生活经验被压榨干瘪之后,部分年轻创作者只好将目光投向了对电影本体的探讨 —— 某年创投涌入的大量元电影叙事引起了李穗的反思,他知道,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有作品的地方,并不一定会有观众。泛滥的元电影内容很容易遮蔽创作者单一的生活经验、贫瘠的想象和自恋的表达。让对话发生的前提是先走出圈内人自说自话的热闹。「目前大部分编剧都缺少对不同真实生活的感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引入了小说的视野。」李穗谈起「从文学到电影」的设立初衷。
文学为不断「盐碱化」的电影创作圈地注入活水,源源不断的灵感在此滋生。72 本小说由 9 家出版社筛选、推荐,经理事单位共同讨论后,剩下的 16 部文学作品被青年导演又一轮挑选、提案,最终剩下 6 部,与 6 位导演一一匹配,进行改编。市场的倾向性在这场漫长接力中被核验、传递,真正的终点线设在观众席。

「我们推荐的书目中有格非的《隐身衣》、阿乙的《骗子来到南方》,还有非常年轻的《出山》—— 这些都来自不同年龄段和生活经历的作品。」李穗谈及几部风格迥异的文学推介小说,并惊喜于青年导演基于细微的生活洞察的再创作。《鱼骨寺》导演崔晓东与观众分享了他选择改编作家叶昕昀短篇小说《午后风平浪静》的原因。故事里,女主角长年饱受丈夫「呼噜」的折磨,而现实中,他也常被深夜吵架的邻居夫妻打扰,整夜无法好眠。由「失眠」走上「犯罪」听起来无稽,但在另一个失眠者镜头的解释之下,「呼噜」也能成为令观众共情的创作锚点。
「主创和演员就是第一波观众。」剧本围读阶段,李玥带着主创团队反复讨论剧本和改编方案。短篇小说《经济型越冬计划》的灵感源于作家沈大成在巴萨罗那圣保罗医院的观光经历,她评价自己的小说「不太有中国感」。想把这个故事影视化,需要导演完成不少诸如选景、台词及人物行为动机等「转译」工作。

某些语境下,电影会被定义为一门独裁的艺术。以文艺片见长的李玥也曾因晦涩的叙事习惯受到观众的质疑和挑战,她直言自己会关注豆瓣评论,在复盘中调整下一次的表达策略。科幻小说改编难度不小,为了让观众更好地进入剧情,李玥主动尝试了类型化改编,「这也是我制作这部影片最大的进步。」《大寒》中的山洞奇观、仿生人妆造、发光的床以及男主区别于原著的「警察」身份,让观众看得入迷 —— 李玥欣喜,故事打动了她以外的更多人。
当晚放映结束后,场内灯光准时熄灭。观众久久不舍离场,把主创围堵在路中央,攀谈、合影。「麻烦把面光打开一下。」人群中,李穗冲远处的放映室喊道。追光快速跟了上来,夜晚再一次被照亮。从业多年后,李穗很难再以单纯的旁观心态看待电影节,但这样的瞬间,仍让他感到幸福。
剧场的热闹蔓延至社区街道,装潢着大幅落地窗的街角商店内,半藏式的灯管和邻街构成的画面,
仿佛 Edward Hopper 的《夜鹰
》,一幅灵感来源于小说的画作。「电影就像门上的铃铛,每一次开关门发出的愉快声响都在提醒着你,它一直在。」李穗希望所有路过这里的人都能明白:电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推开商店的门,铃铛声清脆,「欢迎光临,随意挑选。」物质资源愈发丰富的时代让渡给观众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无论商品,还是电影。此时,沙滩上的两块屏幕正分别放映着《完美的日子》和《爱乐之城》,场地「午夜绿洲」则上映着动画片《魔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