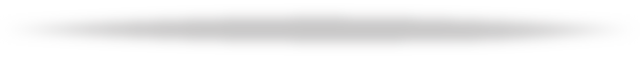
财富的传播者,
一
路同行,一起成长


数据揭示的秘密就是:
在病毒携带者中,大部分人(超过60%)毫无症状,根本不知道自己曾经感染过这个病毒。25%的人症状很轻,基本能够自愈
。
病毒的致命性不高,大约为流感的2倍;但是病毒传染性高,短期内医疗资源的挤兑效应明显。因此最最关键的,还是严防死守(60%无症状!),最好隔离和防护!
各国从武汉撤侨后,均进行了最严格的全面检查。
这些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也是最详细的、最完整的,具有很高的参考性。
新加坡、韩国、日本、德国共撤侨1149人,查出16人感染病毒,比例高达1.39%。
如果只是一个国家的侨民如此,那还可能是聚集性或偶发性病例,但东西方多个不同国家侨民的被感染比例都差不多,这就相当程度能说明问题了。
其中撤侨人数最多的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报告。
第一批包机1月29日,206人中8人咳嗽和发烧。但第1次检测均显示阴性;第2次检测测出3人阳性,但只有1人有明显症状(入院时体温37.9℃,后上升到38.7℃),2人无症状。
还有1位侨民,26日在武汉出现咳嗽,抵达时低烧(37℃以下),前2次检测均显示阴性,第3次才检测出病毒阳性。但此时症状已迅速改善。到2月1日,仍然有一点咳嗽,但发热已不明显。
总共是1人较明显症状、1人轻症、2人无症状。
第二批包机1月30日,210人中13人咳嗽和发烧,但测试显示这13个人均为阴性。
而在此之外的无症状群体中,反而有2人经检测确诊阳性,但均无明显症状;
第三批包机1月31日,149人中10人咳嗽和发烧,但其中只有1人确诊,为轻症(中等程度发烧,38℃以下),另有1人无症状,却被测出携带。
也就是说,目前日本总共撤侨565人,有咳嗽发烧症状31人(比例约5.5%),其中只有3人测出携带病毒(比例约10%)。但在此之外,却另有5人无症状却携带病毒。
共计确诊病毒携带者8人,5人无症状、2人轻症(1人低烧37℃以下并自愈、1人中度发烧38℃以下)、1人有较明显症状(38℃以上)。
这些数据都证明,病毒感染的比例比学者们最大的想象还要高。
只是统计的标准不同。
在病毒携带者中,大部分人(超过60%)毫无症状,根本不知道自己曾经感染过这个病毒。25%的人症状很轻,基本能够自愈。
只有约15%的人病情较重(体温超过38℃)。
另外,国内也报道了多起连续3、4次检测,才发现病毒存在的案例。
目前来看,日本对撤侨侨民的检验,是检核最全面的样本。
按流行病学的统计推算,每10万武汉流出人口中,无症、轻症、明显症状的人数分别是885人、354人和177人。
当然,用小样本数据去反推大样本,会有一定偏差。
但以千人规模的样本出发,已经不会出现量级上的颠覆。
再参考检验较为严格的国内、省外各地区,可以推算出每10万武汉流出人口中,重症、病亡的人数分别为31人、0.6人(仍在发展,预计会有所增加)。
以此回推到目前900万在城人口的武汉,
可以估测,携带病毒、且有明显症状需要治疗的人数在1.5万人左右,其中重症人数应在3000人左右。
但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巨大人口组成的复杂系统,特别是在人口大国、在特大城市,1/8000的比例乘以巨大的基数,就会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美国年平均死亡4万人,流感高峰年死亡6万人。一座1000万人的城市,平年死亡1200人,高峰年可能会达到1800人。
这就是公共卫生统计与个人视角的重大差别。
毕竟,武汉是一座人口数量超过希腊、葡萄牙、捷克、瑞典、匈牙利全国人口的千万人口特大城市。而一个人的日常亲友交往圈只有100~300人,但互联网则能极大地放大这一点。
公共卫生主要是关注群体的预防,临床医生和普通人主要关注的是个体的治疗。
公共卫生的视角是群体,临床医生的视角是个体;公共卫生不可脱离临床,临床也不可脱离公共卫生。
衡量病原体的危害,包括传染性(Infectivity)、严重性(Severity)和致命性(Lethality)这几个维度。
从各方学者主流接受的传染性来看,nCoV的传染数RO是2.6~2.8之间,比flu的6要低。
被感染人数、控制难度也相对低于flu。在当下巨大的人力物力努力之下,疫情总体上的确也做到了“可防可控”。
从严重性来看,nCoV从携带病毒到需要住院的比例在15%左右,从表现病情到需要住院,更是达到了约40%。
而flu在实践中只有1.6%(多为老人)。nCoV明显高于flu,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流感完全无感,而对nCoV感到恐慌的原因。
但从致命性来看,flu从病情发作到最终去世,比例达到了1/900;
nCoV从病情表现到最终去世,目前外省比例是1/530,未来随着病程会有所增长,但预计不会超过1/400。nCoV的致命性实际仅是flu的2倍,当然两者都很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