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人间乐园》局部,ca. 1495-1505
在讨论到伊斯兰的普世精神和普罗精神章节,霍奇森提到
萨珊帝国
中的马兹达教徒是如何在帝国的支持下铸建一套整体性的个人与社会生活规范。霍奇森指出,波斯教士这套规范跟犹太教是同理的,二者的基础就是一套关于
“洁净与不洁净的观念”
,以及随之而来的“神圣化的社会分层制度”。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观察。洁净与不洁净,我们远在
希腊诗圣Hesiod的长诗《劳作与时日》
后半段就见识过了,啰里啰唆一大堆,一言以蔽之就是幼儿园老师教导幼童那套关于常洗手的必要废话,背后是对
一个不洁净的世界
的警惕以及对一个洁净世界的确认。
这就是
二元论
认知图景
,幼儿园小盆友都掌握了的。这个二元论图景是健康的终极保证,也是健康思考的起点。之后如果出现不洁净、混乱、腐败、大灾役等等,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差不多都会追溯到一个被破坏的二元图景这个原因上来,这就是圣奥古斯丁所警惕的
“致命的混合”
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是最致命的混合?当然非一元论莫属,一性论、泛神论、万物有灵论、唯物质论等等都是这种东西,其政治对应物就是大一统,我送它一个绰号叫
一元强拆游牧秩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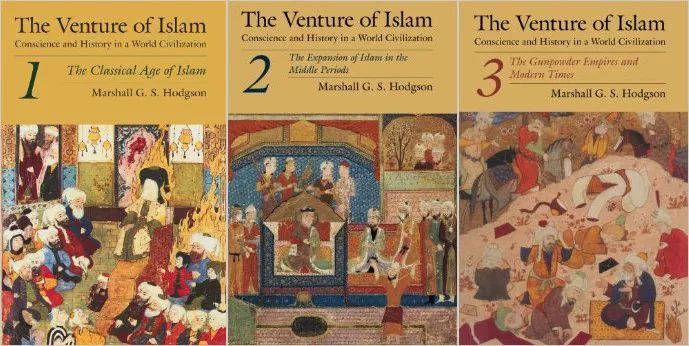
霍奇森,《伊斯兰的历险/试炼》,3卷6分册
霍奇森认为,伊斯兰完整地承袭了这种
犹太—波斯
式样的二元世界-生活图景,这与南方阿拉伯沙漠游牧民族北上扩张征服行动中疏离西部拜占庭、亲和东部波斯的轨迹刚好是重合的。试想一下,如果他们征服了拜占庭,继而与基督教拜占庭秩序发生混合,又会催化出什么东西呢?Christian-Islamic?不可想象!
霍奇森,highly aptly,在这个环节提示道:与犹太—波斯传统相较,基督教则没有整体性地革新、
净化
整个世界的野心,他们仅仅满足于建立一个离群索居的少数群体,仰赖着不洁净的世界的鼻息而生存,
“基督教的精神不支持把所有社会层面都建立在修道院式的雏形上。”
翻译成我的语言就是,这个教派致力于一种与世界小心翼翼的混合,在保留一种二元图景的同时,试图谋求一种不那么致命的混合,也就是说,这个教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不洁净”,所以也就有了
血淋淋
的十字架这种
生物性肮脏
的事物可以赫然占据着该教派最核心的位置,这在激进的二元论者
(比如
马克安和我
本人)
看来简直是不可饶恕的对上帝的莫大亵渎!——这种对一个不洁净的世界的妥协
(二元论身体上的一元论欲望)
是这一派的神经中枢所在,随着这一混合的完成度越来越高,它给自己、给世界所引发的痛苦也越来越剧烈,最终导致了15-17世纪的
“大分离”
,那个分离场面异常惨烈,因为它撕裂了血肉和灵性,混合的双方都赔付了巨大的代价。
值得一提的是,那场被称为“政教分离”的大分离,在犹太秩序、伊斯兰秩序、古萨珊马兹达秩序中都没有出现过,原因上面已经讲过,它们从来没有出现过实质的混合,所以也不会出现痛苦的分离,这从伊斯兰秩序中的阿里派、出走派、什叶派、阿萨辛派这些极端洁净主义派别所引发的微小波澜即可见其一斑。
这是一种幸,还是一种不幸,
只有亚伯拉罕、安拉和阿胡达知道
。
(霍奇森把佛教归为基督教一类,也是一种试图谋求一种混合的宗教,可惜他没有继续深究,我对佛教的观感是它在谋求与世界混合的长路上早早夭折了。)
霍奇森的
世界诸宗教史
学养不次于马克斯·韦伯,甚至直追威尔豪森那一代巨擘
(稍微夸张了一点)
,拥有这种学养的人自然而然都有一种“比较研究”的本能。在讨论洁净与不洁净这一关键环节,霍奇森谈到了
“中国秩序”
,作为中国读者,这很容易引起我的高度注意,这段话原文抄录一下。——
首先,霍奇森用“告解宗教”
(confessional religion)
统称前述几个大教派,这是一个非常“cute”和“acute”的名词,它提示的是一个庞大文明体的根本气质和性格,一直到卢梭写作《忏悔录》
(
Les Confessions
,1770)
的时代都不绝如缕。霍奇森说:
“所有的告解宗教传统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它们都意图改革所有社会模式,以切合宗教上的要求,并消除早前世俗的虚假思想,而中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中国境内,任何在告解宗教传统中发展而成的上述期望,都几乎彻底失败。在默罕默德前的几个世纪,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徒偶尔能够成功地对抗
儒家哲学
,但他们无法阻止儒家精英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取得主导地位,尽管儒家也受到告解宗教的影响,引入一种更为宇宙观的思想倾向。”与此相较,“欧洲的例子则相反,基督宗教成功消灭了
柏拉图和斯多亚哲学
家的政治势力,虽然在六世纪以前,他们的胜利也备受挑战。”
(霍奇森,中文台版,上卷第2册,页14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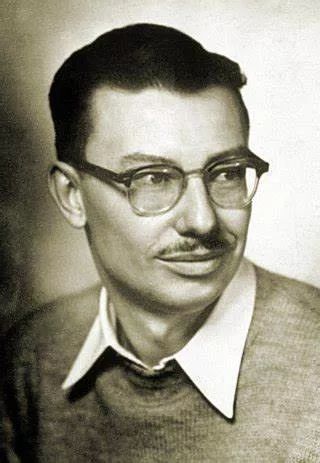
霍奇森,1922-1968,史学巨擘
霍奇森这段话蕴含的内容远远大于它表面呈现出来的东西,非常耐琢磨,它似乎在儒家哲学与柏拉图哲学(以及代表着它
晚期溃败状态
的斯多亚哲学)之间谋求一种共同性,换言之,他似乎试图把这两个教派划归到某种“不洁净的”或者准备与“不洁净的世界”谋求混合与妥协的阵营之中。
(这是一种“正典”阵营)
——这似乎就是儒家哲学和柏拉图哲学的交集点,这个交集当然仅仅发生在政治层面。对于政治表象之下潜隐着的巨大理论冰山,霍奇森没有再追问了……
洁净与不洁净的混合,就是政治哲学家
沃格林
用“居间”
(metaxy)
这个词试图指称的东西,他希望用这个词归纳古典希腊生活秩序的根本意图特质,并与东方希伯来传统开辟的“逃离”
(exodus)
路径相区别,这就是“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的大概含义。这是一个非常粗陋的解释框架,只能在极度狭窄的范围内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此处不祥论)
在针对
《灵知沉沦的编年史》
(商务印书馆,2019)
这本书(
——这是一本为健康的二元论认知图景提出重要辩护的小书
)撰写的书评中,
小枫
援用了沃格林的“居间”(metaxy)概念,并发出了恳切的
告诫
,试图把那个“逃离”的《编年史》作者唤回“居间”的正典之道。这是那篇长篇书评最有价值的部分。
然而,正如《灵知沉沦的编年史》所试图论证的,在这个充斥着致命混合所导致的灵知沉沦的
空难现场
的年代,一种指向洁净理想的“告解”比一种谋求与不洁秩序的混合的“告诫”更具迫切性。——新秩序往往诞生在“逃离”的路上,而旧制度在混合中必死,这是古代出埃及的
摩西
和长征在雪山草地中的现代
红军
留给我们的命运般的指引。
Magnus ab integro saeclorum nascitur ordo
.
(Vergil,
Eclogae
, 4.5)
(2020.02.02 疾书于南国,瘟疫年代,致命的混合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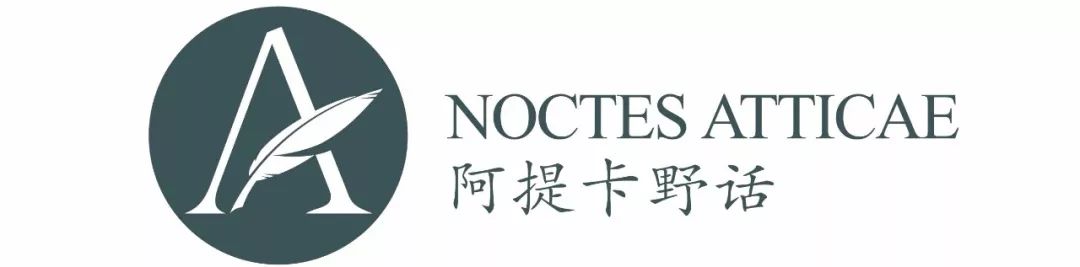

漫漫冬夜,阿提卡乡野蛰居的日子,草草写下这些笔记,是为“阿提卡之夜”。
Aulus Gellius,
Noctes Atticae
,Praef,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