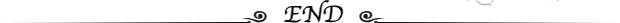《耳朵缠着绷带、吸烟斗的自画像》(
1889
)
乔治·巴塔耶 /文
○●○●
lightwhite /
译
拜德雅·卡戎文丛主编
泼先生执行编辑
在其劝服的力量中令人安心的卓越的形象如何在我们中间出现?在无限可能性的混沌中,某种散发一道突如其来之光辉,散发一种排除疑虑的信念之力量的形式,如何成形?这似乎独立于人群而发生。人们一般同意,一旦一个人停下来在一幅画的凝视中徘徊,这幅画的重要性绝不取决于别的任何一个人的赞成。
这个观点,当然作为一种对一切明显蒸发了的东西的否认,而站在展览的油画面前;访客不是来寻找自己的快乐,而是来寻找别人对他期待的判断。但强调绝大多数观者和读者的贫乏没有什么意义。在当下惯例的荒谬界限之外,甚至透过包围绘画和梵高之名的鲁莽的困惑,一个世界可以敞开: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人不再心怀怨恨地对人群置之不理,而是对我们自己的世界置之不理,在那个世界里,当春天到来的时候,一个人以一种欢乐的姿态,抛弃了自己厚重的、发霉的冬衣。
这样一个脱去外衣,随众
——
更多地在天真而非轻蔑中
——
漂浮的人,不得不带着恐惧把悲剧的油画视为如此之多的痛苦符号,视为梵高之生存的可感踪迹。但那个人随后会在不只他自己一个人身上感到梵高所代表的伟大:他仍在共同之悲惨的沉重下,时刻跌跌撞撞
——
不是在他一个人身上,而是因为他在他的赤裸中,是对所有那些欲望生命,并且同样欲望摆脱尘世的人而言未经诉说的希望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也是那与他毫不相似的东西之权力的承担者。感染了这全然未来的伟大,这样一个人所感受的恐怖会变得可笑
——
可笑,甚至,耳朵,妓院,
“
梵高
”
的自杀;他不是把人的悲剧变成了其全部生命的唯一对象,不论是在哭泣、笑声、爱,甚或斗争中?
他必然惊异到这样的程度,对强大的巫术发出笑声,而为了这个巫术,野蛮人会毫无疑问地要求一整个迷醉的人群,得到维持的喧嚣,以及许多鼓的击打。因为梵高从他自己的脑袋上割下献给那
“
房子
”
的不只是血淋淋的耳朵(我们向他人再现的令人烦恼的、粗糙的、幼稚的世界图像)。梵高,他在
1882
年决定成为普罗米修斯而非朱庇特,从体内撕下了不是一只耳朵,而恰恰是一个
太阳
。
首先,人的生存要求稳定性,要求事物的持久。结果是一种就一切伟大而暴力的精力耗费而言的矛盾心理;这样的耗费,不论是在自然还是人身上,都代表了可能最强大的威胁。由此诱发的赞美和迷狂的感觉因而意味着,我们远远地关注着赞叹它们。太阳最为便利地回应了那种审慎的关注。它是全部的光辉,是热量和光的巨大散失,
火焰
,
爆发
;但它离人很远,人可以安全地、静静地享受这个巨大灾变的果实。维持石屋和人之脚步的坚固性属于地球(至少是在它的表面上,因为埋在地球深处的是火山岩浆的炽热)。
关于舍弃,必须指出的是,
1888
年
12
月的深夜过后,在其进入的房子里,他的耳朵遭遇了一个一直未知的命运(人们只能模糊地想象在某个未知决定之前的笑声和不适),梵高开始赋予太阳一种它尚未拥有的意义。他不把它作为布置的一部分引入油画,而是像用缓慢的舞蹈唤醒人群的巫师一样,在其运动中传送它。在其绘画的一切最终变成
辐射
,
爆炸
,
火焰
的时刻,他自己,在
辐射
的生命之前,失于迷狂,
爆炸
,
燃烧
。当这太阳的舞蹈开始之时,突然之间,自然本身受到撼动,植物爆发成火焰,而大地像一片迅猛的海洋一样荡漾,或爆发;事物根基处的稳定性不复存在。死亡在一种透明中出现,就像黑暗所勾勒的骨头的裂缝里,穿透了一只活手之鲜血的太阳。花朵,明亮或黯淡,令人沮丧地憔悴的辐射之面孔,梵高的
“
太阳花
”——
不安?支配?
——
终结了不可更变之律法的所有权力、根基的所有权力、一切把讨厌的防御色彩赋予面孔的东西的所有权力。
但太阳的这一独一的当选不得引发荒谬的恐惧;梵高的油画
——
就像普罗米修斯的斗争
——
没有形成一份献给天空的遥远至尊者的礼物,而太阳,就它被捕获了而言,是主宰的。地球,远没有认识到天上灾变的
遥远
力量(仿佛只有其单调的、免于变化的表面的一种延伸得到了要求),就像一个因其父亲的放荡而突然目眩并堕落的女儿一样,反过来沉溺于灾变,沉溺于爆炸的迷失和光辉。
这恰恰解释了梵高绘画的巨大的节日的特性。这位画家,比其他任何人,更具有那种花朵的感觉,它也在大地上再现了陶醉、欢乐的堕落
——
爆发、闪耀的花朵把它们燃烧的头抛入让它们凋谢的太阳的光芒。在这深刻的诞生中有如此的扰乱,以至于它诱发了笑声;我们怎能忽略把耳朵、收容所、太阳、盛宴和死亡如此肯定地联系起来的纽链?梵高用一把剃刀的一划割下了耳朵;接着把它带到其所知的妓院里。疯狂激励着他,正如一种暴烈的舞蹈维持着一种共同的迷狂。他画出了他最好的画。他有一段时间待在收容所里,而在割下耳朵的一年半后,他杀死了自己。
当一切就这样发生的时候,艺术或批评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甚至可以在这些情境中坚持,艺术本身会解释展览大厅里人群的响声吗?梵高不属于艺术史,而是属于我们人之生存的血淋淋的神话。他是在一个被稳定性,被沉睡困住的世界里,突然抵达可怕
“
沸点
”
的极少数的同伴,没有那个
“
沸点
”
,一切宣称持忍的东西都变得无趣、不可容忍,并没落了。因为这个
“
沸点
”
不仅对获得它的人而言,具有意义,而且对
所有人
,都具有意义,哪怕
所有人
还没有
觉察那把人的野蛮命运束缚于
辐射、爆炸、火焰
,因而唯一地束缚于权力的东西。
193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