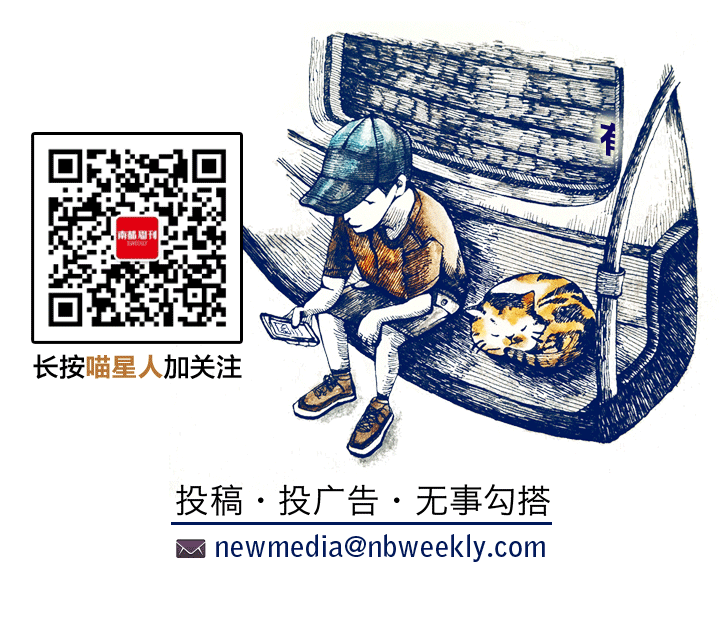隐私之所以成为难言之隐,其根源仍在于社会的恐慌。一个艾滋病感染者,很有可能被拒绝上岗,很有可能失去朋友,很有可能在学校、社区、工作环境中遭受各种非议、诽谤和排挤。
文◈
姜思达
文章经授权转自公众号
思达帕特
(ID:
SidaPart
)
11月16号,我推了一条文字——
“想找到6-8个艾滋病人,有意一起吃个饭加闲聊天。
地点北京,时间在本周。
ok的话可以给我发一封邮件,不必署名不必贴照。邮箱[email protected]。
需要你在邮件里尽可能提供年龄、性别、性取向、大致职业、病情、本周何时有空。
我会保证你的隐私,请放心。”
首先为我不当的措辞道歉,比较合理的说法是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感染者
而非艾滋病人。HIV携带者和AIDS发病人群不是同一个群体。推送文字的时候没有注意用词,是我的过失。
推出这条文字后,我一直在收件箱里刷新。五分钟内,收到十余封来信。此后的三天,我和同事一直在检索信件,并望寻求联系。这些信件中,有讲述自己的病情和个人情况的,也有人跑来凑些热闹的。更多人在后台回复消息。这些消息,有表示关注和支持,有表达困惑的。实话讲,有两种常见的回复我特别的不解——
一种是:“大美玲你有什么想不开的?”——
这些人把HIV携带者妖魔了,仿佛我和他们吃了饭,我就被感染了。
另一种是:“哇我从来没有这么想得艾滋病!”——这些人固然在表达浓浓爱意,可是
又把艾滋病随意化了,开些并不好笑的玩笑。
正如那则广场舞大爷传播了艾滋病的新闻——如何提高中老年群体对艾滋病防范知识的议题迅速被“哈哈哈炮王”这类的调笑取代。
HIV携带者从来不应该被当作怪物去恐惧,这不意味着艾滋病是一件能来开玩笑的事情。
严肃的时候不该活泼,轻松的时候不该紧张。这仍然是本文想要传达的观点。
在征得各位同意后,同事拉了一个微信群——这群里有七位HIV携带者、一位AIDS病患家属。19日,我们共十人,一起吃了这顿饭。
在走去餐厅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吃饭的时候我该说些什么。我不想充当记者,去做深度访谈,去调查,这些事情已经有很多人努力在做了。有大把大把的数据和报道,在艾滋病日这个档口你无法无视。我希望我能浸透地参与进去,闲聊,不带有任何设定和节奏,想到哪里聊到哪里,即便给后期成文增添了一些难度。
因此我只能尽力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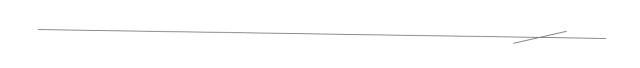
餐厅在朝阳门附近。6点的时候,我到了三楼的包厢,一开门,看到已经有两位坐好,还有我的同事。两个男生,他们看到我,惊了。是那种,“哇塞见到本人”的那种惊。事实上在前一天晚上,收到群通知的他们,就在说,哇又兴奋又紧张。其中一位在事业单位工作,理工男;另一位是河南过来的学生。
说实话,刚开始的气压有一点低,我不太知道该说些什么,可能也是因为餐厅没什么背景音乐,服务生脸还怪臭的。其他几位陆续来了,我们就一起看菜单,等人。一群陌生人吃饭,真的不好开头;而这顿饭又有一个难以隐藏的话题,且这个话题无法让人喜笑颜开。40分钟后,最后一位女生到进来了。她进门的时候戴着口罩,说刚下班,堵车。
除了那位病患家属,其他人都是携带者,
6个男生1个女生
。因为我的受众差异,关注我的直男比较少,所以这6个男生也都是gay。他们的年龄从18到28,这意味着理工男要比学生男大10岁。有即将出国读大学的,有硕士在读的,有工作的。共同点除却感染外,就只有都是我的粉丝,一般进门之后第一件事是和我怒拥抱一发。
我们点的菜,避开了所有的“发物”和酒水。河海鲜居多的菜单上,我们能点的并不多。朋友跟我讲一个故事,他本身很排斥中医,有一天他一位患艾滋的朋友告诉他不能吃发物的时候,他调笑了一番中医理论。
他的朋友说:“那是你他妈没得艾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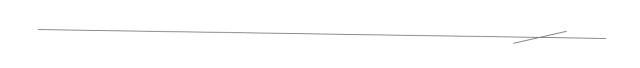
“我性生活那么少,怎么也没想到我感染了”
得知阳性,换谁都不会好过。但确诊阳性的时候,他除了难过还有纳闷——“我性生活这么少一人,我怎么感染的?”事实上吃饭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还在推算是因为那次对方牙龈出血还是别的。
“别说了,估计就那次。”我说。
“嗯!应该是。”
有人比较清楚自己的感染来源——他认为另一方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不知情,而他提出相约检测后,对方在一阵激动后把他删除了。而除此之外,
饭桌上的大家,都没法说清是谁把HIV传递给他们的,如果一定要用“罪责”去形容这件事,他们一定是受害者。
但罪责说来也不妥当,这件事里,没有坑害,只有不幸——除非是对方明知自己阳性却不跟你讲甚至在套上动手脚。
年龄最小的一位,是今年查出来的,但是几年来身体一直都不好,以肺炎的病症住院。查出来的时候,他的CD4
(表面抗原分化簇4受体,通常身体素质较好的人CD4在500以上)
低到了个位数,医生推断,应该感染三年了。“但也没什么别的表现。”
而其他人,也多是近期查出来的——最近的一位是饭局前五天,他也因此正好吃了五天药。换句话说,若我在11月10号发布这则文字,他都不会参与进来。
“我也挺纳闷的,我认识的人,嘿,比我’乱’多了。人家都没事儿,我有事儿。”他说这话的时候,调笑中带点气。他得知阳性后,几晚上睡不着觉,一直在网上搜索治疗的相关信息。
“有条件应该去泰国,有些最新的药是美国发明的,但是世卫组织应该有一种特许,默认事关重大的医疗药剂不受专利限制。泰国有百万感染人群,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研究美国的配方……但是请假是个麻烦事。”他是这个局里年纪最大的那位,期间一直给大家普及信息。
如果说久病成医,那么被检出HIV,可以让一个普通人在两天内成为专家——用尽一切精力去获得信息。
有人查出来也因为偶然——献血。学长让他陪去献,虽然他心里还比较抵触献血这件事,但最终还是去了。正在上课的时候,医院打电话通知了他的化验结果,称血液中检测出HIV——那是他生日的第二天。回到教室的下一堂课上,他努力向同桌讲着一则饭局中全桌人并不觉得好笑的笑话,用以平复心情与故作镇定。
“真的不好笑吗?”
“真的不好笑诶。”我说。
“哈哈哈好吧。”
被检测出HIV的他们,有人相对乐观些,也有的更加冷静理智,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但大多数人都难以“真正地相信”自己感染的现实
,那个女生,对谁传染给她也闭口不谈,可能没有听到我的问题。在局里她的话非常的少,表情又很严肃。
——没有人是注定要来这个局的。一周前、一个月前、一年前的他们,本都不必来。
“觉得不是真的。”这是那女生说的为数不多的话之一。餐桌转盘在徐徐转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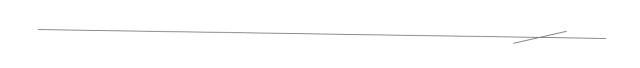
“这个发的药盒,比自己买的还好”
这几位基本都开始用药,聊到药的时候,像是粉丝们拿出一模一样的应援板——他们拿出一模一样的药盒,整个包厢哗啦啦地响。药盒都会随身带在身上,圆形的几粒、椭圆形的几粒。
这些看不出任何门道的药片,按照目前的医学进展,将会陪伴他们可预见的一生,帮助他们把HIV数量控制在某个水平下,以“HIV带原者”生活,不致艾滋病发作。
每月领药,一天一次按时吃。
“绝对不能停,药一停,HIV就有变异的机会,这款药对它来说就失效了,就不得不换药。”目前他们领的药,都是国家免费发放的,采取主流的鸡尾酒疗法。“我定的是每天十点吃,绝对不能错过或忘了。”
人可以一天不睡觉或一天不吃饭,但是他们不可以一天不吃药。
我们用肉眼看自己的身体时,看不出任何一枚HIV病毒都在做些什么,起一些什么变化。我们能做的除了定期检查,就只有吃药、吃药、吃药。
“我去医院检查的时候,看到河南的那些一家子一家子在医院领药。”之前有一篇文章提到过这些人卖血感染的事情。“但我还没有开始领,我怕过年回家拿着一大堆药父母发现。”
“那不行,我建议你要早点上药。”其他人开始劝这一位。“嗯,医生说勉强还可以先不用药一个月,我也在等第三次检查结果。如果必须用,那就用。”目前,他们CD4水平良好。
关于药的副作用,他们说刚吃药的时候会晕沉沉的。“我明显感觉到记忆力不行。”但还是要吃的,除了怕父母发现的那位,其他人都开启了自己的用药史。他拿着手中的药盒说:“这个发的药盒,比自己买的还好。”
“有个新闻是说,一个人被一条狗给咬了,结果发现自己的HIV病毒消失了。”
“对,还有一个人,接受了骨髓捐献。捐献者拥有一种不会感染HIV的基因缺陷,然后患者就神奇地痊愈了。”
这些新闻里的小概率事件,成为偶尔爬上他们心头的一道阳光——倒也不知道哪条狗咬了自己就好了。
“大家放轻松啦,我们还年轻,我们肯定能等到痊愈疗法出现的那一天。”我是真的这样相信着,才这样说的。我不是在冠冕堂皇地打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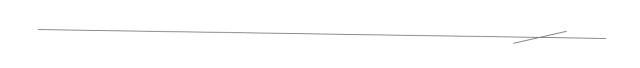
“坚决不能让他们知道”
在饭局筹备时,同事收到最多的问题是——这个饭局的目的是什么?会不会保密?甚至女生提出,能不能戴口罩去?我说,我们是吃饭诶,怎么戴口罩。
为了保护他们的秘密,我保证不会在文章中涉及任何指向性线索,也为了让他们相对自在地聊天,除非自己说出来,否则我不会问及他们的姓名。这些人都叫做什么,我目前也不知道。
这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最大的苦衷,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人去讲。偶有交流,也限于极亲密关系的朋友、关怀小组的病友。年纪最小的那位,父母离异,他的母亲知道,但是父亲不知道。
“坚决不能让他们知道……没必要。”
今年有一则新闻加深了他们的恐慌。有报道称一些艾滋病感染者接到了诈骗电话,不能满足对方条件就会把他的个人信息暴露出去。事实上信息已经暴露了,且暴露给这些图谋不轨又丧心病狂的犯罪分子。官方语境中,国家艾滋病感染者相关信息系统被列为国家网络信息重点安全保护对象,并且按信息安全三级等级保护进行管理。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的信息暴露仍存在巨大隐患。
隐私只是表象,
隐私之所以成为难言之隐,其
根源仍在于社会的恐慌。一个艾滋病感染者,很有可能被拒绝上岗,很有可能失去朋友,很有可能在学校、社区、工作环境中遭受各种非议、诽谤和排挤。
“艾滋病感染者肯定不检点。”“他会把艾滋病传染给我。”但即便拥有相关的知识——比如了解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只要不发生,就不会感染——也难以让一个普通人泰然所素地与艾滋病感染者共餐与共游。
因此它固然是一种生理疾病,但
它也全然是社会的心理疾病——这是所有人的心理疾病。
“大学开学的时候,有一节卫生课普及艾滋病知识。但是开始没多久,就变成了同性恋批斗大会。老师始终讲同性恋怎样怎样的,下面的人也跟着起哄。”来自杭州的大学生说。
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关联带来的不恰当的传达,是一种传播手法的问题。你可以在数据中发现同性恋中HIV携带比例确实比较高,但你不能因此认为“同性恋是艾滋病传播主体”,这是相对比例和绝对比例的差异;也不能轻易地表达“同性恋是艾滋病高危人群”——这种传播极易带来污名化的误导。
“其实我比较建议说——把高危人群改成高危行为,我们只说行为,不指向任何一群人。”另一位拿着筷子,郑重其事说出了这句话。
我们早已进入艾滋病知识普及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如何在普及中恰当地、有节制地传达。不应该有哪个人是高危的,只应该有哪个行为是高危的。事实上我所能接触到的同性恋人群,都对AIDS有高度的重视,他们对HIV检测的频率远远高于我身边的异性恋人群——不是相比谁高谁低,而是想让所有人都将一部分生活精力,分配给与自己生计密切相关的身体检查。
艾滋病作为心理疾病存在时,伤害的是那些已然不幸的HIV携带者——
他们的工作,不会让他们传播病毒;而让他们失去工作,却是你心理病带来的后果。
他们的性取向,不会让他们传播病毒;而从人群中圈出他们,标红加粗,却是你心理病毒的大肆传播。
每个人都有基本的分享欲——事关自己的喜怒哀乐的重大事件,一个人扛太难——但在这个时代的思维中,他们不得不继续扛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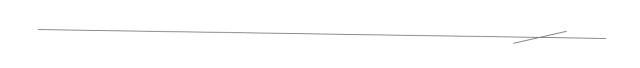
“没感染的时候,有一个HIV携带者喜欢我,被我拒绝了”
他们应该拥有自己的爱恋,拥有和众人一样属于年轻人的热络的私密的交往。但比较可惜的是,这将成为另一桩难事。
“我还没想过。”
“嗯,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办。”
另一个女生,父亲因艾滋病去世,她分享了自己和母亲都没有受影响的现状。而这样的事也频现报端,夫妻二人同居几十年一方没被另一方感染这样的事。
我想起去年这个时候到北大参与了一场世卫组织的辩论赛——关于安全套的发放。组织者一直非常郑重地提醒我们,不应该叫它们避孕套,要叫安全套——因为Condom这个东西,不应该在第一时间内和避孕联系起来,而应该是安全——它以极高的概率保证我们发生性行为而不受病毒传染。
但你真的很难解释,我们只要带套,就可以相爱——甚至很难实践。
桌上几位应该都是单身。其中一位提到了谈恋爱这件事,说曾经有一个人追他,那时候自己还没有感染,但对方坦白了自己的病情后,就没有接受。
他未曾想到自己也会进入这种非常被动的情感状态。
一位携带者从杭州赶来,他正在报考阶段,想读传媒类专业。“我可能发育比较早,8岁的时候有了性意识,初中搞对象……后来接触的人年龄都比较大。”这些“年龄比较大”的男人似乎没有给年轻的他施以足够的保护,而曾经的他也许数次掉以轻心。
“啊!你那么小,我比你大十岁。我身边都没接触你这么小的。”
“但我接触过大的啊。嘿嘿。”
台湾地区的手天使拯救的是残障人士的生理需求,因为后者不能自己解决;而HIV携带者,阻碍他们正常性生活的是复杂的心理情绪。但这里面有人仍保持着安全措施下的性行为,发生的对象是否是携带者,我也没多加追问。
我又问到身旁的大哥,“嗨,你检测出来后做过没?”
“我五天前刚查出来的,怎么可能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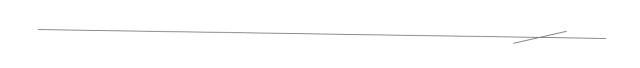
我们闲聊了各自的出柜史,也基本吃得差不多了。
结束之后我没想到他们还想一个一个和我合照。那一刻我像是回归了一种常见的身份——我重新变成了kol也好艺人也罢,他们重新变成了粉丝。
但与被喜爱相比,我更喜爱了解别人的过程,和传递的过程。他们似乎也不需要格外的汹涌的关怀,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不需要类似AA互助那样的场合,不知道说啥。”我能想到的是,不要给他们添乱就好了。因此这篇文章不是写给他们的,更像是写给屏幕前的你的。
九点来钟的时候,我们十个人挤在同一部电梯里,有人搭地铁,有人启动自己的车,有人回郑州有人回杭州,同事回去忙工作,我去和别的朋友喝酒。
——这是一顿平静的饭,这顿饭,和其它一顿饭,真的没什么两样。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