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2年10月爆发的中印边境冲突是冷战期间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中印、中苏和中美关系的走向,以及冷战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使得美国开始重估中国的战略意图与能力,加上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中国的强硬反应,使得美国对华威胁认知大大升高。肯尼迪政府一改初期试图调整对华政策的尝试,转而强化对华遏制政策,并将扶植印度制衡中国作为强化其对华遏制战略的重要一环。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也成为加剧中苏分裂的重要事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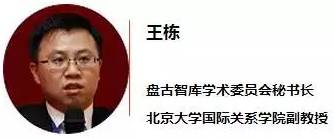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是冷战期间的一个重大事件,不仅对中印关系、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走向,而且对冷战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同时,国内学者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苏联方面的档案资料,对美苏对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基于这些研究,本文试图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与肯尼迪总统图书馆)与中国(包括外交部档案馆和江苏省档案馆)的档案资料,考察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对1959年—1962年间的中印边境争端如何影响中国对印度和美国的认知、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以及中苏围绕中印边界争端的争执和美国的战略选择等问题进行探讨。
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印之间曾经经历了“政治蜜月”。由周恩来总理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954年联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标志着中印友好关系及双方在不结盟运动中的紧密合作。共同的反殖民主义的经历使得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亚洲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同声共气、紧密合作。
然而,进入50年代后期以后,中印在西藏问题上的争执及在边境的冲突,导致中印关系迅速恶化。1959年3月,叛乱失败之后,DL喇嘛被劫持逃往印度,使得中印关系骤然紧张。
叛乱和DL喇嘛出逃使得中印两国关系中原本一直处于水面之下的西藏问题浮现出来。印度在此之后的种种举措也使得中国领导人开始对印度在西藏的意图产生严重怀疑,特别是开始逐渐形成印度搞敌对、挑起边境纠纷是为了获取美援的认知和判断。
1959年5月,在会见苏联等11国社会主义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周恩来指出:尼赫鲁和印度大资产阶级的目的是要“使西藏停滞不前,不改革,作为‘缓冲国’,置于印度势力之下,成为它的保护国”,“这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印间的争论中心”。
在1959年7月的一次内部会议中,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指责印度长期以来一直对西藏“垂涎三尺”,并“试图把西藏变成一个缓冲区”。
1959年10月,中印爆发小规模的边境冲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在1959年12月底的一次报告中谈道,中印边境冲突“暴露了民族主义的真面目。过去只看到它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积 极 一面,现在看到它暴露了他对西藏的领土野心。想借西藏问题向我们敲竹杠”。
“他要向西藏扩张,这是事实。他不策动,DL坐在西藏不是好好的,有什么问题”。陈毅幽默地说道:“印度干涉西藏失败,……把坏事变成了好事。现在达赖真正变成了和尚,修身养心”。
陈毅又语带讽刺地隐射刚刚访美的赫鲁晓夫道:“DL要朝圣,艾森豪威尔是西方圣人,DL要朝圣应到西方去朝艾森豪威尔,现在却跑到什么圣地去了”。
陈毅认为,面对印度挑起的边界纠纷与敌对,中国坚决顶住,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因为“我们真正得到了西藏,从元朝以来没有解决的,现在解决了”;“随你怎么反,西藏他是争不去的。不管怎样,西藏总是在我们手中”。
“西藏问题的胜利,是我们得到了西藏,DL成了和尚”。陈毅认为,印度不敢“对中国挑起全面斗争”,“只能利用西藏搞些负面宣传。我们将来一定要把铁路修到喜马拉雅山。这个局势不是印度能阻挡得 住 的”。
陈毅判断:对于中印边界问题,尼赫鲁“不愿扩大,也不愿爽爽快快地解决,他要保留一个缺口来解决他们国内问题。”陈毅认为尼赫鲁旨在“一箭三雕”:
首先,要打击、削弱、缩小中国的政治影响;其次,打击、分化印共和进步势力,说“印共是中国的工具”;再次,同时依靠美国借债度日。
1960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时,抨击尼赫鲁希望在美苏两大阵营“左右逢源”,并且利用中印边境争端问题向美国和苏联寻求援助。
1960年4月,中共中央调查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题为《印度国内形势的特点和对中印会谈的打算》的分析报告。这份报告指出:
近一两年,印度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其主要原因是印度经济困难,四处求援,在制造中印紧张局势后,又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印度的外交更加摇摆,但还不放弃不结盟政策。
中央调查部还对美国对印政策做出了分析:“美国统治集团认识到一下子迫使尼赫鲁改变外交政策是有困难的;‘中立主义’对美国搞假和平并没有害处。
反之,利用这块招牌更有利于扶植印度来‘抵制’我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因此改变了过去对尼赫鲁‘操之过急’的做法,更多以美援为钓饵,采取明捧暗压的策略,逐步地迫使尼赫鲁彻底改变外交政策。这种做法收到一定效果。
印度目前已经越来越深地陷入美援泥沼中,美援已成为印度考虑外交问题时的一项重要因素”。报告估算,从1948—1959年底,印度接受帝国主义国家援助共33.5亿美元,其中美援(包括世界银行贷款)为26.62亿美元,占78%。
而且,中央调查部认为,从美援的数量和条件看,美国都加大了拉拢印度的力度:美援的大部分是最近这两年答应给的,条件也有所放宽,如1959年11月签订的一项剩余农产品协定,赠予部分即达40%,而且免费运送。过去此类协定的赠予部分一般只占15%—20%,运费也由印度承担。中央调查部的报告继而对美国试图诱使印度改变不结盟政策的策略也做了分析:
“印度挑起中印边界纠纷后,美国一方面鼓励右派大吵大嚷,企图使中印关系长 期 紧张,另一方面又力促巴基斯坦对印度和解,要求(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一再提出‘印巴联防’的建议。
在美国的鼓励下,印度右派(包括一些高级军官)正和巴统治集团密切交往。美国阴谋趁机引诱印度和军事集团挂上钩,从实质上改变不结盟政策。”
中央调查部还指出:美国还暗中多次向印度提出军援方案,宣传印度可向印尼一样,接受军援而不放弃“中立的原则”,并对因购买军火已给予方便,如不用先付订款和提早交货等。
中央调查部的报告认为,尼赫鲁及其印度统治集团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视为“对它很大的威胁”,“惧怕我国每一个伟大的成就,力图缩小我国的政治影响,因而在我国大跃进以后,即逐渐公开采取捧苏联、压我国,并拉一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
这种做法又正好配合了美国集中打击我国、分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战略,讨得美国的欢心。尼赫鲁挑起中印争端后,苏联持中立态度,还给印度贷款
这使得尼赫鲁更以为得计,甚至幻想通过苏联‘抑制’我国,印度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套做法于是更为露骨”。中央调查部的报告不无忧虑地指出苏联、捷克和波兰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一年以来对印度援助大为增加。
从1955—1960年初,印度共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获得38.42亿卢布(合8亿美元)贷款,其中苏联占32.2亿卢布(合6.76亿美元)。
而这些援助中的绝大部分(24.26亿卢布,合5.1亿美元)是1959以来给的,其中仅在1959年苏联就答应给印度援助20.16亿卢布(合4.2亿美元)。
中央调查部的报告认为,自从中国平定西藏叛乱,打破印度想把西藏变为所谓的“缓冲国”的幻想之后,印度深怕中国影响扩大,借口“共同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加紧对尼泊尔、不丹和锡金进行扩张,企图变这三国为印度敌对的“第一道防线”。
印度不仅增加在锡金的驻军,阴谋伺机吞并锡金,同时还想压尼泊尔和不丹接受印度驻军的要求。中央调查部也指出,印度为了集中力量敌对,避免两面树敌,同时也由于美国的“调解”,印度同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表面上有了某些缓和,但矛盾还很尖锐。
两国官方都公开承认,克什米尔问题不解决,印巴关系很难改善。实际上,仅在1959年,印巴在克什米尔邦的边境冲突达115次,死24人,伤22人,较之1958年的冲突次数和伤亡人数都增加了一倍。
在克什米尔停火线和印巴边界上,两国仍然重兵对峙,各占其全部兵力的2/3。中央调查部的报告还对印度可能的政策方向做出分析与估计:
第一,印度准备在边界问题上“与我长期拖”,“同我纠缠,达到把现状冻结起来,伺机再闹的目的”。尼赫鲁已指示外交部要准备同我进行一场印度独立以来“首次大规模的外交战”,收集大量资料同我做“板门店式”的谈判。
第二,印度在致我照会中已表示,不准备和我全面谈边界问题,只能做“较小的调整”,实质上“容忍”双方实际控制线的现状,但不愿使它“合法化”,避而不谈解决问题的原则,把会谈局限于如何避免再次发生冲突的具体措施上。
第三,印度提出所谓“以东换西”方案向我讨价还价,实际上是使目前中印控制线“合法化”。中央调查部估计,“这可能是印方解决边界问题的底牌”。
中央调查部认为印度之所以抓住东段不放,根本原因是它已经事实上占领了中国这片领土。而且在印度看来,东段现状一打破,将“意味着放弃喜马拉雅山脉主要山脊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山”,从而削弱“印度的防御能力”。
中央调查部还揭示出印度领导层对于共产主义扩张的担心与恐惧:尼赫鲁甚至认为,一旦没有喜马拉雅山 的 阻挡,印共就可以很方便的得到中国援助,印度的“东北特区”有沦为“印度的延安”之虞。
第四,除中印边界外,印度还可能提出西藏问题与我纠缠,主要包括三个内容:(1)要同中国就“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下的地位”达成某种“谅解”;(2)探讨DL回藏的可能性;(3)印藏贸易和留藏印侨的问题。
基于这种分析,当时中国领导层提出的对印方针就准备与印度“拖”,长期保持“和平武装共处”的状态。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访印,与尼赫鲁就中印边界问题谈判未果。中印边境继续处于僵持状态,“不仅没有和缓,反而日趋紧张”。
1960年初,尼赫鲁和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多次召集高级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制定了所谓的“前进政策”的方针。1961年11月,尼赫鲁召开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决定继续推进“前进政策”。
面对印度步步蚕食、咄咄逼人的姿态,中国也开始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在印军越境设立的哨所周围构筑更多据点,以遏制印军行动。
由此,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出现双方哨所、据点“犬牙交错”的局面;同时,中印“照会战”不断持续,中印边界从外交上、军事上逐渐出现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中国领导人对尼赫鲁已经毫不信任,认为尼赫鲁“有奶便是娘”,已经“恬不知耻地”倒向美国,“自觉地作(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北京研判印度挑起边界争端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依靠美国借债度日”。但实际上,在1959年,美国在中印边境争端问题上态度谨慎。这部分是由于尼赫鲁仍然坚持“中立主义”的不结盟政策,反对将中印边境争端与反共联系起来。尼赫鲁也明确拒绝议会中的右翼保守势力寻求国外军事援助的要求,宣称从国外寻求帮助或者考虑引入“某些军事集团来拯救我们”是道德软弱的表现。
1959年1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印,试图进一步促成印巴和解。尼赫鲁对艾森豪威尔表示担心当印度应对中国威胁时,巴基斯坦会“在印度背后捅刀子”。
艾森豪威尔立即向尼赫鲁保证:美国将永远不允许巴基斯坦把美国援助的武器用于反印的目的。不过,艾森豪威尔此行未能说服尼赫鲁加入具有反共军事集团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具体条件和方式上双方也存在分歧。
在这种情形下,美国自然不会对拉拢印度加入西方阵营抱有过大幻想。另外,部分由于台湾蒋介石政权的反对,美国对于印度领土的主张并没有给予明确支持。
当DL喇嘛出逃印度之后,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征求美国两位 前 驻 印 度 大 使 切 斯 特 · 鲍 尔 斯 (Chester Bowles)和 库 柏 (J.S.Cooper)的意见,二人都敦促美国政府采取低调,避免公开支持印度领土主张。
对此,中国情报界也有较为准确认识,中央调查部在其报告中指出:尼赫鲁拒绝印巴联防,对美国支持印度右派的做法有反感,对美援的条件也有不满,双方讨价还价很激烈。在美国方面,大量援助印度也不是没有困难。
因此,“印度对美国总保持一些距离,不敢把赌注完全压在美国一边”。1960年,肯尼迪上台之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肯尼迪认为,以往美国的对外政策过于注重正式的军事联盟,而对于不结盟国家重视 不 够。
因此,美国要对不结盟国家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具体到南亚,肯尼迪希望印度在南亚与东南亚能够承担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领导角色。
但是,肯尼迪很快失望地发现,尼赫鲁对于他的大战略构想并不热情。1961年,尼赫鲁访美暴露了美印在国际事务上的深刻分歧,从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到对共产主义影响扩大意义的分析,以及克什米尔、越南和东南亚等问题上,肯尼迪发现尼赫鲁的观点与他迥然有异。
尼赫鲁拒绝肯尼迪拉拢印度承担遏制共产主义领导角色的建议,部分原因是美国拉拢印度的政策受到印巴敌对的极大制约。尽管如此,肯尼迪仍然视印度为“红色中国经济和意识形态力量的主要对抗者”
肯尼迪决意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印度的不结盟立场,以此换取印度增强亲美的倾向,美国经济援助源源不断涌向印度,印度也成为接受美援最多的国家。
肯尼迪上台后,在对华政策上一方面对中国长期的战略意图抱持疑虑,另一方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能力也甚为担忧,因此,维持基本的对华遏制战略局面并没有改变。
但同时,肯尼迪及其主要外交顾问都认为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政策过于僵化,“并不反映亚洲的现实”。早在担任参议员时,肯尼迪就认为
两极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西欧和中国正在崛起,成为新的政治力量中心,在这种战略形势下,美国对华政策过于刻板、僵化,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敌对关系是“不正常的,也是不理性的”。
1960年1月,肯尼迪在讲话中称:“只是因为红色中国是共产主义的,就拒绝承认它,那是无益。”但肯尼迪同时又提出了条件:
“承认中共的先决条件是红色中国保证遵守联合国宪章。还必须有某种表示,表明共产党中国愿意同美国和睦相处”。
在总统大选中,肯尼迪又多次在不同场合声称“明确宣布民主党希望同人民中国和平相处是正确的”,“人民中国应当首先改变它的外交政策,因为它目前的官方政策是好战的政策。如果他们取消这种政策,我们的政策就可能改变”。
肯尼迪主要外交政策顾问如副国务卿鲍尔斯、驻联合国大使民主党领袖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en)及驻南斯拉夫大使乔治·凯南等都主张美国应当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为灵活的姿态,提出“两个中国”的主张,在支持台湾方面的同时,应考虑与中国大陆进行接触,甚至考虑改变对华贸易禁运政策。
另外,国务 卿 迪 恩 · 腊 斯 克(Dean Rusk)、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等虽然不主张改变对华政策,但也都支持“两个中国”的主张。肯尼迪及其主要外交政策顾问的这些微妙态度变化,都得到了中共情报部门的密切关注。
1962年夏,随着中印边境形势日益紧张,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情报系统密切关注中印边境局势。7月18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给美国国务院发回一封密电。
在这封电报里,美国驻香港总领馆对北京在中印边境争端中的战略意图和对策做出了详细分析。美国驻香港总领馆观察道,面临不断升高的来自印度方面的压力,北京采取几手措施。一方面,北京通过舆论宣传指控印度的侵略性和敌意来“准备舆论空气”,并且进一步警告当前局势蕴含的危险
另一方面,北京采取措施力图“使印度进退失据”,为此,北京启动与巴基斯坦的边界谈判,并且宣称愿意与印度进行边界谈判。美国驻香港总领馆认为:“总体而言”北京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态度仍是“防御性的”,尽管“为了维持其战略位置”,北京决意“不惜冒敌意(升高)的风险”。
尽管如此,1962年10月20日爆发的中印边境冲突还是让华盛顿猝不及防。10月20日,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组成的东段指挥部和新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奉中央军委之命发动反击,中国边防军在西线的阿克赛钦和东线跨越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同时发动大规模军事反击行动。
至24日,西藏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东段歼灭入侵“麦克马洪线”以北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第七旅和其他印军一部;新疆边防部队在西段拔除了印军非法设立的37个哨所。
数天之内,印度军队一触即溃,中国军队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印军的败绩不仅对印度总理尼赫鲁造成摧毁性的打击,也使得华盛顿大为震惊。
10月23日,印度外交部部长德赛(M.J.Desai)告知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由于苏联态度倾向中国,印度认为不能指望苏联能够约束中国,所以,印度考虑向美国请求大规模援助。
中印边境冲突爆发的时候正值“古巴导弹危机”之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紧张对峙,核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印边境冲突此时爆发,使得美国决策者不由得不怀疑北京是否有意配合莫斯科,在远东发动攻势,以牵制美国。
自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分歧逐渐浮现时,美国决策者却对中苏分歧的性质和程度一直抱有非常谨慎甚至怀疑的态度。
“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境冲突在一周之内先后爆发无疑强化了这种怀疑。美国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斯的日记也显示当时美国决策者倾向于把“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境冲突联系起来,并认为“古巴导弹危机”是共产主义阵营“侵略行为的开始”。
1962年10月26日晚,肯尼迪总统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浦·塔尔伯特(Philip Talbot)
以及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卡尔·凯森(Karl Kaysen)等人的陪同下接见了印度驻美大使布拉加·库马·尼赫鲁(Braj Kumar Nehru)。
显然,肯尼迪对中国的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战略行为及意图颇感不解。在会谈中,肯尼迪不无困惑地问道:“有谁知道共产主义制度的奥秘吗”?
肯尼迪对印度大使问道:“他们(中国人)从这一冲突到底能得到什么?他们对你们动手了。但为什么他们没有在越南或者其他地方对我们动手呢?而他们又是究竟为什么要对你们动手呢”?
面对肯尼迪的一连串提问,印度大使回答道:“或许他们认为你们会在此卷入并使我们或者你们的古巴成为另一个匈牙利”。印度大使的回答引起在座美国高官的一阵会意的笑声。
然而,当肯尼迪思考北京与莫斯科再次携手的可能性时却 是 严 肃 至 极。众 人 笑 声 刚 止,肯 尼 迪 又 道:“他 们 又 回 到床 上了—俄国人和中国人”。
肯尼迪坦承美国当前不得不面临战略上的两难困境:“当对他们[中苏]压力的升高时,他们就会抱成一团。而当对他们的压力减轻时,他们就又会分道扬镳。但他们现在抱团是因为中国人正卷入一场战争而俄国人正几乎要陷入一场战争”。
肯尼迪敏锐地抓住了中苏关系变化的关键所在:即来自外部的特别是美国的压力是影响中苏战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肯尼迪也注意到印度倒向苏联的倾向,因此,肯尼迪明确表态要对新德里提供“军事援助”,并敦促印度人要对苏联人“更加强硬”。
肯尼迪对印度大使说道:“当中国人蜂拥而至并停在前门的时候,我不想让他(赫鲁晓夫)从后门溜进来”。在会见前,印度大使向肯尼迪递交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信,在信中尼赫鲁请求美国紧急提供军事装备。
但出于对不结盟政策的坚持,尼赫鲁指示印度大使转告肯尼迪在回信中不要提及军事援助,并称印度仍在考虑以现金购买美国武器。10月29日,尼赫鲁接见美国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斯,正式向美提出军事援助的请求。
10月30日,美国五角大楼收到了印度目前所需武器的清单。与此同时,印度也积极向其他国家请求军事援助,并得到了英国、加拿大、西德和埃及的应允。
11月3日,美国向印度提供的首批包括武器弹药和通讯装备的紧急军事援助抵达印度。与此同时,美英在伦敦建立联合工作组,跟踪研究中印边界局势并对两国的对印政策进行评估。至11月中旬,伦敦工作组建议美英为印度提供价值超过一亿美元军事援助,为印度装备五个山 地 师。
11月16日,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凯森在给肯尼迪的备忘录中指出,伦敦工作组提出的初步方案其目的旨在帮助印度抵御中国的进攻,同时,要以此继续对印度施压,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11月16日起,中印边境战争进入第二阶段,中国边防部队在西山口、帮拉迪和瓦弄等地区先后粉碎印军的军事进攻,迅速清除了16处印军据点
并且一直追击到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附近。经过两个阶段自卫反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共歼灭印军两个旅和三个旅的大部,毙、伤、俘准将旅长豪尔·辛格和达尔维以下官兵8700余人。
面对印军的全面溃败和中国军队大幅推进的可能,尼赫鲁大惊失色,震惊之余急忙两次致信肯尼迪,吁请美国紧急向印度派遣12个中队的超音速战斗机,并提供先进的雷达和通讯设备。尼赫鲁并请求美国提供两个中队的C-47中程轰炸机,以对中国境内基地和机场进行轰炸。
11月19日,肯尼迪在白宫召集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专门就中印冲突开会,决定派助理国务卿哈里曼率领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赴印,就印度军援需求的种类、数量和援助方式与印方展开磋商并进行评估,同时派遣C-130大型运输机,帮助印度抢运增援部队与物资。
与此同时,美国也积极在印巴之间斡旋,敦促巴基斯坦向印度保证不会乘机对印发难。不过,此时中国也积极做巴基斯坦的工作,以图尽快解决中巴边界问题,改善与巴基斯坦关系,从而从地缘战略上对印度施加压力。
1962年10月,中国与巴基斯坦边界谈判正式开始,12月两国即就边界的位置和走向达成原则协议。中巴边界问题的解决使印度陷入被动,为中国在对印军事和外交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虽然肯尼迪担心中苏几乎同时卷入“古巴导弹危机”与中印边境冲突这两场危机会使中苏在面临战略压力时重新“抱成一团”。
但事实上这两场危机的同时发生恰恰激化而不是缓和了中苏分歧。尽管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试图争取中国支持,并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采取支持中国的表态,但由于中国对苏联的战略信任已经非常薄弱,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伸来的橄榄枝是别有用心,是“实用主义”。
在短暂的貌合神离之后,很快中苏争论复起并再次激化。1962年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即停止战争,重开谈判,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并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
在1962年11月7日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详细列举了中国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指责苏方在中印边境争议中的态度是“表面中立,实质上是支持印度”。
章汉夫愤愤不平的指出赫鲁晓夫在10月25日的时候公开支持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的立场并宣称“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但仅仅五天之后就自食其言,“又不谈麦克马洪线非法了,三项建议也不谈了,只讲什么‘友好’,‘停火’,‘和平谈判’,‘停火谈判’等等”。
章汉夫道:“为什么25日到31日,只有五天又变了呢?那是因为25日古巴形势很紧张”。22日肯尼迪宣布实行“隔离”政策,对古巴外海实行封锁,并威胁使用武力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
“赫鲁晓夫害怕了,怕得要死。故在此时赫鲁晓夫骗我一下,真是实用主义”。章汉夫接着道:“31日他在古巴问题上投降了,反过来就不讲‘麦克马洪线’了,不讲支持我三项建议,本质东西又出来了。
对修正主义不能看他说几句好话,就好一点,好点,过不了三天,这次是七天,又变了,完全是实用主义,早晚行情不同,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 样”。
章汉夫指出仅在1960年5月到1962年5月间,苏联就同印度交货并接受订货,供给飞机94架,喷漆引擎6台
其中:安1212运输机32架,米格直升机26架,米格21战斗机12架,伊尔14运输机24架。“最近还要交货,源源不绝,还给印度山地作战的被服、帐篷,运输机、直升机都给了。还建设工厂制造飞机、坦克”;“口唱‘中立’,实际上支持印度。政治上捧、支持,物质上援助、给飞机,愈冲突紧他愈要去访问。边界上我打下三架飞机,其中有一架是苏联的”。
最后,章汉夫下了结论:修正主义“完全是实用主义,早晚行情不同,今天 是 这 样,明 天 是 那 样。……他对美国要搞,需要加码时,需要我们时,对你‘好’一点,不要时,倒头来打你一巴掌”。
事实上,对于苏联对印的军事援助,中国一直心怀不满。在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前夕,周恩来曾于10月8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与其严正交涉印军使用苏制运输飞机和苏制M4直升机在中印边界运送军需事,指出:“印度使用苏制飞机进行挑衅,对我们前方战士有影响。”
不过,章汉夫对赫鲁晓夫的指责倒未必完全公允。事实上,即使是美国官员也注意到,实际上,中印边境争端从一开始就使莫斯科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冲突的一方是莫斯科“主要的盟友”,另一方则是其号称不结盟运动中“最伟大的朋友”。
当印度新任驻苏联大使考尔(T.N.Kaul)11月9日拜会赫鲁晓夫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对于印度人实际上颇为不耐烦。直到11月24日,中苏分歧重新加剧之后,赫鲁晓夫才对印度的援助请求做出了积极回应。
随着美苏围绕古巴问题关系趋紧,赫鲁晓夫也曾试图做出友好姿态,拉拢中国。10月13日,奉调回国的驻苏联大使刘晓辞行拜会赫鲁晓夫。
在谈话中,赫鲁晓夫特意对卖米格飞机给印度一事做了解释,辩称:“我们认为卖给印度飞机对我们有利。我们不卖,英美帝国主义就要卖。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印度的影响增加了”,“我们卖给印度几架飞机是不会使中印力量对比就变得有利于印度了”,并称“我们不认为,现在我们两国应当组成一个共同反对印度的战线。这会使它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而这恰合印度反动派的心意”。
针对数天前周恩来会见契尔沃年科时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谈话,赫鲁晓夫特意强调“我和我的同志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意见”,批评印度的立场是“不正确的”,并表示希望中印能“早日解决争端”。
此外,赫鲁晓夫还详细地从苏联角度谈了美苏围绕古巴问题的交锋,宣称:古巴问题是“我们在美国人身上插了一把刀”,“美国人只好吞下去”。
此时,古巴导弹危机尚未爆发,赫鲁晓夫在谈话中也刻意没有提及苏联在古巴部署弹道导弹之事。第二天,赫鲁晓夫和全体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为刘晓举行饯别午宴。在宴会上,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做了长篇讲话。
在讲话中,赫鲁晓夫“突出表白苏共对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和立场”,称“一九五八年以前两党两国关系好到无法形容的程度,现在应该把分歧和争论一笔勾销。
如果中国兄弟理解并同意我们的意见,我方将尽一切努力采取措施改善两国关系”。赫鲁晓夫还对刘晓表示:“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这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致立场。如果不幸发生反对中国的战争,我们将同中国站在一起。
过去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公开宣布过这一点,如果你们意愿的话,我们明天还可以重申这一声明。”赫鲁 晓 夫 解 释 道:苏联“仅仅出于策略的考虑,才没有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公开声明”,因为“不能把印度推到美国那一边去”。
赫鲁晓夫表示支持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的立场,并称,如果“苏联处在中国的地位,也要采取同样的措施”。赫鲁晓夫还表示,苏联“应该暂缓向印度出售米格21型飞机”。苏共中央主席团为刘晓举行的送别午宴持续了近五小时之久,“气氛热情友好”。
根据王泰平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记载,赫鲁晓夫在这次宴会上还说道苏联应古巴要求,在古巴部署了中程弹道导弹,以维护古巴安全,并称希望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也采取措施。次日,米高扬又约见刘晓,详细通报有关“古巴导弹危机”情况。
但这一观点遭到历史学者戴超武的质疑。戴超武引 用 解 密 的 前 苏 联 档案,指出均未发现赫鲁晓夫提到在古巴部署中程弹道导弹之事。
根据笔者在外交部档案馆所看到的解密档案,在10月14日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送别刘晓大使的午宴中,赫鲁晓夫并没有提及古巴问题。
倒是在前一天10月13日刘晓辞行拜会时,赫鲁晓夫提及了古巴问题,但他刻意没有提及苏联在古巴部署弹道导弹事。
一种可能是王泰平的记载误把刘晓辞行拜会赫鲁晓夫和赫鲁晓夫设午宴送别刘晓混淆在一起,并对赫鲁晓夫的表态做了误读。10月25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支持中国政府10月24日声明中提出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并称:
“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从来都没有得到中国的承认”。但是中方对赫鲁晓夫并不信任,认为苏方不过是想摆脱“因偏袒印度所处的被动局面”,而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要求也并未做出任何反应。
直到中苏分歧重新加剧之后,赫鲁晓夫才于11月24日对印度的援助请求做出了积极回应。在和印度驻苏联大使的第二次会面中,赫鲁晓夫毫不讳言对中国的批评态度,而向印度提供军援显然有教训中国的意思在里面。
这时,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中国领导层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到1962年底,中国领导人纷纷强调“要充分认识到两个国家的性质变了。
过去都是马列主义,以马列主义对马列主义”,但现在苏联“对我国是一套武装叛乱、颠覆活动,无视我国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这是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根本不同的路线,是对抗性矛盾,只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 处 理”。
表 面 上,中 苏 “闷 头 打 官 司”,没 有 “在 报 上 宣 布 公 开斗”,但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国与“现代修正主义斗争越来越尖锐,中苏分歧实际已经公开化”。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进一步解释道:
“我们要明确地认清,赫鲁晓夫是叛徒,不是无产阶级,不要向他交底。对他不能排除出反美统一战线,但又不能当作阶级兄弟”
“对赫鲁晓夫来说,我们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不能的,但利用他与美帝的矛盾,拉着他,是个策略。对苏联人民、国家,我们是认真的团结,不是 策 略;对 赫 鲁 晓 夫 是 策 略,拉 住 他,利用他”。
美国也注意到,苏联在中印边境争端中采取“中立”态度一定程度上是与中国“分歧的结果”,但同时也“导致了(中苏)更大的裂痕”。
美国对印度采取的军援姿态则进一步“加剧”了苏联的两难困境。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室主任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在给国务卿腊斯克的备忘录里就做了如下分析:
莫斯科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力图“避免”在北京和新德里之间被迫“做出最终选择”———这突出表现在莫斯科在向印度交运后者订购的米格-21型战斗机时的犹豫不决———从而试图“找到把印度人和中国人拉到谈判桌上的途径”并使自己跳出这样的两难困境。
希尔斯曼建议:美国应尽量“使莫斯科被钉在这个两难困境的利角上不得动弹”,从而使其与新德里和北京的“关系恶化”。这是对美国战略和安全利益最有利的对策。
中苏在古巴问题和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很快出现的争执使得华盛顿的决策者不仅大大松了一口气,而且甚至还可能暗自窃喜。1962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oergy Bundy)就在给肯尼迪总统的简报里指出:
随着北京对莫斯科“发动日益尖锐的攻击”,指责后者在古巴问题上先是冒险主义,然后是投降主义,并且在中印边境冲突未能对中国提供“明确的支持”,古巴和中印边境的危机已经“使得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几乎到了破裂的边缘”。
肯尼迪政府初期,美国情报系统通过西藏叛乱人员所获得中国军方的秘密文件,即所谓的“西藏文件”(The Tibatan Papers)。这些情报显示,粮食短缺危机已经使影响到“军事机构”。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考恩(John McCone)得出结论,认为美国需要“极大地降低”对中国军事力量的估计。国务院情研室主任希尔斯曼也认为,由于国内自然灾害和经济衰退的影响,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将处于战略上的防御态势。
截至1961年11月,肯尼迪已从其核心外交政策顾问得知“由于粮食短缺,中国总体战略进攻的态势已经基本上被阻滞”,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将处于战略守势。
而在1962年春夏的台海危机中,中美相互试探各自战略意图,中国发现美国没有支持蒋介石反攻的意图,美 国 也 发 现中 国 大 陆 没 有 用 武 力 夺 取 金 门 等 外 岛 的 计划。
1962年台海危机的顺利解决,对于中国力量由于经济困难受到削弱的认知,加上美国在东南亚拥有的军事优势,使得美国决策者对远东形势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战略乐观主义”。1962年7月18日,美国驻香港总领馆在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认为中国的经济困境将“阻碍”北京“采取大规模的公开军事冒险”。
在致肯尼迪军事特别顾问马科斯韦尔·D.泰勒(Maxwell D.Taylor)上将的信中,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主任沃尔特·W.罗斯托(Walt W.Rostow)对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的观点表示赞同并指出“很显然共产党中国在60年代不可能成为工业和军事大国”。罗斯托预测道:“在可预计的将来,我们不会在东南亚面临历史上曾有的那种压力,从而使我们产生注定要失去这一区域的宿命主义”。
罗斯托相信,中国陷入困境的事实“应当增强我们追求在无限期的未来期限内防止共产党人夺取南越、泰国及老挝这一政策的意愿;并且我们应当带着内在的信心来追求这一政策”。
然而,随着中印边境冲突的发生,罗斯托所宣扬的这种“战略乐观主义”被迅速粉碎。中印边境冲突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对于中国力量及北京所构成威胁的评估。具体来讲,中印边境冲突的爆发及其结局急剧地改变了美国对于中国战略意图及能力的认知与信念。
中国在这场边界战争中展现出来的军事与外交技巧及复杂性使美国领导人深感震惊。肯尼迪政府意识到,中国已经从暂时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正在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敌人”,而且将是“具备娴熟政治技巧”的对手。
美国决策者坦承,中印边境战争是中国统合军事、政治和心理手段来遂行服从于政治目的之下的一场“单一的、有限的、有纪律的和受掌控”的军事行动的杰作。
从军事上来看,中国克服后勤、运输等困难,在喜马拉雅山这一号称世界上最困难的地形令人信服地完败印度军队。
从宣传和政治上来看,中国娴熟利用印度方面的挑衅行为,相当程度上成功地摆脱了侵略的指控;并且整个冲突过程中,中国始终保持“政治主动”,在每一个政治敏感的转折点呼吁停火和谈判,从而成功地将对于拒绝和谈的指责转移到印度身上。
从战略上来看,中国对印度的军事和政治胜利羞辱了印度这一中国亚洲领导地位的主要竞争对手,并在历史上首次将中国权力与影响投射到印度次大陆。
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前,美国决策者从未感到美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战略和安全利益如此强烈地受到中国的威胁。美国国务院的高官担心中国的力量将被“拓展到印度平原”,并且中国将通过排挤印度“增加”其在尼泊尔、锡金与不丹的“权势与影响”。
1962年11月7日,希尔斯曼及其下属的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室为国务卿腊斯克准备了一份报告,详细分析了中印边界冲突的战略影响。这份报告的有关观点随后得到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有力支持并被迅速转呈给肯尼迪总统。
这份报告对中国之所以在中印边界采取攻势的长期战略和政治目标,以及短期的军事与安全考虑都做了详尽的分析,认为北京的最低目标是“巩固其对藏控制并且保卫其不受渗透与颠覆”。
为确保实现这一最低目标,北京就必须首先控制争议中的拉达克(即我阿克赛钦)地区,以便能顺利完成通过此区域连接新疆和西藏的要道。
斯尔斯曼认为,在“西藏安全”这一层最基本的考虑之外,北京战略行为的深层动机是更加重要的战略和政治目标,即与“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位置的设想”有关。
首先,印度在第三世界寻求领导地位的傲慢姿态引起了广泛的怨恨,这种怨恨恰恰可以被中国所利用。
其次,印度的所谓的“前进战略”及在中印边境的不断挑衅,则为中国提供了在不结盟国家眼中证明其军事行动合理性的借口。
一场军事失败将重重羞辱印度,使印度不发达国家“样板”的自我吹嘘不攻自灭,并且大大削弱印度寻求第三世界领导地位的努力。
更为重要的是,斯尔斯曼认为,印度的失败将证明喜马拉雅山和西藏高原都将不再是可以把印度次大陆与欧亚大陆隔绝开来的“无法通行的军事屏障”,也不将再是“中国权力前进基地”的阻障。
希尔斯曼指出:北京已经令人信服的证明中国现在是印度次大陆“需要被认可的一支力量”,“世界上不再有任何人能够言称印度次大陆而不考虑中国的利益及其力量的事实”。
尽管希尔斯曼并不认为中国“试图征服印度”或者“将其领土控制扩展到喜马拉雅山麓的群山与丛林之中”,但他却担心北京可以通过“政治颠覆、武器和游击战干部的渗透,以及在山居民众中煽动叛乱”等手段,轻而易举地将其影响扩展到南亚次大陆并实现其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特别是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扩张主义野心”。
因此,希尔斯曼得出结论,认为“印度次大陆的安全攸关美国利益”,“中国支配喜马拉雅山内侧的威胁”应成为华盛顿的“直接担忧。”
这一报告建议,为使这一区域免受北京的“政治—军事渗透”威胁,美国应当寻求“持续加强印度的防御位置并通过游击战破坏中国运输线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