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的「BFI经典电影细读」丛书中的《八部半》。
我拍了这部电影,这样我就用不着感到羞愧了。但是确实有「某个人或者某件事」促使费里尼迫于羞愧感而拍摄《八部半》,那正是对这即将介入的某个人或者某件事的恐惧。
他没有将羞耻感抛到身后,反而需要靠这种羞耻感来逼迫自己完成这部电影(「我不能面对忠实的影迷们」)。就像我们看到的,因为羞耻而拍摄这部电影跟在拍摄这部电影时感到羞耻,这两者的差别不是那么大。

费里尼做出决定将主角刻画成跟他一样的导演后,这种斗争和崩溃感并未消失。它一直持续在电影之中,影片中的主人公同样对他的化身感到惊慌。
《八部半》开始的时候,导演的化身还没有被观众认可,一切就像是一个创世神话,里面充斥着原始的涌动,主创的形态还不能确定——纠结在多种可能的形式之间。这种模糊不定的存在,这个「最初的圭多」,占据了电影著名的开场镜头。

「他」(能确定的只有这些)的轮廓首次出现在一辆被围得水泄不通的汽车的方向盘后面。他瘦弱的外形没入了寂静之中,就像困于瓶颈,这只会更让我们感觉电影正要开始,它还没有真正开始。
突然,拥塞的不仅仅是外面的车了。毒气在车内愈加浓烈,好像通风系统把周围所有汽车的废气都集中到车内。仪表板的按键一点用都没有,就在他最需要新鲜空气的时候,车门和车窗都打不开了。

很快我们就得知这个场景叫做「GA的噩梦」(GA是电影男主角的姓名缩写),这个标题很好地掩盖了影片叙述上的不连贯。因为我们第一遍看的时候没法知道这就是场噩梦,我们也没法知道它是属于GA还是属于其他「人」。
决定这个段落的不是一个「角色」,不是具体人物的叙事样貌,而是一个「形象」,一个隐匿者占据的位置。这个形象的暧昧性有着双重含义:视觉上,我们没有正面看到也没完全看清楚;社会意义上,他也不是我们可以认出来的某个人。
就像是廉价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最初的圭多忽隐忽现,不受(普鲁斯特所言的)「特定的专制」的影响。「特定的专制」会管控角色的传统呈现,还会规定跟他置身同一场景的「人物」。

尽管其他人都是匿名的,却有着格外鲜明的中年面孔,脸上带有各自阶层的烙印,我们不无道理地称这些人为「角色」。他们引人注目,过分夸张的特征就等同于奥斯丁或狄更斯小说中那些所谓扁平人物身上最典型的特殊习性。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司机和旅客的故事,但是因为他们的面孔,他们已经以第三人称存在于传统叙事形式中了。
拍了《八部半》之后,费里尼会因为这些面孔而出名。可是,有必要认识到标志性的「费里尼面孔」之外的社会环境——成就人物社会性的环境。这些社会环境都高度凝缩于这些面孔中。

在以明星为根基的电影业,费里尼拍的那些面孔,我们并不觉得好看。它们之所以令人厌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缺乏青春和美丽,或是特征过于夸张,更是因为它们强调坚持「我们自己的面孔」也是如此(自然,因为我们自己没法露脸,我们能有的当然只是他们的面孔!)。这些面孔既是可耻的,又是无耻的。
它们是可耻的,因为它们太形象生动了,过多地透露了面孔主人的灵魂;脸上的线条好像是由一个无情的漫画家勾画的——正如GA在情人的眼睛上画出妓女般的眉毛。它们又是无耻的,因为这些面孔上充满顽固甚至是傲慢;它们透射出面孔主人恬不知耻、尖酸刻薄的个性。

可是,不管是令人尴尬还是厚颜无耻,它们从不改变表情;画面是静止的,人物是僵硬的。似乎我们作为第三人称的社会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屈服于这种死后的麻痹状态;在车厢这样假设的属于个人的灵魂空间里,我们坐着,摆出的姿势既可能出现在驾照照片上,也可能出现在死亡报告的照片上。
最初的圭多没有这些面孔令人羞愧的特征。影片中,相衬于他的人物地位,他是从后面被拍摄的;他的身体要么只是碎片化地呈现,要么就是以晃动的,仅仅是暗示性的侧影来呈现。
尽管很多人都死盯着他看,但是我们不清楚他是否真的被看到,如果他确实被看到了,他看上去又如何?并没有什么反打镜头来展现这些面孔所凝视的对象,这一缺失并没有赋予主人公更多权力。

这一缺失并不意味着「主人公看到或未被看到」(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主人公、导演、观众),而是意味着「主人公在被看着,但是未被认出来」(处于社会性死亡地位)。这种未被识别也解释了为什么其他司机和乘客尽管看到主人公十分沮丧,却不愿意帮助他。
相反,在他们凝视的专注度和他被毁灭的威胁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隐约的关联。如果说其他人由于面孔僵硬而看起来像活死人的话,最初的圭多则像不死者:一个被驱逐的吸血鬼,社会这面镜子不能也不愿映出他的模样。

就像他的车一样,他被卡在两种难以忍受的命运之间——角色的社会固定性以及人物的社会边缘性——最初的圭多突然超越了这种尴尬的两难境地,变形成为第三种存在:一个神,逃离了他的汽车,飞上了天。在这场交通瘫痪的「活人画」(tableau)中,他成了唯一一辆真正意义上的「自动车」。
我们看见他从高架桥下飘出来,腾空在汽车和电线之上;我们看见他在太阳和云层中漂浮;最后,我们只看见了太阳和云层,似乎他已经变成一个经典的神的形象。查尔斯·阿弗伦(Charles Affron)认为云的镜头用的就是GA的视角;为了更契合GA神圣升天的逻辑,我把这个镜头理解为,视角的消失正显示了事物本身的客观性。
多么像一个神啊!1963年,GA的升空自然让人想起费里尼之前那部电影《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1959)著名的开场画面,耶稣的雕像被直升机空运过罗马。

石像形式的耶稣必须依靠现代科技来移动,最初的圭多却是靠自己的力量飞升;那座耶稣雕像只能俯瞰那些不够庄重的泳装美女,或者仰望那些玩世不恭的美男跟她们调情,而最初的圭多则升至这样的境地:他在下面遭遇的毒气都化为纯净的云层。
这样一个在视觉和社会地位上都处于边缘地位的人物身上展现出来的非人性,已经被一种更高等的非人性所取代了,这种非人性属于只能以其创造物来显现其形的神。

他轻盈的身体本可升腾入云且消融其间,但现在却又恢复实体了,他的脚踝上系着一根绳子。就像一个风筝一样,它可能会被拉回地面;一旦被拉回来,它马上就会获得铅坠般的重力。
「下来吧,再别上去了。」在海滩上拉着绳子的人说道;如果按照字面翻译的话,就是:「下来吧,早晚得下来。」最初的圭多脑袋离开云层,他掉落下来,落入了确定性,也同时落入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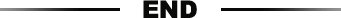
往期精彩内容
塔可夫斯基和费里尼都喜欢用他当编剧
费里尼的《八部半》过时了吗?
刚刚出炉的史上最伟大的100部电影排行榜,《异形》这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