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浪漫主义画家John Martin这幅作品(1840)再现了古以色列开国大元帅约书亚在与基遍人作战之际命令日月停转的史诗场面。——利未集团对被地球土著视若神明的星辰天体的大不敬及其搅动这个星球的鸿浩志可见一斑。

1
.
古犹太人有十二个支派,利未人是其中一支,但是,利未人并不是犹太人,而是外族人,他们凝聚在一起,构成一个
神秘的宗教—政治集团
,这个集团肩负神秘使命,注定搅动整个星球。
2
.
韦伯在《古犹太教》提到一则非常古老的传说,认为
利未集团
是摩西的私人保镖,他们支持摩西对抗民族内部不顺从的敌对势力,并在一场亲族之间的浴血内战中确保了摩西压倒性的地位。无独有偶,犹太裔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对本族的精神体验结构保有浓烈的兴趣,在其《摩西与一神教》中,他做一番考证,得出结论说,利未集团是摩西从埃及招揽的卫队,作用类似罗马执政官的扈从,后者手持木棒,端头帮着一把斧头,罗马人称这种武器为“法西斯”,也是我们今人说的“法西斯”的来源。
3
.
和手持“法西斯”的罗马扈从相比,利未集团在数量、权威等所有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被摩西列入犹太民族花名册中,成为十二支派中的一派,地位很特殊,
它们放弃土地要求,换取了祭司权能
,也就是说,它不占取土地,但对整个民族施行精神统治,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无空间(
spaceless
)式的权力存在,
nowhere but everywhere
,这是其精神威力的要害所在。
4
.
在旷野游牧时期,利未集团起到了
发动机和先锋队
的作用,驱赶着犹太人在新月沃土上奔逃、劫掠、祭神、建国。利未集团及其精神律法可以说是犹太沙漠游牧民族的精魂,
它永不定居,永远在路上
。可是,草肥水美的平原绿洲实在是巨大的诱惑,利未集团带领犹太民族最终在一块据说流着蜜和奶的地方定居下来,初心远去,并慢慢在绿洲洼地里腐烂,最终以亡国收场,但利未精神并没有死去。
5
.
利未集团的神经中枢是它深入骨髓的游牧基因,可以称之为“贝都因人”的基因,它决定了利未集团
把世界当作牧场
的这个特殊世界图景,它使犹太人以世界牧人自居,在它们的驱赶下,万物生灵匍匐在大地上,静默无声地运动着。在研究霍布斯的时候,笔者曾经检索到一副犹太画家的作品,绘制于上世纪
80
年代,题名《利维坦》(见下图),感受一下,其中深意无需多谈,一切尽在不言中。

▲“有经民族”就是这么气定神闲地驱动世界史吗?
6
.
“牧羊人—牧场”这个游牧格局是利未集团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正统理论参照系。这个游牧框架后来升级成一种
历史神学
,主导着所谓的“亚伯拉罕天经崇拜体系”。这个沙漠一神教史观并没有局限于内亚沙漠地区,而是道成肉身,进入世界各个角落,并在最真实的意义上驱动了这个曾经沉寂的星球。
7
.
利未集团进入“蜜汁迦南”后,就演化出了一个堕落形态,即定居的利未集团,他们在保留既有精神祭司统治的同时,开始着手声索土地法权。然而,他们在占取土地的同时,并没有转型改制,采纳地球土著的和平定居秩序,而是圈占良田,继续游牧。圈地游牧,就是竭泽而渔的汲取和劫掠,它催生出
东方专制秩序的最劣版本
。这是“定居型游牧秩序”的秘密逻辑。定居(沃土)与游牧(沙漠)
在元素层面上的水火不容
决定了“定居型游牧秩序”的运行轨道实际上是一条通向自杀的不归路,这种秩序本质上是自我摧毁型的(self-defeating),这和犹太人
“自我憎恨”
的精神体验结构是一脉相承的。二次大战前“柏林犹太学术院”的创始人——犹太民族精神的代言人——罗院长曾尖刻地说,反犹的情结是从犹太秩序内部诞生的,最反犹的其实是犹太人自己。
(从很多层面看,柏林犹太学术院等同于华夏文化精英在同时期创办的清华国学院。——阿刻隆河学者按)
8
.
“定居型游牧秩序”之所以是游牧秩序的堕落形态,是因为后者的精髓是牲畜跟着草走,而牧人跟着牲畜走,它是自然秩序的初级版本,类似于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的荒野自由的开放秩序。一种秩序,只要不反自然,其内部就必然蕴含有健康的良种,可以生根发芽,演化出
文明正典
,荒漠中的自然自由就是这样一种秩序,它向所有人自由开放,衍生出
部落式平等竞争的封建国际体制
,其政治等价物介于
卢梭
的自然状态和
霍布斯
的自然状态之间,既有黄金时代部落小共同体的
牧歌元素
,也不乏只能在健全硕壮的躯体上才会展露出来的
尚武美德
。这是一种可称之为在荒野中自然生长出来的
原始的星球占取习惯(
Nomos of the Earth
)
。与此不同,“定居型游牧秩序”是对自由荒野的分割独占和封闭暴政,它中断了原始游牧秩序中的“部落自由”体制,旧制度中自由竞争的部落自然法、万民法和战争法也就被釜底抽薪。这种秩序由羊和狼构成,这里的狼就是从之前的牧羊狗变形而来。这种秩序其实是一种内战,一种秩序的坍塌和无秩序,是从政治状态向战争状态的倒退,维柯
(Giambattista Vico)认为
这就是亡国。
9
.
神圣的敌意
是这种秩序的外交工作的理论基础,正义战争(
圣战
)几乎是它唯一能够采取的战争模式,它永远体会不到
荷马史诗
中那种竞技赛会意义上的贵族战争。在荷马式的战争中,交战双方作为彼此正义的敌人为了荣耀传承和德性的磨砺而有规则地决斗,而在圣战中,人们为嗜血的正义祭坛和致命的最后审判而毁灭妖魔化的敌人。
10
.
狼对羊群的游牧是一种自杀性劫掠,这种秩序成于此,也将于此败亡。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无比悲催和无能的命途并非狼的自愿选择,而实在是“定居型游牧秩序”的内在自杀逻辑驱动的结果,原因上面已经提到,即利未集团的定居导致自由荒漠所承载的
“国际游牧秩序”
解体,继而滑入孤独的穴居人暴政。
11
.
“定居型的游牧秩序”和滥觞于欧洲并奉行于今的以领土国家为单位而构筑的维斯特伐利亚
“国际和平定居体制”
在形态上
是暗合的,这给了利未集团的孤独暴政以国际法理据,这是威斯特伐利亚体制最可悲的地方,也是其创始国始料未及,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
Carl Schmitt)
的观点:诞生于
17
世纪欧洲的这套和平定居体制只适用于欧洲基督教民族,欧洲以外适用难度很大。在欧洲之外,在神秘的东方,尚有大片土地仍被利未集团的
游牧战争法
主宰着。维斯特伐利亚那套欧洲基督教主权君主国之间的平等战争法和源自亚洲沙漠的利未集团的游牧战争法是南辕北辙的。
12
.
利未集团的统治状态(stato)是一种永不止息的战争状态,一种对内游牧战争状态,因此,
利未集团的宪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战争法
,一套或隐或显的战争法框架左右着利未宪法条文和论证。笔者认为,这是利未秩序的最大秘密。如果看不到这个战争法框架,则利未宪法就会衍生出诸多难以索解的矛盾,如果看清这个战争法框架,则所有矛盾都迎刃而解。
13
. 利未集团经营的定居秩序是伪定居秩序,它是征服者为
战败者
量身定制的战后秩序,在本质上是战争秩序的延伸,是利未征服行动的组成部分,它在最极端的程度上证明了罗马史家
塔西佗
的真知灼见:蠢货们眼中的和平只不过是征服者的奴役(
Idque apud imperitoshumanitas vocabatur, quum pars servilitutis esset
.
)。在这种秩序中,那种专属于战争时期的紧急例外状态从来没有取消。利未集团对此拥有清醒意识,他们知道他们处在
永恒的战争
中。
14
. 永恒的战争意识,是利未集团及其所代理的
亚伯拉罕天经联盟
的根本驱动力,由于这个联盟的存在,曾经在宇宙一角沉寂怠惰的
异教地球
开始躁动癫狂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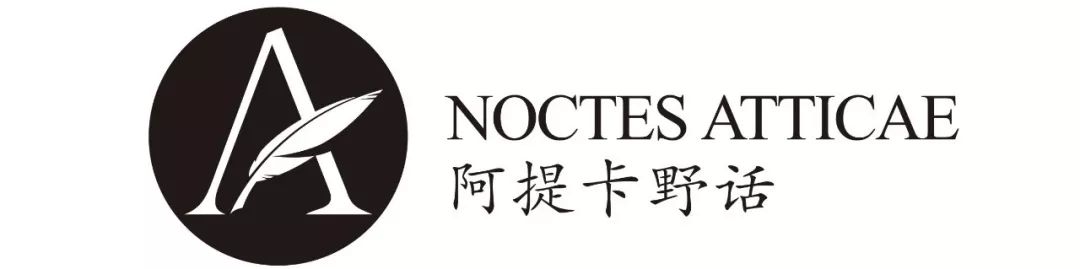

多山的伊庇鲁斯深处,幽寒的阿刻隆河畔,诸世代的观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