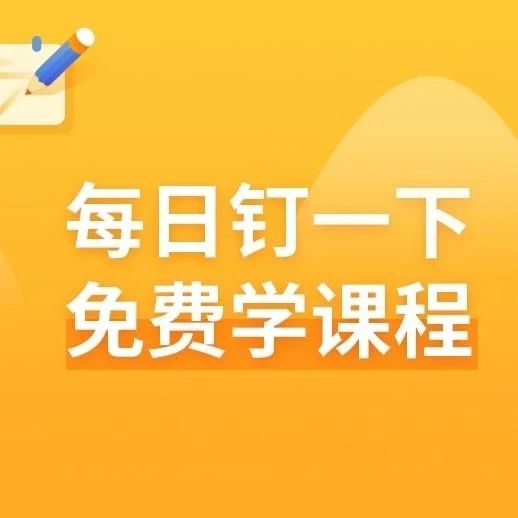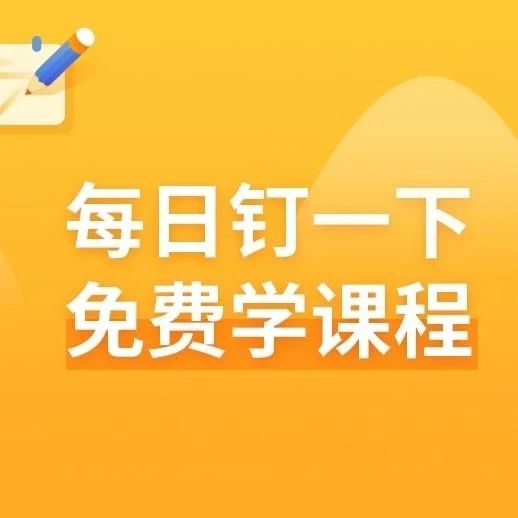2025年是王逊先生诞辰110周年。王逊(1915—1969),著名美术史家、美术理论家,中国现代高等美术史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作为20世纪的重要知识分子和新中国文化建设中罕有的枢纽型人物,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三联书店有着长期关注知识分子与20世纪中国的传统,于今年出版了王逊先生的学术评传《上水船:王逊与现代中国的艺术理想》,希望为更广泛的人文知识界勾勒出这位学者的人生轨迹与思想历程,使其多方面的才华与事功更准确地为读者了解。
为介绍这位“出色的哲学家、美术史学家和历代工艺美术鉴赏家、评论家”(林徽因语),“三联学术通讯”将以“寻找王逊”为主题推送6期内容,从其早期思想、西南联大时期的现代学术积累、重大工艺美术实践、创建共和国的美术史学科体系、美术通史写作,以及对于王逊的寻找、搜集与拼合等六个方面,展现其短暂而波澜壮阔的一生。
今日推送集中于王逊先生的工艺美术活动。抗战胜利后,陈达、费孝通等学者从恢复战前产业、解决经济危机的角度发起“北平特种工艺复兴运动”,王逊受沈从文和韩寿萱影响加入到这项工作中。新中国成立,王逊、林徽因等组建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小组,正式启动了对传统工艺的改造,景泰蓝改造为最早一项。他们把新的设计原则概括为八个字:好看、好用、省工、省料。我们附上《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1951)和《红楼梦与清初工艺美术》(今日二条),可知王逊先生等是如何拒绝了“乾隆品味”,并实现了“一件器物,一眼望过去就产生单纯的完整的明朗的印象”。
* 我们的读者俱乐部正在招募中,详见文末,欢迎加入三联学术的朋友圈!
*选自《上水船:王逊与现代中国的艺术理想》第三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建筑学家吴良镛曾将王逊主持清华文物馆时期(1949—1952年)的工作概括为国徽设计、文物馆创办、振兴工艺美术三项活动。
[1]
前面主要谈了文物馆创办,下面再说说景泰蓝改造和国徽设计。
景泰蓝改造是王逊接手最早的一项工艺美术实践,从他1949年一回到清华就开始了。
为什么要改造景泰蓝呢?景泰蓝是京式特种工艺的代表。前面说到挽救北京特种手工艺,到1949年调查统计,全北京共有特种工艺19种
[2]
,景泰蓝是产值最高、最具代表性的,所以改良传统工艺就从景泰蓝开始。那时的景泰蓝作坊都是个人的,师傅带徒弟那种,规模小,产品质量也上不去。用王逊的话说,最大问题还是在产品设计上:“主要表现在图样方面的循规蹈矩,师守成法,偏向无原则的繁琐工巧”
[3]
,就是说,在图案、形体上都没有创造性。乾隆那时不就追求卷草纹、缠枝莲那些?林徽因批评的“乾隆Taste(品味)”
[4]
——非常规矩,但没什么生命力。
乾隆时代还是最高水平
[5]
,以后越来越差,民国时的景泰蓝说白了就是糊弄。过去宫廷工艺都是不惜工本、穷工极巧的,但民间作坊没那么大的实力,相比已往只能算是粗制滥造,掐丝歪歪斜斜,图案也越来越呆板,更谈不上创新。这些东西主要是卖给老外,国内没有市场,后来老外也不买了,恶性循环,就濒于消亡的边缘。北平解放后,首要任务是恢复发展工商业,解决吃饭问题。
[6]
1949年6月,北平举办了工业品展览会,政府组织银行为特种工艺行业提供大笔贷款
[7]
,又召开座谈会商讨对策
[8]
。同年8月31日,北平市工商局召集“北平特种工艺品产销问题座谈会”,特邀文物、美术方面的专家梁思成、邓以蛰、费孝通、徐悲鸿、林徽因、高庄、吴作人、马衡、韩寿萱、王世襄等30余人举行座谈。会上,先由手工艺作坊主、北平特种手工艺联合会代表、贸易行等代表发言说明困难
[9]
,再请专家建言献策。梁思成、林徽因在会上指出,产品的艺术性与销路应是一致的。徐悲鸿也提出,特种手工艺今后要与美术家联系,改良现今产品的图案。座谈会当场推定由清华大学营建学系、文物陈列室、中国营造学社、特种手工艺联合会、仁立毛纺公司等机构联合组建“北平特种手工艺改良设计研究会”,决定先设计制作出一批改良样品在北大博物馆展出
[10]
,以便征求意见。
[11]
这次座谈会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挽救特种工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靠政府贷款、减免税收等经济上的扶持手段,而要通过美术家的参与,从产品设计入手,提高质量,实现行业自主发展。用王逊的话说就是:“北京的手工艺作为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和作为一个文化艺术的问题,是同样重要的。”
[12]
“(景泰蓝)新图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全面地争取自主的发展的工作。”
[13]
1949年9月开学后,“北平特种手工艺改良设计研究会”正式成立,主要成员有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和清华大学梁思成、邓以蛰、林徽因、王逊、高庄、莫宗江、李宗津。除徐悲鸿外,其他成员都是清华“国徽设计小组”(1949年)、清华文物馆“民俗工艺组”(1950年)和清华营建系“工艺美术教学组”(1951年)的成员。这方面的具体工作由王逊组织实施,包括设计原则的确定、新图案和形体等方面的设计、工艺流程的改进、产品性能质量的提高等,林徽因也扶病参加了其中一些工作。到1949年底,清华小组就设计制作出了第一批样品,当时被报刊称为“北平特种工艺的新生”。
[14]
王逊和清华小组的其他美术家一起讨论,首先明确了景泰蓝新产品的设计理念:“我们的设计总的方向是为了产生新中国的新的人民工艺而努力。这个新的人民工艺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15]
他说,所谓“民族的”应包括两个内涵:一是表现我们民族风格中伟大昂扬、优美健康的一面,而不是因袭晚清以来繁琐杂乱、病弱无力的古怪作风;二是要发展出今天的、能体现新中国精神的新工艺,这是更重要的。所谓“科学的”也包括两点:一是必须从技术和材料出发扬长避短;二是要有实用价值,不能像过去那样只作为陈设器使用。所谓“大众的”,就是要考虑大众的购买力和群众喜好。
在这样的设计理念下,他将景泰蓝新产品的设计原则概括为8个字:好看、好用、省工、省料。这8个字可能源于维特鲁威的“建筑三原则”
[16]
,后成为工艺美术发展的指导方针。
维特鲁威《建筑十书》插图,本书中提出“建筑三原则”:坚固(Soundness)、实用(Utility)、美观(Attractive)
关于“好看”——就是美的表现,他提出不仅要花纹好看、形体好看、颜色好看,更应注意三者之间的协调统一效果,“一眼望过去就产生单纯的、完整的、明朗的印象。”具体说就是先要考虑形体设计,做到健康、挺拔、有气概;其次是花纹,反对一味的细碎繁琐,提出在对古代花纹进行科学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规律,重新组织到新形体上;颜色方面,反对五颜六色、杂乱无章,追求单纯明快的表现。
这里,王逊特别强调单纯、素朴的美感,这是他在长期研究中国美术史的过程中提取出来的重要概念。1948年他写过一篇《几个古代的美感观念》
[17]
,对先秦史籍中的审美观念做语义分析,提取出两个最重要的概念:“素朴”和“对称”。他说西方也讲“对称”,而“素朴”则是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观念,是“中国美感观念中最精粹的一个”。王逊将他的研究用于景泰蓝及其它传统工艺美术改造,在设计中特别注重表现朴素的“单纯美”。
王逊从为清华文物馆征集的《永乐北藏》佛经封面图案整理的《中国锦缎图案》,人民美术出版社1953年版
在重新组织传统花纹元素上,清华设计小组做过很多试验:“最初我们主要借鉴古代铜器花纹,因为我们对于景泰蓝最初只认识到它的庄重端丽,风格上和铜器相似。经过一年来的试验,我们发现景泰蓝的表现能力很强,它可以表现出很多种其它的材料所能表现出的风格。景泰蓝能产生古玉的温润的半透明的效果,也能够有宋瓷的自然活泼、锦缎的富丽,甚至京剧的面谱也给我们启发。我们曾利用过建筑彩画的手法、战国金银错的手法、唐宋以来乌木或黑漆镶嵌的手法。尤其今春,敦煌文物展览开幕以来,敦煌艺术宝库的丰富内容,更供给我们大批材料……”
如前所述,“好用”是提高新产品的实用性,也是为了促进“大众化”。过去景泰蓝几乎没有实用性,国内老百姓一般不会购买,即便是外销,老外也要求实用,比如景泰蓝盒子,能盛放邮票、文具、香烟等,就更受欢迎。所以王逊他们设计时就“尽量设计小件而有用的东西”,开发了台灯、烟具和能盛放小件零散物品的罐盒等。“省工”主要是从工序上加以改进,传统景泰蓝制作有十几道工序,科学总结和简化工序是必要的。“省料”是开发新的原材料替代品,节约成本又不影响效果。所谓“改造景泰蓝”,主要包括以上这些工作。
[18]
在这个过程中,王逊特别强调了解材料性能和工艺流程的重要性,他指出:“材料性能与实用目的密切结合应该是被当作工艺美术的基本原则。”
[19]
景泰蓝改进实验初步成功后,1950年4月,在清华文物馆筹委会主办的“手工艺展览”中展出了新样品,受到观众喜爱和好评。在此基础上,清华营建系成立了对外开展合作的“服务部”,这时新成立的“北京市特种工艺公司”
[20]
找到他们,委托他们设计景泰蓝新图样和改良图案,王逊与林徽因、高庄、莫宗江、李宗津几位美术家深入生产一线调查研究,又设计出一批景泰蓝新图样,在工艺上也有所突破,使景泰蓝的改进工作得以顺利进行。1951年4月,《人民画报》报道《中国特种工艺品——珐琅和地毯》
[21]
,刊出清华营建系改良设计的景泰蓝台灯、烟具、和平鸽盘等图片。同年5月19日,王逊代表清华大学营建系在北京特种工艺专业会议上做了景泰蓝设计总结报告
[22]
,报告中总结的成功经验成为工艺美术发展的指导意见。这天会上,北京市特种工艺公司与清华营建系合作组建的“国营特艺实验厂”正式成立。这个厂设在崇文门外喜鹊胡同3号,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福开森在北平的寓所,最早是清代一位总督的府邸
[23]
,庭院宽敞,花木扶疏,极富文化气息。特艺工厂成立后,一方面作为清华师生的实习工厂,一方面又是北京市工艺美术行业改造的示范点,承担了“亚太和平会议”等国礼设计制作任务。
[24]
1958年“特艺实验厂”并入北京珐琅厂
[25]
,是今天珐琅厂的前身之一。特艺实验厂的产品一出来,国外订单就来了,带动了出口,特别是当时正处在抗美援朝期间,新中国刚成立,国际上经济封锁,国内工农业基础极其薄弱,在重重困难下,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外汇,是当时经济方面很成功的一项工作。
[1] 吴良镛:《〈王逊学术文集〉序》。
[2] 194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冯仲撰写的《北平特种手工业恢复与发展的一些问题》,指出北平特种手工业有地毯、骨器、象牙、挑补花、雕漆、刺绣、绒纸花、烧瓷、珐琅、玉器、镶嵌、银蓝、花丝、料器、铜锡器、玩具、宫灯、玉树、铁花等19种。后经王逊调查研究,认为有14种,见《工艺美术的基本问题》。
[3] 《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光明日报》1951年8月13日;《文集》第三卷。
[4] 据清华建筑系关肇邺回忆,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关肇邺有一次把浮雕的线条画得太柔弱了,林徽因看了说,这是乾隆taste(品味),怎能表现我们的英雄?关肇邺也用玩笑的口吻说,如果让我自己来画,我只能画光绪taste了(意即更“俗气”一点)。”鲍安琪:《1953:“太太的客厅”的最后时光》,《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11月总第970期。
[5] 关于乾隆作风,王逊认为:“乾隆时代的景泰蓝,是只宜于近看的,因为唯有拿在手中仔细端详才能看出丝工的精细。但在配色上,不调和的居绝大一部分。丝工的精细是景泰蓝唯一可以值得欣赏的。”一年总结
“十八世纪以后的景泰蓝曾表现了今不如古的现象……景泰蓝工艺曾经出现了一种表面上热闹,实际是繁缛、琐碎、杂乱的庸俗风格。那些人似乎在追求乾隆时代的一些特点,但在事实上,与乾隆时代优秀匠师们的工致繁丽、谨严精确的做工,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景泰蓝工艺》,《新观察》1954年第1期;《文集》第三卷。
[6] 1949年1月6日,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在接管北平的干部会上说:“我们进城以后,除了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的政权以外,必须抓工商业……还有很多手工业者,如不好好组织,他就没有饭吃。”《掌握党的基本政策,做好入城后的工作》,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北京出版社,1993年。
[7] 北平工业品展览会1949年6月6日—23日在中山公园举办,其间中国银行提供了总额1300万元的贷款。为打开销路,还组织了订货会和海外巡展。李苍彦、王琪主编:《当代北京工艺美术大事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
[8] 见座谈会报道:《北平特种手工艺到何处去》,《进步日报》1949年6月7日。
[9] 《马衡日记》,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10] 这一展览后在清华大学举办。
[11] 李苍彦:《北京工艺美术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18年。
[12] 《景泰蓝工艺》。
[13] 《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
[14] 1949年11月17日《大公报》(上海版)刊发谭文瑞文章《北京特种手工艺的新生》,介绍清华教师对景泰蓝等传统工艺的改进工作。
[15] 《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
[16] 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在《建筑十书》中提出建筑三原则:“实用、坚固、美观”。[古罗马]维特鲁威著、高履泰译:《建筑十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按,前苏联据此提出“适用、坚固、美观”。1949年夏,朱德对中直修办处指示:我们的建筑物只能是适用、坚固、经济,去掉了“美观”。1950年代梁思成提出新的建筑三原则:“适用、经济、美观”。梁思成:《从“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谈到传统与革新》,《建筑学报》1959年第6期。
[17] 《几个古代的美感观念》,《益世报·文学周刊》1948年10月25日第116期;《文集》第二卷。
[18] 关于清华改造景泰蓝的工作,王逊说主要是“新图样设计和改良图案”。。
[19] 《景泰蓝工艺》。
[20] 1950年6月,国营北京特种工艺公司成立,主要从事景泰蓝工艺改造和生产销售。
[21] 《人民画报》1951年4月号(总第10期)。
[22] 《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
[23] 参见[美]聂婷(Lara Nieting):《福开森与中国艺术》。
[24] 1952年10月2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1949年后中国政府举办的第一个国际会议。同日,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访华,林徽因、常沙娜等为这两个国际交流活动设计了景泰蓝礼品。
[25] 北京珐琅厂成立于1956年1月,由42家私营作坊合并成立。
*原刊《光明日报》1951年8月13日,署名“清华大学营建系”。发表时文末附注:此文系清华大学营建系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在北京特种工艺专业会议上报告的摘要
北京特种工艺(包括景泰蓝、陶瓷、雕漆、挑补花、地毯、象牙玉石雕刻、绒绢纸花、料器等十余种行业)在过去一向是受压迫行业的艺术。
在经济上先是仰赖封建阶级的“恩赐”,后来则呻吟在中间商人、买办,和帝国主义“洋商”的剥削下,勉强维持。
作为一种艺术活动,它们也是被压迫的、受尽屈辱的。这主要表现在图样方面的循规蹈矩,师守成法,偏向无原则的繁琐工巧。——工匠师傅们虽然尽了最大努力制作出一些高度精致工细的作品,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发挥出他们真正的创造力。
北京特种工艺风格繁琐呆板的原因是北京特种工艺在满清时代是用来装点少数封建贵族的生活的,是为了迎合日趋没落的封建贵族的堕落思想和感情来制作的。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北京特种工艺被帝国主义的殖民者喜爱。
他们把中国看作不文明,稀奇古怪。他们也就把北京特种工艺当作不文明和稀奇古怪的代表,并且更进一步鼓励往稀奇古怪的方向发展。
这样也就使北京特种手工艺更脱离了人民和我国原有的健康传统,主要地变成了外销商品。
仰赖外销,经济上的不能自主是随着北京特种工艺的堕落的宫廷风格而来的,而又成为北京特种工艺品质低落的原因。
这种情况到北京解放以后开始有了本质上的变化。在去年六月公营北京特种工艺公司成立以后,这个变化已经非常具体了。去年下半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了,更针对美帝的封锁,展开了对美帝的经济斗争,直到今天,北京特种工艺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尤其在北京特种工艺公司的具体领导下,已经完全走上了自主地发展的道路。
新图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全面地争取自主地发展的工作。所以新图样设计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同封建主义的、帝国主义的、买办的残余影响、不良作风进行斗争。
去年六月,北京特种工艺公司初成立时,同清华大学营建系服务部研讨了新图样设计和改良图案的问题。清华同人也愿意把过去曾进行过的景泰蓝新图样设计的尝试性的工作,变成一件正式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所以便接受了公司的委托。在过去这一年的工作中,我们深深体验到,如果没有北京特种工艺公司的领导,不同公司领导的其他方面的工作,尤其是经济上的翻身运动结合起来,新图样设计的展开是不可能的;不同全国整个政治形势、经济形势的发展配合起来,新图样设计工作的展开更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设计总的方向是为了产生新中国的新的人民工艺而努力。这个新的人民工艺必须是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所谓民族的就是要表现出我们民族风格的伟大丰富的内容。旧日景泰蓝中有模仿日本七宝烧的。例如装饰杂花的萝卜瓶,花纹胎形和色彩都是日本作风。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我们还反对,例如象牙雕刻中的半裸体美人,或林黛玉式的病美人,那是低级的庸俗的。我们还反对一向因袭保守满清末年西太后时代的繁琐杂乱、病弱无力的古怪作风。因为那不是我们民族传统中好的一部分,那不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我们要求承继优良的传统,而且不只是承继,我们还要求发展出新的民族工艺。
它们必须是民族的,而更重要的是它们必须是今天的。
所谓科学的至少包括两点:(一)新图样的设计必须从技术和材料出发。
设计一定要充分利用技术和材料上的特长方便,一定要避重就轻,使一定的技术和材料在它的限制之内充分发挥它的长处、回避了它的短处。
这样才能使设计出来的东西可以省工省料。(二)设计的东西要合于使用,便于使用,并且牢固耐久。反对过去有闲者嗜好的单纯小摆设。
所谓大众的就是我们必须照顾到大众的购买力。
从简化图案和尽量利用制造时避重就轻的办法,求其省工省料。当然,工厂中能同时改进技术和改善经营方式,使之减低成本那就更好了。设计小件的器皿也是适应大众购买力的一种办法。此外,工艺品有实用价值时,购买的兴趣也可以提高的。大众化另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适应群众的喜好。这个问题也就是如何向群众学习,了解群众的爱好习惯的问题。
设计不能完全从个人出发,但是也不能成为群众的尾巴,例如七宝烧作风的景泰蓝和象牙雕刻的半裸体美人等即使有销路也是错误的。
以上所说是我们工作总的方向。概括的说便是
我们设计的目标,是产生好看、好用、省工、省料的工艺品。
我们实际工作时就是基于这些原则,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景泰蓝的设计的。
一、我们对于景泰蓝的制作技术和釉料性质本来一无所知。我们的设计过程就成为我们的学习过程。过去指导我们最多的是作坊中一些老师傅们。现在公司正式成立了实验工厂,使我们有了更好的学习机会。一些有关技术和材料的初步的基本的常识我们已经摸着了一点门路。
二、为了适于实用,为了适应一般市场购买力,
我们尽量设计小件而有用的东西
。但是景泰蓝因材料的限制,实用的范围较狭。铜胎不宜于装水,甚至作为可能被溅上水的器物也不合适。所以花瓶、饮食用具都是不可能尝试的。结果我们所设计的大都是台灯和烟具。但是我们也发现有一种很简单的东西在使用上是变化多端的,就是有盖的小罐和小盒。罐盒之类可以用来装纽扣、针线、邮票、糖果、首饰等等,是一种能够适应多种不同场合不同生活的方便的容器。我们时时刻刻在思索着扩大景泰蓝的使用范围。将来在制作技术上、在原料获得改善时,这个问题当比较容易解决。至于在目前,客观事实既然限制着我们,那么在一定的客观限制之下尽量觅取解决问题的方法正是设计者的主要任务之一。
最近我们也曾设计了几件有装饰性的大件东西。那是为了公司参加各地展览会,以便有效的介绍北京特种工艺。此外更因为我们时常有国际性的友谊馈赠,也需要一些比较庄重富丽的大件。所以今春以来,我们偏重于设计一尺左右的大件。
常沙娜设计《和平鸽大圆盘》,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份国礼”
三、关于新图样设计中最使朋友们关心的问题便是花纹图样,美的表现的处理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说明七点:
1、新图样设计并不是单纯设计花纹。——一件好看的东西,除了花纹好看以外,还要形体好看,颜色好看,而且要三者配合得好看。新图样设计必须同时包括这三个因素,要把三个因素联系在一起考虑才能进行设计。新图样设计决不是仅只拟出了一种新颖的花纹。
花纹不是一个虚空的花纹,它必须附着在一定的形体上,和这个形体有不可分的有机关系。
它必须具有一定的色彩光泽。色彩光泽是花纹的具体的形象上的内容。我们要求三者:花纹、形体、颜色的统一的效果。所以把同一花纹随意变换它的颜色,或者随意搬家,从瓶子上搬到碟子上,而不经过慎重的考虑,都是不妥当的。
2、花纹形体和颜色统一的一致的效果。——
我们要求一件器物,一眼望过去就产生单纯的完整的明朗的印象
。与单纯完整明朗的效果相反的便是我们在前面所说过的满清末年以来的旧作风。旧作风的景泰蓝,形体是病态的软弱无力的,甚至畸形的、稀奇古怪的。花纹是繁琐零碎的,颜色是五颜六色、杂乱无章的。三者在一起既不统一,也不完整,而是互相扰乱。
3、新图样设计中花纹是最次要的考虑。——我们的设计在形体的决定上选择一些健康、挺拔、有生气、有气概的形体。颜色方面时常利用显明的对比色或近似的接近色。
花纹只是界划颜色、分布颜色,陪衬着形体,呼应着形体,加强形体的装饰性的手段。
所以我们的设计往往是以形体为第一位的、首要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加以考虑的,其次是颜色,最后才是花纹。
4、新图样设计反对花纹的繁琐零碎,并不笼统的反对丝工的精细。——对于旧作风的景泰蓝,有人往往只注意到花纹的繁琐零碎,而赞美其精致工细。这是片面的看法。精致工细,单纯从技术上看,我们工匠师傅的技艺水平是达到了惊人的高度。但是
做得细致并不等于好看,就如涂脂抹粉、描眉勾鬓的并不一定就是美人。一件非常丑怪的东西也可以做得非常细致
,而且往往过分的装扮恰恰就变成了丑怪。
盲目的追求精致工细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一种浪费。而且这正是过去封建统治者扼杀我们创造力、压迫我们、窒息我们的发展的手段。
以无限制的浪费人工材料为美的标准是腐朽的残暴的封建主义的特征之一。
我们并不一般的、笼统的反对做工的讲究,尤其是丝工的讲究。而且相反,我们要求,绝对要求做工的准确、认真、严格、一丝不苟。我们反对产生繁琐零碎效果的精致工细,并不是主张偷工减料的粗糙马虎。
过去的景泰蓝,例如
大家一向推崇的乾隆时代的景泰蓝,是只宜于近看的
,因为唯有拿在手中仔细端详才能看出丝工的精细。但在配色上,不调和的居绝大一部分。丝工的精细是景泰蓝唯一可以值得欣赏的。但是今天,虽然我们也要求新的景泰蓝仍是可以近看的,近看仍可以欣赏其做工的严谨准确。但是丝工的严谨准确不必是细碎繁琐。而同时,更重要的是必须也宜于远看。不必拿在手中,远远摆在桌上就非常触目、引人注意。这样就必须要它产生单纯完整明朗的印象,如前面第二点所说的。
5、在我们的设计中,若单就花纹来说,我们曾尽量利用古代花纹图案的精华,把古代工艺家的杰作作为我们组织花纹的借鉴。
在选择了一种古代花纹的时候,我们先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出它的规律。根据它特有的规律,例如虚实相间的规律、疏密对比的规律、曲线重复应用的规律等,然后把它重新组织到一个新的形体上去,给它一个新的安排。
通过今天景泰蓝的新材料与新技术,让古代工艺的优美成就重新再出现一次。大家看了今天的景泰蓝还能联想到、认识到我们的老祖先的创造力和杰出的智慧。
这不是单纯的仿古,因为它们是重新组织过了
,并且充分发挥着景泰蓝材料和技术的特有性能。
在景泰蓝的新图样设计中,我们是做着各式各样的试验。最初我们主要的借鉴于古代铜器花纹。因为我们对于景泰蓝最初只认识到它的庄重端丽,风格上和铜器相似。经过一年来的试验,
我们发现景泰蓝的表现能力很强
。它可以表现出很多种其他的材料所能表现出的风格。景泰蓝能产生古玉的温润的半透明的效果,也能够有宋瓷的自然活泼、锦缎的富丽,甚至京剧的面谱也给我们以启发。我们曾利用过建筑彩画的手法、战国金银错的手法、唐宋以来乌木或黑漆镶嵌的手法。尤其今春,敦煌文物展览开幕以来,敦煌艺术宝库的丰富内容更供给我们大批材料。结合着这个展览,结合着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为了推动借鉴古人以创造新艺术的运动,我们吸收敦煌图案来设计了景泰蓝,并且也试验绘画烧瓷,使烧瓷也表现活泼生动的新风格。
6、因为我们的试验是各式各样的,所以设计出来的东西的风格也是各式各样的。尽管还不够多,而已经有了变化过多的感觉。然而这正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多样和变化,以尝试着开辟新的道路。我们要求新,然而不离开传统的基础。我们需要从传统出发,然而我们不做死板的抄袭和机械的模仿。完全的新创或完全是机械的抄袭模仿都不能解决今天新工艺的问题。
7、景泰蓝的新图样设计到今天还说不上有什么成绩,但是已经起了一些作用。
在消极方面,新图样的出现消灭了许多顾虑。例如顾虑没有人要,顾虑会增加成本等,现在大体上已经不存在了。
在积极方面,第一起了教育作用,有人认为中国花纹只有龙和凤。有一位眼光狭隘的领导干部在北京特种工艺公司参观,竟认为新图样的景泰蓝不是中国花纹。那么,这些景泰蓝,恰可以扩大一部分人的眼界,进行了爱国主义的教育。第二新图样的景泰蓝已经带动了工厂作坊中的工匠师傅。他们不仅要求供给新图样、在仿制新图样,而且也在创造新图样。这个现象是值得欢迎的,掌握了技术的师傅们积极起来为景泰蓝的新生命而努力,制作和设计的密切结合是中国工艺的优良传统,也是将来新工艺发展的必然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