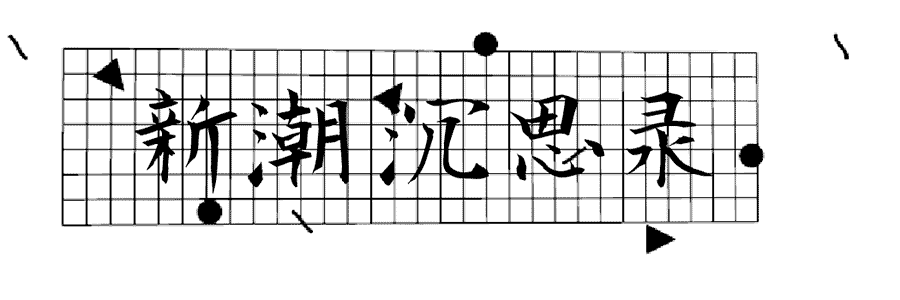
小孩2017年8月12日晚,90岁高龄的海南“慰安妇”受害者黄有良阿婆去世;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我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二十二》上映;次日,便是军国主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日。
这一连串事件和纪念日,是契机,让我得知某位相识,竟是这本书——《不一样的日本人》——的作者。而该书记录的事迹,指向一个特殊群体: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去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并求偿的日本人。
这些日本人的身份“五花八门”,有教师、律师、公司职员。但他们目标一致,在保护中国死难者遗骨、抢救“慰安妇”和劳工集中营受害者的口述历史、帮助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与日本右翼势力斗争等“行动”中,贡献出了极大的力量。
他们的工作没有酬劳,全是付出。
然而至今,这些努力的结果,仍没有一个完满的结局:无论是“慰安妇”,还是中国被掳掠去日本劳作的受害劳工及遗族,他们针对日本政府的诉讼均败诉;甚至对使用劳工的企业的诉讼,也均败诉。
书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副会长陈春龙,总结出的对日诉讼中“日本法律四大‘拦路虎’”。
其一,日本法院认为中国受害者“个人对国家无请求权”;
其二,国家公务人员行使职权发生违法侵权损害时,受害人只能追究公务员的个人责任,“国家无答责”;
其三,“超过10年的诉讼时效”,这是日本法院判决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败诉的主要理由;
其四,根据《中日共同声明》,中国人的个人索赔权已放弃,原告没有理由提出诉讼请求。
1995年3月7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就已经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就第四点进行“掰谎”:“在中日共同声明中,中国政府声明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请求,限于国家之间的战争赔偿,不包括中国国民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除此以外,前三点的逻辑和法理荒谬,简直不值一驳。
日本法院在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中,表现嚣张,这只是一个表象。而其本质,仍旧在于日本政府根本没有对中国人民做出合格而有效的道歉。
一个合格的道歉,是会产生法律上的连锁效应的。

不合格的道歉:逡巡在“迷惑”、“反省”和“御诧”之间
日本政府一向中国“道歉”,全世界都会发笑——因为它显然没有达到道歉应该达到的效果。
记得2001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日本神奈川大学的学者,分别对中日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有个问题是:“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您认为日本对这场战争已经谢罪了吗?”答案有四:1、已经充分谢罪;2、谢罪了,但不充分;3、没有谢罪;4、不清楚。
中国大学生答题者,没有一个人认为日本已经充分谢罪,即使认同答案2的,也只有26%。而日本大学生有21%选择了答案1,选择答案2的,高达48%。该结果反映的中日两国大学生认知差异倒是其次,重点是:时至今日,受调者恐怕已经开始教养下一代——其中隔膜和差异说不好会日益扩大。
日本学术界有些学者,研究起这种“差异”来,说得头头是道:中日在“道歉”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主要来自中日双方对语言感觉上的不同,以及文化差异。
然而全是扯。
只好请出正式文件中日本政府对侵略中国作出的所谓“道歉”瞧一瞧了,重要的有二:1972年9月29日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的《中日联合声明》;以及1998年11月26日江主席访日时中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
先说前一个。
当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周总理设宴欢迎。田中首相在开吃前的致辞中表示,战争中日本“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添麻烦嘛,日语原文用了“迷惑”两字……结果友谊的小船还没启航,差点说翻就翻。
周总理委婉地指出“添麻烦”的说法会扎中国老铁的心,因为该表述只适用于很小的事。田中对此没有回复。
后来毛主席亲自接见田中,开启了吐槽模式:中国年轻人不会接受你这个说法的,因为在中国,“麻烦”这词是用在你拿水泼湿了对方裙子的时候。
田中的解释是:“迷惑”听起来像个日本词,实际上还是从中国进口的,而且日本也确实是把它用在真心诚意表达谢罪之意的时候。
主席听后笑了,说:看来“迷惑”这个词你更会用。(我有什么办法,我听了也表示很迷惑呀!)
《中日联合声明》在双方磋商下出台了。日本政府的表述是:“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这里需要着重注意的是,其中“反省”一词,成为以后日本政府所谓的对侵略中国“道歉”的主基调。
从中可以看出,为了中日友好大局,我们这边是做出了让步的。我想,可能也是第一代领导人希望中日恢复邦交后,官方民间持续的交往,能够促使日本政府主动承认错误。然并卵,对方显然比我们想象得更无耻。

时间到了签订《中日联合宣言》的1998年——江主席访日。这是上世纪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访日。我们的愿望是“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相当于给对方一个充分道歉的机会,然而《中日联合宣言》里是这样写的:
“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讲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有点眼熟,该不会是照着1972年那份抄了一遍吧。基调还是“反省”,没什么新意。
之后大家就看吧,日本所有的所谓“国家道歉”,都可以在“反省”的基调上,打上“疑似”两字。要么是“对此深感痛心”(明仁天皇,1992);要么是“深刻反省和歉意”(村山谈话,1995)……something like this。
当然也有个“笼统”的道歉,就是前文所述“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讲话”。这位大臣村山富市在为纪念日本战败50年所发表的演说中提到:“由于日本在过去一段时期国策错误走上了战争道路,陷国民于存亡之危机;又因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的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害与痛苦。为了未来不再重犯错误,我虚心地接受这一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在这里再次表示沉痛的反省之意,并表示由衷的道歉”。
1995年的这次“道歉”,用的日语汉字为“御诧”。

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访日,与日本民众面对面对话。当时主持人就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总是要求日本道歉,这种道歉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朱总理当时就严正指出:“我想提醒一点,在日本所有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1995年,当时的村山首相曾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日本方面考虑这个问题。”
“御诧”,正是这次“笼统的歉意”。
日语中除了日常生活中的道歉用语,用于外交场合的正规用语有“御诧”和“谢罪”。英语翻译比较简单,都是“apologize”或“apology”。但实际上,它们的道歉程度是有区别的。朱总理肯定很清楚这一点。
从一个例证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中玄机。
1996年8月,日本政府决定通过日本民间组织“专为女性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向在二战中曾被逼充当“慰安妇”的亚洲妇女发放所谓“赔款”,还附上当时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桥本龙太郎的道歉信。
该组织要求信里写入汉字“谢罪”,而日本政府只愿用“御诧”。官员们还就两词用哪个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用了“谢罪”,就等于日本政府承认了战争的法律责任,赔偿就成了国家行为——这会引起其他未解决的赔偿问题的连锁反应。最后,日本政府用了“御诧+反省”的表述。
可见,其中的区别他们很清楚。
不过单纯“反省”终归是没法糊弄事儿——它在日语中只表示对自身过去的言行进行回顾考察,没有道歉的意思。后来小泉和安倍都用了“谢罪”,不过小泉的表述是希望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应背负“谢罪的宿命”;安倍倒是用了正面意义的“谢罪”,只可惜尼玛还是个过去式。

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
合格的道歉:瞧瞧德国,别不服气
在为二战罪行“道歉”这事上吐槽日本,还真绕不开德国。谁让二者罪行类似,但表述和效果完全不同呢。
二战刚一结束,德国就表示要对发动二战“全面担责”,向受害国人民“认罪、道歉”并“请求宽恕”。
在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的推动下,德国政府承认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光承认还不够,并表示会赔钱:“新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了罪并且有义务给予物质赔偿时,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罪恶一刀两断”。
此后历任德国领导人,都曾向不同受害国下跪谢罪,并忏悔:“德国这个名字永远和数万波兰人的苦难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莫斯科缅怀遭受希特勒伤害的俄罗斯人和苏联其他各族”……
2005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纪念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60周年大会上说:“对于纳粹罪行,德国负有道义和政治的责任铭记这段历史,永不遗忘”……
2015年5月,德国外交部民事专员格诺特·埃尔勒代表政府为纳粹在白俄罗斯的罪行道歉,他提及该国被屠杀的 80 万犹太人,并强调“这个罪行不会被遗忘,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光道歉不算,德国给予战争受害个人实打实的经济赔偿。1956年德国通过《联邦赔偿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个人求偿权,并且强调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各州政府,都对个人求偿负有责任和义务。1957年,《联邦财产返还法》通过,这就为战争受害者收回被纳粹掠夺的财产提供了法律依据。赔款方面,上至联邦政府,下到民间组织,建立了一整套机制,在60年间,支付了受害者约640亿欧元赔偿款。
我有个朋友曾去德国旅游,说对那里最深的印象,就是二战纪念设施随处可见。有专门机构负责对战争遗迹进行保护修复,不断提醒国人悼念逝者,铭记历史错误。而且一旦涉及纳粹言论、符号,言论自由的红线就会异常明晰。上个月,就有两个国人,因在德国国民议会大厦门口行希特勒纳粹军礼被德国警方逮捕。其法律依据,便是《德国刑法典》第130条:以扰乱公共安宁形式公开或在集会中对纳粹党执政期间暴行、专政予以赞同、否认其存在或为其辩护,并因此侵犯受害者尊严,将处3年以下监禁或罚金。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一条赫然即是:“人之尊严不可侵犯”——这正是对当年纳粹践踏人权罪恶行为的彻底反思。

首尔“分享之家”,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向“慰安妇”纪念像鞠躬
合格的道歉,是有标准的。
在语义上充分、明确、公正地就所有战争罪行予以认罪,并请求相关国家宽恕;给予受害者或受害国经济补偿;致歉本身,以及致歉过后言行一致;不伪善,尊重国家道歉在国际法惯例中的意义和地位——这些,都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
可惜哪怕是在语义上,日本的所谓“道歉”都不合格。还是以德国为对比:
其一,德国很明白笼统道歉只是开始,被道歉主体只能是具体的,比如白俄罗斯、波兰人民;而日本的“道歉”则往往始于“东亚国家”,终于“亚洲人民”。
其二,在对罪行的承认上,德国的原则始终是“清晰明确”,对战争犯罪细节进行客观介绍,并直截了当谴责纳粹的滔天罪行。日本则从不详述战争罪行,很少使用“屠杀”、“侵略”、“殖民统治”等负面但表意真实的词汇,代之以“添麻烦”、“造成巨大损害”、“历经不幸”等模糊的字眼。
其三,对于向他国悔罪,以及悼念本国死难者,德国历来“一码归一码”。而日本历次“赔罪”,总要强调自己也是战争受害国,不感慨下广岛长崎之惨,就没法谈战争的罪恶——最后以“战争受害国”和“爱好和平之国”的面貌来祈愿和平。
每次看到日本“道歉”,我就有种狗血剧里“求你说句‘爱我’吧,哪怕是说出来骗骗我”的心情……日本是连说都懒得说啊。
语义上都如此扯淡,就更别说实质的了。
比如日本政府总说我们已经放弃了国家索赔,但这不等于民间索赔权同时丧失。德国政府为了赔偿二战劳工,政府和企业都设立了基金。而在《不一样的日本人》一书中,着重介绍的日本政府对中国劳工的赔偿,至今就从未见到。这些劳工的求偿诉讼,仅仅是以同企业“和解”的民间方式了结。至于苦难深重的“慰安妇”求偿,日本政府也是妄图不走官方对话和诉讼,而希望通过民间组织给笔钱,草草了事。
此外,在“道歉”背后发生的恶心事多得很:多次枉顾受害国感情参拜靖国神社;多次修改教科书,模糊对“南京大屠杀”的定性,试图从表述上弱化侵略恶性;强推《安保法案》;同我们的领土争端……
就一个合格的国家道歉而言,无论是根据理论,还是外交实践,日本还差得太远太远。

套路深,以及套路深的成因
综合前述,日本政府玩的套路很清晰:用笼统的道歉掩人耳目,让国际社会和自己人,都认为日本已经道歉;“笼统道歉”的目的,则不但创造出“已道歉”的语境,还可以躲掉法律责任,不触发国家赔偿。
而日本法院之所以明目张胆让中国劳工败诉,也正是基于这一条脉络——反正,我就是不承认自己错了。
真是套路深,玩得自己都信了。然而也有很多学者表示很费解啊:相对于德国,日本简直就是个奇葩,这是为什么?于是大家纷纷给出解释,试图说服下自己受到刺激的心灵。
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往往会给出“地缘政治差异”这个原因——基于特殊地理位置,引发的大国角力,成为德日道歉程度不同的主要原因。
无论一战或二战,战后周边大国对德国的立场比较统一:要么是清算和削弱,再要么就是转向马歇尔计划,让西德融入,共同遏制苏联。无论哪个立场,从积极的方面看,一旦决定接受德国,就是全员接受——因此完全取决于德国的认错态度。东西德都表示一点压力木有:德国和美国一样都是新教国家,西德很容易在意识形态上同美国融洽,民族主义挫败后妥妥退回普世价值;而东德即便进入苏联式文化圈,警醒民众抵抗西方意识形态,也是殊途同归。地缘政治压力以及冷战阴影,都必然使德国通过彻底的国家道歉,来寻求民族和解。
而日本所处的东亚,在二战后一损俱损,没有一个强大政治实体能逼迫其对战争罪行负责。美国既怕苏中朝在东亚搞社会主义小团体,又怕把日本逼得太急,导致这奇葩狗急跳墙搞点什么全民玉碎本土决战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便干脆对日由“遏制”转“扶持”——意在养一条狗,来恶心苏中朝。穷得揭不开锅的日本,乐得跪舔美国换取“投喂”,实现经济复苏。美国有“求”于他,加上周边缺乏利益制衡,日本自然理直气壮地把受害国的谴责声讨,当成耳旁风。
还有一些学者则强调“历史文化观差异”。
德国由于历史上是城邦国家,贵族与平民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而非纯粹从属,因此民众更容易有独立意志,更容易认同个体自由和权利。加之德国有基督教传统和赎罪情结,宗教基底使德国人不抵触赎罪,也就更容易引导国民将二战视为国家错误对个体权利的践踏和亵渎。国家道歉理所应当——这在德国民众认知中,不是迈不过去的坎。
日本则否。日本天皇号称“万世一系”,本身就是神(而非神的代言人),而日本则是神国。人家都是神了,你还不跪舔么——因此任何宗教在日本,最后都会被改造成对天皇的崇拜愚忠和盲信盲从。这种精神土壤就非常容易被军国主义分子利用,对民众进行集体洗脑——对外侵略是“效忠天皇”,是应该且光荣的,这怎么能是“罪”呢?认罪,则是一等一的耻辱。
可见对于“耻感文化”浓重的日本人来说,道歉无异于骂祖宗十八代都不是东西,丢的是国家的人,毁的是大和民族的集体荣誉。

还有一种归因,是“战争记忆差异”——德日反思程度不同,与其民众在二战前后对国家的记忆关联甚深。
不妨做个“国拟人”。
德国在欧洲历史上,就是个天天打群架,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小地痞。他的每一次打架斗殴,基本都意味着伤人八百,自损一千。而真正让它从愣头青走向成熟的,就是二战:回顾了以前那么多毫无意义的群殴,倒把自己搞得一身伤痛,犯不着。从此这位“社会哥”走上了反躬自省之路,金盆洗手——记得疼,所以不再打架。
而日本,是个绿茶型小混混。最开始力量弱,每次打群架,他就站在一边蹭点好处。后来胆子大了,也开始做点“打一拳,当次婊子,再立个牌坊”的事——我不是打你哦亲,我是帮助你认识自己并且完善自己哦亲。无论是日俄战争、日朝战争还是中日甲午战争,日本都是这么个模式,并且获益良多。往往还都是他去打别人,自己老家没怎么挨打,而德国的家早就被干成筛子了。后来美国受不了,直接开干,狠狠扇了日本两耳光。你以为日本会记得疼?然而并不。只见他捂住脸,开始嘤嘤嘤:“兔兔我辣么可爱辣么萌,辣么为你着想,你为神马打兔兔,兔兔好委屈哒……”
请容我去吐一会儿。
但是战争记忆差异这点,是很恐怖的。
我们看很多日本反思战争的影视作品,就会发现许多日本老百姓对于二战的视角无非是:我们以前过着平静的日子,战争开始不顺利,我们于是过得渐渐不好了,命运开始变得悲惨了。
这里隐藏的事实是:在日子过得渐渐不好之前,他们所享受的平静的生活,以及日本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对他国老百姓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剥削的基础上。

“语境真空”的代价,“蚂蚁战大象”的希望
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存在一大片空白。
这片空白不但绵延到战后日本人的生活中,更被日本政府所利用,通过对战后“道歉”的敷衍了事,通过对教科书的修改和内容弱化,通过对受害国个人求偿诉讼的打压和拖延,创造出一个集体无罪的“语境真空”。
这个“语境真空”中不是没有战争的痛楚,但这些痛,仿佛都是落在日本人身上的。
在《不一样的日本人》这本书中,帮助抢救“慰安妇”历史证据的石田米子就指出:“战时的日本人在国外做了极其野蛮的罪行,但回到国内依然做‘好爸爸’、‘好儿子’、‘好丈夫’。”这些“好爸爸”、“好儿子”和“好丈夫”,其中绝大多数,都因为羞耻感,而不愿向家人回溯侵华往事。
而曾在鹿岛公司,犯下虐待中国劳工罪行的志村默然人,曾悲愤地指出:“战后日本政府都否认这段加害历史,加害的企业因为遣返强掳的中国人,而从国家得到大笔的补偿金和优惠政策,却装作不知道!个个都只盼望着‘都过去了,大家快点全都忘记吧’,这个态度让我激愤了!”
参战的一代日本人,大部分选择沉默,而他们孕育的下一代日本人,成长在和平时期的“语境真空”中,也即将忘却一切。
参与中国劳工对日诉讼的著名学者,田中宏,生于1937年。他上小学时,就已经开始觉得:“‘八·一五’之后的日本……是新鲜且充满信心的。”然而,在他为留学生后援团体工作后,才切实感受到,二战中东南亚受害国的留学生,对日本政府有多么不满,而日本的整体形象,在他们眼里有多么糟糕。
即使日本战后曾长期位居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但它的政治地位,由于在对战争罪行上的暧昧态度,在很多国家眼中,是存疑的,缺乏公信力的。日本,正在为它政府的文过饰非,持续付出着代价。

2013年7月2日,在东京枣寺,町田忠昭站在菅原惠庆住持的墓碑前。两人都是60年前的二战中国殉难者遗骨送还活动亲历者。
我用这篇文章,讨论了日本“道歉”的问题,但我更想探讨的,是:我们该如何面对“战争共同记忆”?
《不一样的日本人》的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记录,把真相写下来。
她曾将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形容为“同时间赛跑”。历史是沉默的,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从书中这些不断为唤醒日本国民战争记忆而奔走的日本人身上,看到了历史的紧迫感——如果不抓紧,可能大家就真的都忘记了。
忘记历史,何以言未来?
书里有一群“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日本人,他们所做的,也都是“蚂蚁战大象”的事——日本政府以国家机器之力,碾压着、否认着这些日本人希望为后代留下的一切历史真相,而他们仍旧在竭力挖掘、诚心谢罪、帮助战争受害者求偿,并试图打破“语境真空”,让更多日本青年能够认识到忘却战争罪恶的可耻和可怕。
我在他们身上读到了这样的焦虑:身为日本人,他们无法去爱一个不承认战争罪行的祖国。
正如同我们作为中国人,绝不可能去爱那些忘记战争伤痛的同胞。
面对中国人赴日诉讼或抗议战争罪行时,这些日本人,并不像他们的政府那样冷漠而暧昧,其中有位瘦削的老人,总是笑着,双手合十,说道:
“现在中国这么多人来要求日本谢罪,对战后活到现在的我们来说,是奇迹一样的存在。这让我们看到希望。”
而我多想同时也能让你们知道,就在六十几年前,这位叫町田忠昭的老人,曾守护着二战中国死难者遗骨,冒着船被台湾炮火击沉的风险,漂洋过海,一心送他们回家。
本文转自公众号 大燕威王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