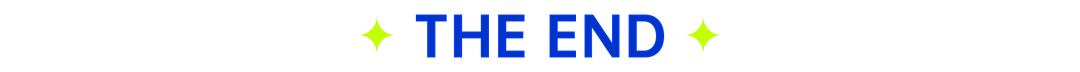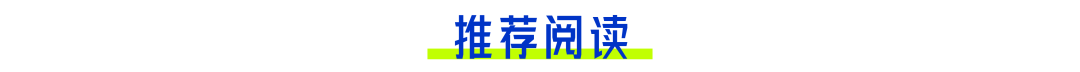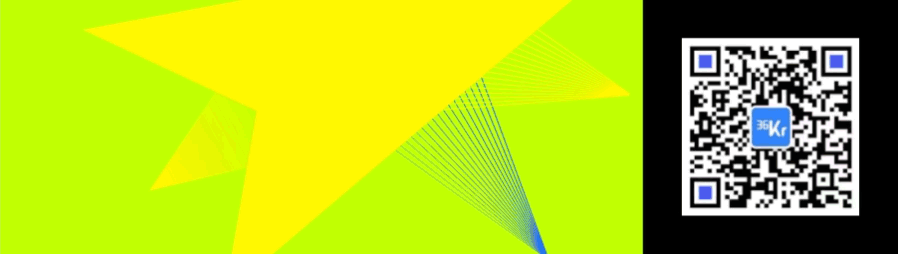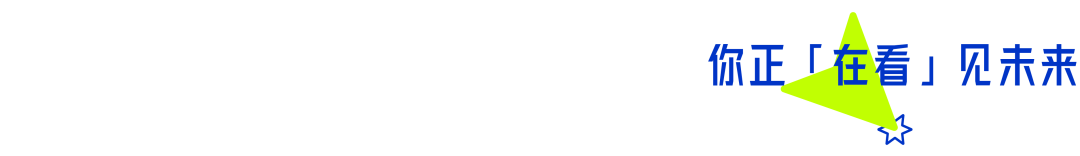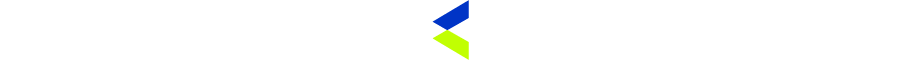
来源|IC实验室(ID:InsightPlusClub)朋友们,糖果真的要退出年货序列了。
随着90后、00后接手年货采办权,年货的格局正在改朝换代。
以前过年的回忆,是听着刘德华的《恭喜发财》,在超市散装糖果柜台前,一把一把往塑料袋里装徐福记。如今有了口感更丰富的卤味辣条,有了包装更精致的糕点礼盒。一个个糖果品牌,逐渐成了童年回忆的代名词。
糖果的式微,早已不是个新鲜的话题了,过去10年里,国内消费品行业经历了一波原地飞升,但糖果市场规模一直起起伏伏,原地踏步,甚至有过一波连续5年的衰退。过年吃糖的历史,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要短得多。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过年时候能拿着肉票排队买点猪肉,全家一起包顿饺子,已经是很多父母辈人童年时的最大愿望了。
至于糖,在大多数国人生活中算得上是轻奢消费了。
60年代,为了支援古巴经济,我国曾经大力进口古巴糖。尽管当时古巴的制糖业水平也是一言难尽,所以生产出来的糖类似红糖,杂质很多。
但就是这种初级工业品,也得凭票供应,对中国大多数家庭来说,是难得能吃上的好东西了。
一直到八十年代,情况才有所好转。
北京、天津、上海陆续引进了来自欧美的糖果生产线,北京红虾酥、山东高粱饴、海南椰子糖、扬州牛皮糖、厦门软糖这些具备地方特色的糖果开始在市场上风行。
而在这一代糖果品牌里,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上海大白兔。
这是一个怎么吹都不为过的品牌。
在80年代崛起的这一波糖果里,它不仅是最火的,也是活得最久的。如今甚至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一个复古icon。
它的前身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商人冯伯镛受英国进口的奶糖启发,创立的糖果品牌「ABC米老鼠糖」。
新中国成立之后,ABC糖果厂改名为爱民糖果厂,包装上的老鼠也换成了兔子,从此,大白兔就成了国产奶糖的代表,一代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
作为一个从匮乏时代走来的品牌,大白兔奶糖浑身上下,都带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
不知道看文章的同学是不是和我一样,小时候问过爸妈这样的问题:
为啥大白兔奶糖里要垫一张糯米纸?
这张薄薄的糯米纸,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奶糖因为高温而融化,黏在包装纸上,也能起到吸湿的作用,防止糖果受潮变质。
以如今的食品供应链水准来看,这种「土办法」原始得像是刀耕火种。
但在小时候,我如果想把那张食之无味的糯米纸丢掉,还是会被我外婆说上两句的,毕竟那多少也是一点淀粉啊。
另外,大白兔早年的营销也很有时代特色。
匮乏时期,小孩容易营养不良,但是奶粉供应也很紧张。所以当时的家长会排队买点大白兔奶糖,给小孩补充营养。当时大白兔的标语就是「七粒大白兔,就是一杯好牛奶」,可以说直击消费者痛点,也符合当时经济条件下,大众对糖果的定位:
糖果,是一种营养品,是匮乏时代难得的高能量密度食物,是爸妈口中的「好东西」。
「好东西」这个定位,贯穿了糖果品类从兴盛到衰败的全过程。
随着八十年代,中国人初步走出匮乏,糖果产量也大幅提升。到1987年,中国糖果业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年产量达到40万吨。
供应量上来了,糖果也从高端营养品,慢慢走向了大众消费领域。
既然是好东西,自然要用在关键时刻。
例如逢年过节。
糖果进入大众消费领域的第一站,就是春节。
很长时间里,中国的消费市场上其实并没有一种成型的「年糖文化」。中国人对过年吃糖这件事的认知,只是基于「过年了吃点好的」这样的朴素认知,以及「二十三,糖瓜粘」这样的传统民俗。
真正把「新年糖」这个概念打包拿出来卖的,是徐福记。
1992年,在台湾卖了14年糖果蜜饯的徐记食品来到内地,在东莞租了块地搭建工厂,经营糖果贴牌加工,再将产品出口到其它国家的生意。
在总工程师的「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召开的背景下,一系列政策支持让许多台湾企业纷纷来到大陆。起初,许多企业看中的只是这里低廉的原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但很快,他们发现大陆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消费市场。
徐记食品也不例外。1994年,他们注册了「徐福记」商标,打算将出口转为内销。
从商标开始,徐福记似乎就有意和春节联系在一起。借着春节喜庆的档口,徐福记打出了「新年糖」的概念,将徐福记与春节牢牢绑定。
当然,只有新年糖这个概念是不够的。
徐福记对大陆消费者的消费心态的洞察,才是这个品牌的取胜之道。
首先,它们了解到,新年糖不止是自家人吃,过年喜欢走亲访友,家里必须准备糖果招待客人,一个普通家庭短短几天内至少要接待十几位亲朋好友,男女老少口味各不相同,新年糖的种类自然是准备得越多越好。
因此,徐福记采用了大SKU战略,依靠制造端的优势,一口气推出了40种糖果,比当时市面上其他品牌加起来还多,一个品牌就能满足消费者所有需求。
其次,他们发现,消费者新年买糖果追求量大管饱,包装糖果性价比不占优,散装糖才是过年的主流。另外,他们买糖时并不精挑细选,而是喜欢每样都来点,如果每种糖果都不同价格,那就太麻烦了。
针对这样的用户特征,徐福记采用了「散装统一定价」的销售方式,所有口味统一价格,而且全都称重计价,极大简化了购买流程。
最后,他们发现,当时的消费者只认产品,不认品牌,像是金元宝造型的巧克力、蓝白格子包装纸的牛轧糖,全国各地消费者都吃过,但要问是什么品牌,其实大部分人都想不起来。特别是散装商品,大家更关心产地和价格,不存在品牌。
因此,徐福记采取了专柜模式。用一个大桶,装满自家糖果,然后贴上海报,来加深消费者的印象。从此和其他的散装糖果在品牌认知上区分了开来。
到了2000年,随着沃尔玛、家乐福进入国内,徐福记和这些大型超市建立了供销关系,有了更具规模的品牌专柜。在电视上,每年春节都能看到的徐福记广告,以及那声尾音上扬的「徐福记」,都让它成为了一个全国性品牌,和地方的小型糖企拉开了差距。
即使20年过去了,在春节的散装糖市场,徐福记依旧能吃下接近四成的份额,哪怕是德芙、阿尔卑斯、费列罗或是大白兔,都无法撼动徐福记的地位,无愧「年糖之王」。
在那个年代,只有徐福记这样来自港台的企业,可以同时具备品牌意识、制造能力、用户洞察和对中国民俗文化的理解,创造出新年糖这样一个独特品类。
直到如今,春节依然是糖果市场最重要的销售节点。许多大糖企的春节期间营收,依然要占到全年收入的40%左右。
与春节平行,糖果的另一大消费场景是喜糖。
作为中国传统婚俗的一部分,喜糖的起源非常复杂,比较主流的一个说法是由红喜蛋演变而来。但到了近代,糖更像是贫困时代里,一个幸福的象征。
在五六十年代,喜糖主要是便宜的水果糖,包装简单,按斤出售,新人结婚买一大包分发给婚礼宾客,可能证婚人,aka单位领导再致个辞,这婚礼也就算成了。
到八十年代,口感更好的奶糖开始取代水果糖进入喜糖市场,并且迅速流行开来,大白兔一度成为婚庆常客。当时甚至还有说法是:「喜糖里如果没有大白兔,这婚就白结了。」
除了现场分发散装喜糖,这个时期人们还开始用印有红双喜字或者龙凤图案的小塑料袋来装喜糖,方便馈赠亲友同事。
此后,喜糖的花样开始越来越多,巧克力、花生糖、酥糖纷纷加入喜糖阵营,另外包装也越来越卷,各种造型别致的纸盒,甚至高档的牛皮纸包装开始出现。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他的著作《身份的焦虑》中文版序言中提到:
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了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中国从80年代开始,展开了一场漫长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场浪潮几乎席卷了所有的社会成员,尤其在城市,社会阶层与阶级地位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动。
在这样的变动中,为了避免产生身份认同危机,人们需要寻找到定位自我的锚点。而最容易找到的锚点,便是物质消费。
婚礼的烟酒糖茶,春节走亲访友的礼物和食物,在许多人,尤其是老一辈的观念里,与其说是刚需,更像是一种仪式,是自我表现的载体和对社会地位的确认。
而糖之所以在其中如此重要,必须承认,这依然带着某种匮乏时代的烙印,依然源于它「好东西」的定位。造神时代
1958年,日本电影新浪潮代表人物增村保造拍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巨人与玩具》。
在片中,三家糖果巨头为了争夺市场,展开了一场癫狂的营销大战。这部电影如同一部预言,在日本经济刚刚腾飞之时,就预见到未来资本主义末期,传媒与商业将以无孔不入的姿态,将所有消费者卷入它滚滚向前的车轮中。
而事实上,在中国的糖果市场,也有过这样一段被传媒统治的造神时代。
营销领域有个名词叫做「利益点」,也就是品牌要向消费者宣传:购买我的产品,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早期,糖果的核心利益点只有两个:甜蜜、营养价值高。在匮乏年代,这两个利益点就足够有说服力了。
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本土民营企业份额逐渐扩大,以及玛氏、好时、雀巢、亿滋这些外企纷纷进入中国,带来一大批创新产品和大量产能,糖果很快从逢年过节才能敞开了吃的「好东西」沦为了普通零食。
当然,飞速增长的肥胖人群、蛀牙人群和糖尿病人群,在糖果的祛魅过程中也居功至伟。
于是乎,糖果企业必须给自己的产品找到全新的神话。
1994年,德芙进入中国。
这个品牌,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传说它来自一个穷厨师和一个皇家公主的爱情。
大家提到德芙,脑海里冒出来的第一个词多半是丝滑,但如果你仔细研究广告代言,就会发现,德芙的代言人常常是一男一女成对出现。
事实上,巧克力搞爱情营销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了。
而在中国,在这方面玩得最花的,还是费列罗。
除了爱心形状包装费列罗礼盒。还推出了不同规格的巧克力花束,你可以直接把一大束金光闪闪的费列罗送到女孩手上,既好看,还很有食用价值,更有一种「我给你花了大钱」的仪式感。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费列罗也渗透进了喜糖的序列里。
在21世纪的中国,伴随着电视的普及,大众传媒的渗透,以及城市中产阶级不断扩大,爱情营销在当代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爱情,就是糖果品类的新神话。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爱情这个打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糖果。只有巧克力、太妃糖以及一部分口香糖品牌比较合适。
另一些糖果品牌,选择了另一种造神方式:
1994年,柳州市糖果二厂自筹资金780万,在厂长江佩珍的带领下成立了广西金嗓子制药厂。
这家糖果企业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国内第—颗果酱夹心糖、第一块花生巧克力,以及第一颗酒心巧克力都来自这里,1988年,糖果二厂产量近2万吨,产值9700万元,是全国糖果业老大。
但到了90年代,在假冒伪劣产品的冲击下,糖果二厂已经濒临破产。为了拯救公司,江佩珍带着厂里仅有的7万元前往华东师范大学,拿到了一个治疗慢性咽炎的配方。
这个配方生产出的非处方药被命名为「金嗓子喉片」,而改进后推出的润喉糖,就是我们无比熟悉的金嗓子喉宝。
金嗓子制药厂成立第二年,江佩珍就斥资500万砸央视广告,让「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在央视反复播放,结果第二年,金嗓子营收就突破一亿,到1998年则是达到2亿产值,成为全国药企百强。
后来和罗纳尔多的「被代言」事件,以及砸钱请卡卡代言,更是让金嗓子成为中国最传奇的品牌之一。
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江佩珍真正的神之一手,是其他糖果还在口味、原料、香型上卷生卷死的时候,金嗓子已经换了条赛道,走上了功能性糖果的道路。
功能性,就是糖果品类的另一个造神手段。
既然甜蜜、营养都不稀缺了,那我创造一个稀缺性让消费者买单就好了。
当然,必须承认,润喉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市场需求,不管是金嗓子,还是其他品牌的润喉糖,依然是超市便利店里动销非常好的品类。
伪需求做起来的,也不是没有。
2003年,国内糖果行业一个划时代的产品诞生——雅客V9。
它开创的是一个新赛道,叫维生素糖果。
雅客能崛起的一个很大原因在于当时正值非典时期,消费者普遍有一种「免疫力恐惧」。而雅客主打补充维生素C,提高免疫力,自然是戳中了市场的痛点。
而且和金嗓子一样,雅客也很舍得在广告上投钱。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还有印象,当时雅客V9请来周迅当代言人,在央视狂打广告,当时每天中午CCTV5的体育新闻中间,总是能看到周迅带着大家跑步,喊着「天天吃雅客,健康又快乐」。靠着营销砸钱,雅客V9一度也是国内糖果市场的明星产品。
事实上,当中国的糖果市场进入了一个造神时代,无论是主打功能性,还是主打情感,都离不开一件事:广告营销。
而且这样的广告营销,必须通过广播电视这样渗透率极高的大众传媒,大力出奇迹,才有机会将对新概念的崇拜植入足够多消费者的脑子里,从而让消费者重新树立「糖果是好东西」的认知。
但反过来说,当糖果需要电视传媒来造神,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原本的它已经彻底走下神坛,那些由于稀缺,由于匮乏带来的时代光环已经散尽。
无处不在的甜
如今,当我们想吃点甜的,我们会选择什么?
我们可以选择蛋糕烘焙,它还能提供一定的饱腹感,有花样繁多的口感,有百变的造型。
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小零食,它研究过人类的味觉曲线,精妙搭配盐、糖和油脂三者的比例,直接命中大脑中的极乐点,让人停不下来。
甚至当我们想吃甜,我们可以选择水果,它更健康,更营养,只要打开外卖软件,甚至可以给你切好剥好搭配好,端到你的面前。
当我们想吃甜,我们可以选择含糖饮料,它能给的还有热饮或冷饮的温度,还有解渴的功能。风味通过液体,也更容易释放到我们的感官之中。
事实上,当下我们摄入糖的主要方式,早就不是糖果,而是饮料了,40%以上的糖分,都是喝进去的。
而糖果太简单,太纯粹了,除了酸甜的味道,它能给的实在太少了。
相比满大街的奶茶店,随便走两步就能找到的蜜雪冰城和古茗,在口袋里放几颗糖果,实在是太前现代,太不像这个消费时代的做法了。
匮乏时代的「好东西」,在当下,早已不值一提。
从这个角度看,糖果的衰退,恰好也是糖的盛世。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
糖在我们日常食物中的比重,远高于我们想象,当你逛超市的食品区,会发现,不含糖的食物可能不超过20%。
即使不是为了吃甜,糖在现代食品饮料里也几乎无处不在。
作为重要的添加剂,它易于溶解,可以为饮料提供不同粘度的口感。
它易于结晶,可以作为冷冻食品的结晶改良剂和膨松剂。
它可以帮助果酱和蜜饯延长保质期,可以帮助蔬菜保鲜和脱水加工。
它可以为食物上色,烘焙后可以提供香气。
更重要的是,糖是人类身体在千百年进化后,形成的本能需求。人类渴求能量,而甜味来自于易于消化吸收的糖类,因此往往意味着高密度的能量来源。
嗜好甜食,对甜上瘾,这是人类基因里的偏好。
即使是在遗传学和饮食传统里,相对不那么嗜甜的中国人,也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几家现制饮料连锁品牌,并且都以甜著称,没错,我说的是蜜雪冰城和瑞幸。
无论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多么热爱东方树叶、三得利和元气森林,中国的饮料市场,依旧是被四块钱以下的可乐雪碧冰红茶这些含糖饮料撑起来的。
在这个食品工业高度发达的当下,甜已经无处不在,它比咸、酸、苦、辣、鲜任何一种味道都更加易得。
糖果的衰退,并不代表我们战胜了本能,战胜了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东西。
相反,它以另一种方式,证明了人类的生物性有多强大。
哪怕我们过年吃糖越来越少,砂糖橘的消耗量也从不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