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该文本是对白先勇先生及其作品的一场详细讨论和解读,包括其文学、情感、历史背景等方面。文章主要围绕中秋节日展开,讨论了白先勇先生的作品中对情感和美的描绘,以及他对红楼梦的解读和翻译。同时,还涉及到了对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和反响的讨论。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白先勇先生的作品中对情感和美的描绘
白先勇先生的作品以情感丰富、美学独特著称,通过对人物和情节的细腻描绘,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情感和美的境界。文章中讨论了他的作品中对中秋节日的描绘,以及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物情感和命运。
关键观点2: 白先勇对《红楼梦》的解读和翻译
白先勇先生对《红楼梦》有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解读,文章中提到了他对《红楼梦》中红色象征意义的解读,以及对庚辰本和程乙本的比较。此外,他还翻译了《红楼梦》的英译本,为推广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
关键观点3: 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和反响
青春版《牡丹亭》在国内外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文章中提到了该剧的演出情况,以及观众和评论家的反馈。同时,还涉及到了对中国传统戏曲和现代艺术形式的讨论。
关键观点4: 中秋节日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
中秋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节日之一,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社会意义。文章中通过讨论白先勇先生的作品和相关话题,展示了中秋节日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正文
“中国人讲‘情’,跟‘爱’又不一样,‘情’好像是宇宙的一种原动力,一切的发生就靠这个‘情’字,它比那个‘爱’字深广幽微。”今年中秋,白先勇先生携青春版《牡丹亭》来京进行20周年纪念演出。理想国有幸邀请他以及一些共同的好朋友,以一场“共读·致敬”活动,共度佳节。月亮的温柔、柔软,含蓄的国人尤能体味。月光勾起乡愁,白先勇先生的作品便构建了乡愁独特的一种:沉湎于过去的《台北人》,或独在异乡的《纽约客》,岁月的悲感和人的孤独、零落,透过极致细腻的文字传递出来。而比凄美更扣人心弦的,是字里行间充沛着的中国人的至情、至美。无论是其文学作品、文学研究还是戏曲,情与美都是白先勇先生永恒的创作主题。
01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读的其实是白先生1988年写的《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即欧风美语。2002年9月—2003年1月,我在台湾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客座。我的教室是林文月先生原来工作的教室——第四研究室,也是以前郑骞和叶嘉莹的研究室。就在那个时候,有一次白先生请客,我和若干个台湾学者一起吃饭。席间谈起《游园惊梦》,以及那篇小说改编成的舞台剧如何受欢迎。记忆中当时并没有提起后来的《牡丹亭》的事情。回来以后的20年间,我看着白先生风生水起,从小说家转变为戏曲的推广人,制作了青春版《牡丹亭》。我在北大听白先生讲小说、讲昆曲、也讲红楼梦研究,很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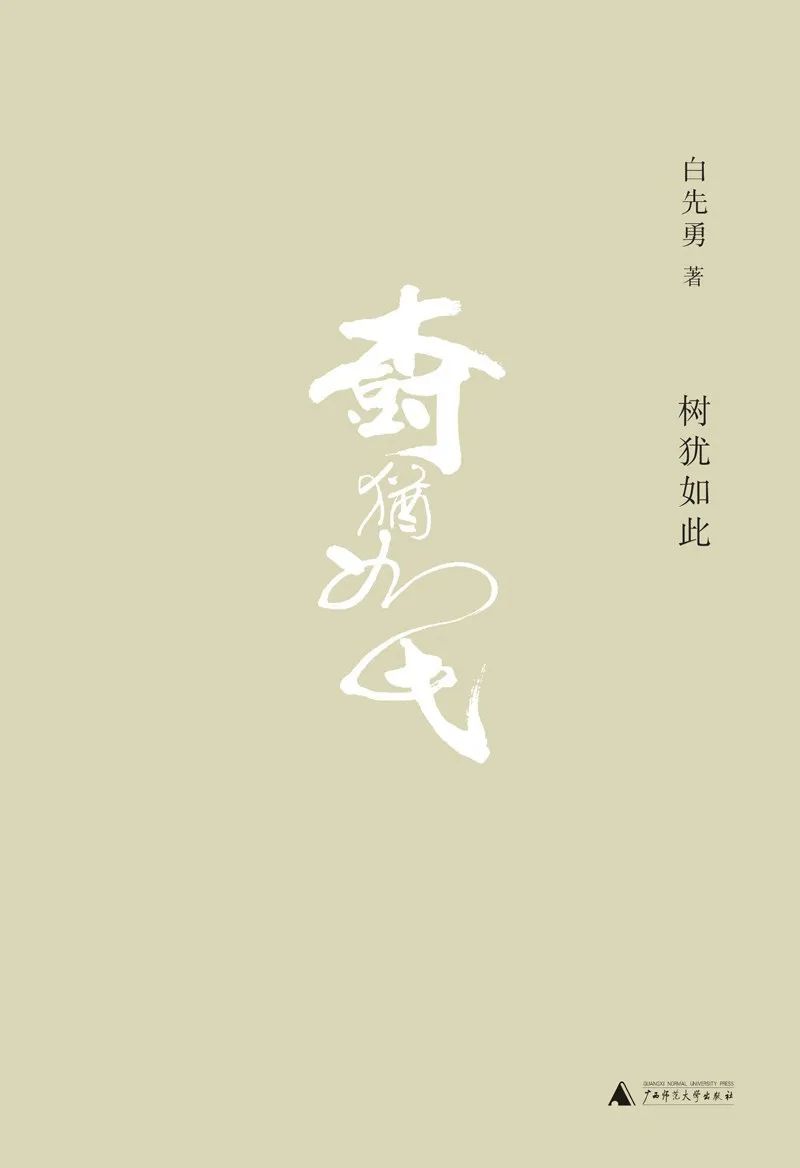
02
戴锦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戴老师说朗读的选段并非自己所选,但这一段却跟她也特别有关系。《谪仙记》被改编成了电影《最后的贵族》,而戴老师就是做电影研究。《纽约客》的扉页上,白老师写下了陈子昂的诗:念天地之悠悠,读怆然而涕下。其实《纽约客》和《台北人》,白老师写出了两种孤独和飘零:一个是异国他乡,一个是活在过去。
03
林白
作家、小说家
林白老师和白老师是同乡,都是广西人。在后面的对谈中,白老师提到,如今他阅读书籍,心中默念的依旧是广西话。04
咏梅
演员
“大家中秋快乐。我们在‘咏读计划’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选了《永远的尹雪艳》,也是一次致敬。那今天是第二次向白老师致敬了,特别的开心,今天跟大家在一起共读白老师的作品。我今天选了一篇是《嫡仙怨》里的,‘给妈妈递一封信’。因为我现在正在上映的电影(《出走的决心》)里面,也有母女情感的表现,就是不同时代的、不同际遇的母女的情感,所以我选了这篇‘给妈妈的一封信’。女儿在年轻的时候,她不能够理解妈妈,她对母亲的自我完全是不懂的。直到她自己成长了之后,有了自我以后,她同时也可以理解她妈妈,在年轻的时候。”
05
李敬泽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评论家
“40多年前,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小说选》,一本蓝色封面的书上,第一次读到白先勇先生的作品《游园惊梦》。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个作品带领我深刻的领会生命之大美,岁月之深悲。当时我16岁,所以对我来说,白先勇先生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作家。所以特别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重读《游园惊梦》,向白先勇先生表达我的敬意和谢意。我读的这一段,小说已经是接近曲终人散了。我想正是这些华彩的段落,特别精彩地呈现了整个《游园惊梦》以及白先生的美学精神:那样一种岁月的悲感,不胜今夕之感,在最后一段里,在一切都要结束、一切终要终结的时候,流露出来。”06
蒋方舟
作家、小说家
“我第一次见白老师是12年前,那时候是2012年,我还是一个毛头记者,大学刚刚毕业,白老师是我采访的第一个大人物,当时是随身采访了两天的时间。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特别喜欢听白老师讲过去的故事,那些过去的故事在他嘴里有一种别样的风采。比如他讲到在80年代的时候,他到上海复旦大学去讲座,结束了之后到一个叫悦友餐厅的地方吃饭,结果白老师发现那是他过去在上海住过的房子。白老师还讲到小时候见宋美龄的经历,还有刚刚轶君谈到的,白老师在主编《现代文学》的时候,见到十六七岁的还留着赫本头的三毛,白老师讲到张爱玲时说她是一个瘦瘦的、淡淡的、像从古画里面走来的人。我当时听这些故事就听得如痴如醉,我就在想,人们总说白老师是最后的贵族,那是我第一次明白‘贵族’是什么。我发现其实贵族并不意味着绅士和财富,而是一种记忆的贵族。我发现白老师经历了那么多,乃至于他随便从记忆当中检索出的一个片段,都是我们常人难以企及的奇观和奢侈。同样的,情与美也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奢侈。我在几天前连续地看完了上本、中本、下本的青春版《牡丹亭》,在看完之后我很久都无法从那种状态当中脱离出来。这种极深的情和极致的美,是一种多么大的奢侈。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我处在一种特别恍惚的状态中:你不在剧院里,同时你又没有回到现实的生活中。如果给这种真空状态以名字的话,那可能就叫做永恒。我想生活在永恒当中的人是不会老的,就像尹雪艳总也不老,白先生总也不老。”
07
陈嘉映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文学我是外行,读的也不多,要是读我就是读一点哲学。没有谁朗读过哲学吧,因为那些哲学文章、句子,写在纸上也半通不通的,要读出来你就完全不知所云了。我斗胆站在这里磕磕巴巴的读一段,就是向白先生致敬。现在我到哪参加活动,一般都是最老的那棵树,今天见到比我还老的树,有一个机会向您致敬,感到非常荣幸。”
08
陈数
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
“说起跟白先生的缘分,我想必须要提到《永远的尹雪艳》这篇小说。在2005年的时候,我刚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很惶恐,不知道自己该演什么。不知道为什么,突发奇想,有了很强烈的演民国戏、演穿旗袍的女人的念头。为此,还是新人的我,花了半年的时间,真真正正的去学习、体验上海。在文学的部分,白先生的这篇《永远的尹雪艳》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调性的定位,为半年后我出演《新上海滩》中的交际花方艳云,一年后在张爱玲女士的小说《倾城之恋》当中扮演白流苏,以及再一年之后在曹禺先生的话剧作品《日出》当中扮演陈白露,奠定了非常强烈的基础,所以这可能也是我民国缘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引导者。”09
都靓
文学博主
“我其实特别喜欢《花桥荣记》这一篇。因为白老师他把那个时代人们的命运,随着波涛汹涌的年代和每个人的命运深深的连接在了一起。我觉得放在今天,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总是理所应当的觉得明天一定是更好的,未来一定是越来越光明的。但其实每个时代人们的命运就像烛火一样,忽明忽暗,不可预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当我们遇到人生的换季,我觉得可以让《花桥荣记》里面的卢先生、里面的老板娘,跟我们站在一起,肩并肩共同度过一段时光,我觉得这就是文学对于我们的意义。”🎤

01.乡愁,在胃里,在语言里
周轶君:今天是中秋节,我有一次看到您的朋友奚淞说,您刚刚去美国的时候,就跟他说美国人就知道晒大太阳,只有您一个人能欣赏月亮之美,在月光底下走。
白先勇:的确是,美国人喜欢到海滩上晒太阳,对于月亮没我们中国那么敏感。你看我们的诗里有多少月亮。
周轶君:我们为什么对月亮这么痴迷呢?
白先勇:我们拥有好多神话,嫦娥奔月等。而且中国人的个性,柔软、温柔一些。他们西方人主张暴烈,像太阳;但月亮的美,我们懂得欣赏。
周轶君:戴老师,您对于白老师的作品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
戴锦华:读大学的时候,也就是七八十年代之交,具体的时间不记得了,我想我可能跟李敬泽读的是一个版本的,应该是一个短篇小说选。
周轶君:就是有一轮月亮的那一本。当时您读的时候有什么感想吗?
戴锦华:当时就会有一种既远且近,一种极度陌生,但是在陌生当中会有一种熟悉。我觉得白老师作品在那个时代,好像有两重功能:它帮助我们建构了一种其实不属于我们的乡愁。逝去的岁月,逝去的优雅,那个原本不在我的个人生命序列和情感序列当中,但是经由阅读这些作品开始产生。同时,尤其是像《纽约客》这样的作品,在那个时候,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外面世界中的华人,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奇特和新鲜的经验。
周轶君:白老师,今天听到 10 位朗读者读您的作品,这些久远的文字又回来了,什么感受?
白先勇:那些都是好早以前写的了,我听起来自己也陌生了。
周轶君:我就是想问您还记得吗?
白先勇:哈哈哈,这真的不记得了,不过讲吃米粉我想起来了。的确就是一回去,我早餐吃米粉,中饭吃米粉,然后晚上吃一份,宵夜了又去找,好像是填不满的乡愁吧。其实我 6 岁就离开桂林,可是很奇怪,我还能说一口桂林话。经过几十年以后,回到我们的三尾村那边,小孩子都很吃惊,你怎么还会讲桂林话。
周轶君:我问过几个小孩,你觉得你故乡是哪里?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小时候吃过的东西。就是您说的这个乡愁,是在胃里。
白先勇:而且语言也是特别的。我现在看书,我心里面默读的是桂林话。
周轶君:看任何书吗?
白先勇:对,我心里面默默诵的是桂林话。
周轶君:用桂林话读《红楼梦》,我不敢想象是什么味道。白先勇:讲到《红楼梦》,我跟理想国渊源非常深,理想国是出版(我的作品)最多的出版社,有 20 种了。引进《红楼梦》的程乙本,是我跟理想国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一次出版关系。
《红楼梦》程乙本是胡适先生推荐的,流传了九十多年,可是后来几乎被庚辰本取代了。可是我自己觉得,我在台湾大学教《红楼梦》教了三个学期, 100 个钟头,把庚辰本和程乙本前 80 回全部对过一次。
周轶君: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看。
白先勇:这个程乙本看了一辈子,就很熟,有一个字不对,我就眼睛眨一下,哈哈哈。
周轶君:我记得您提到过有一个细节,贾府的中秋宴,贾母当时其实有一些伤感。您说程乙本里头写到说她隐隐地有一些伤感就停了,另外一个版本是要说她几乎要落下泪来,您觉得这个情绪就过了。
白先勇:贾母是何等人士?她是这个贾府的大家长嘛,而且贾母这个人很理性的,很能够掌握大局。最后贾家抄家,她一个人还非常理性,能够克制、稳住。那我觉得这一场中秋宴,程乙本写到“她伤感起来”就够了。庚辰本就说她掉眼泪了,这个时候不必。小说,文字上的分寸拿捏最重要,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不哭。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本子,我看到的有197(处)——可能还有更多不同的地方——完全从小说的艺术来看,程乙本是高于庚辰本的。
所以我觉得理想国把程乙本重新印出来,意义非常大。我在台湾也尽量推广。《红楼梦》我看了一辈子,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敢讲说,《红楼梦》是天下第一书,所以非常重要。
周轶君:戴老师,我看到有一次访问,您说《红楼梦》自己隔一段时间隔几年就会拿出来重读一下,为什么要重读?
戴锦华:不光《红楼梦》了,比如《战争与和平》,我也过几年重读一次。不同的年龄,每一次读都会发现我以前没读到或者说以前没读懂的东西。那种突然有所悟的感觉,是非常快乐的阅读经验。
白先勇:我也是同样的,每隔十年重读就有新感受,它(《红楼梦》)是一本天书。周轶君:您是在当中解谜,我看到白老师翻译了当中埋伏的很多密码,把它破解出来。
白先勇:《红楼梦》是说不尽的玄机。
周轶君:我第一次听到白老师讲《红楼梦》中“红”这个颜色的含义,就有点被惊讶到了。贾宝玉最后一场戏,是跟父亲告别,穿着红色的袈裟,为什么是红色?是替大家背起了情的十字架。
白先勇:我想最后那一幕是最重要的,宝玉出家,他穿了一个大红的猩猩毡。猩猩毡是很重的斗篷,他不是穿黑色的袈裟,也不穿褐色的,他穿了一个红色的斗篷。在我看,红色在《红楼梦》里面,有很多象征意义,其中一个是爱情,因为你看这个林黛玉的前身是绛珠仙草。
周轶君:就是暗红色。
白先勇:叫做红色。那贾宝玉的前身他是神瑛侍者,他住的什么地方?是赤霞宫,也是红的,所以他们那一段仙缘、那段爱情是红色的。周轶君:为什么这个颜色这么特别?
白先勇:红色对中国人很重要。
周轶君:是吗,戴老师?戴锦华:不要逼我搞比较文学。红色在我们这是最饱满的和喜庆的,然后在西方就是预警、危险,这个是最浅表的差异。
白先勇:是这样子,那个《红楼梦》的英译者,这个 David Hawkes,他那本书的Story of Stone《石头记》翻得非常好。可他对红色的反应,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看来红色是威胁。比如,我们说的怡红院,他改成了绿色。他觉得在西方绿色比较好。我刚刚讲了,宝玉出家是用红,他穿着红斗篷,是担负了这个情,为情所伤,背了情的十字架。不光是黛玉,他是被天下所有情伤,带着情伤而走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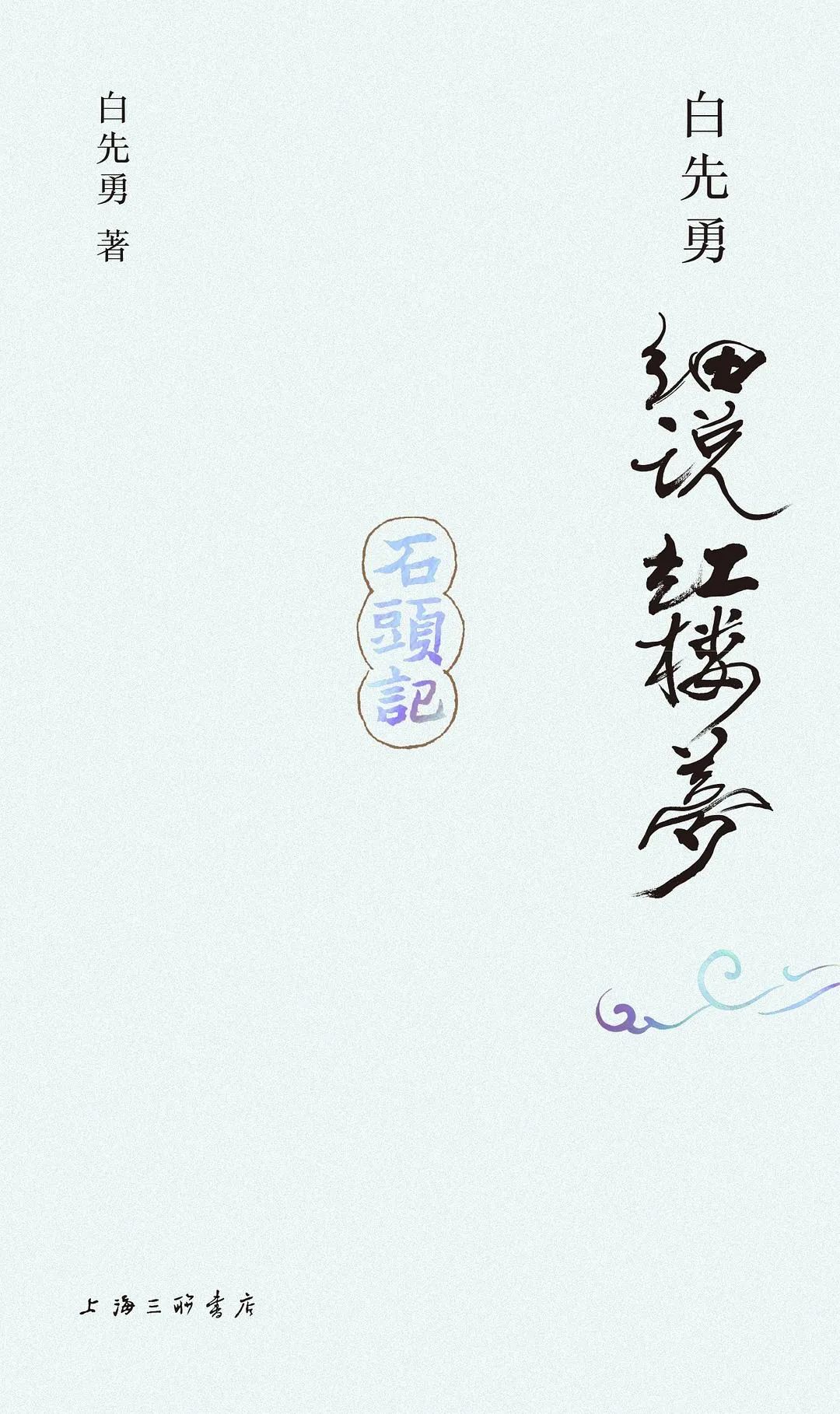
03.杜丽娘的中秋之夜
周轶君:刚才朗读的时候,李敬泽老师讲到说很多您的作品里面,包括《红楼梦》,我们都能感到那种凄美,美到极致之后的凄凉。中国人说月有阴晴圆缺,月圆了,自然的规律它就是要缺——当然我们希望它永远是圆的。包括在作品里面,我不知道这个虽然是喜庆的日子,我们也可以讲林黛玉是中秋之夜消香玉陨,然后《牡丹亭》里面杜丽娘也是在中秋之夜。为什么都要选这个月圆的日子呢?
白先勇:我觉得整个《红楼梦》这种佛道的思想非常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红楼梦》是一个佛家的预言。佛家预言里边讲,月满则缺,水满则溢。人生到了最满的时候,也就是缺的时候。所以中秋黛玉跟香菱不是去作诗去了吗?就写的是“冷月葬诗魂”。《牡丹亭》里面也是,杜丽娘在中秋的时候过世。
周轶君:本来是应该是欢乐的时候,以乐写其哀,倍增其哀。关于《红楼梦》,历史上千言万语,大家说了很多,每个人不同看法。戴老师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觉得其实贾宝玉和林黛玉是一对现代恋人,您的这个现代意义从哪里来呢?
戴锦华:先说我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不是一般的差,哈哈哈。当中国古典文化重新成为大家——夸张一点说——趋之若鹜的东西的时候,我也没有及时补课。所以我完全是作为一个个人的阅读者,对我来说,《红楼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宝玉和黛玉某种意义上是现代的个人。对于他们来说,出身,家世,他们和家族之间的关系,其他人对他们的期待,没有被他们内化,使得他们的爱情非常非常接近西方人现代的爱情,这在传统中国的文学书写当中很难见到。
当然,西方人说的所谓的古典爱情,其实是一个现代的发明。我们老以为中国人不会写爱情,西方人会写爱情,西方有爱情的传统。其实不是,古希腊西方的爱情特指男同,到中世纪,骑士的爱情其实是禁忌之恋,压抑、排除身体。我们所有的关于现代爱情的理解和想象,都是西方现代历史开始以后。
周轶君:其实刚才就是戴老师说的这个《西厢记》《牡丹亭》也贯穿在《红楼梦》里头。
白先勇:这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儒家系统,宗法社会,是克己复礼,是非常理性的。而且对于爱情,尤其男女之间的爱情要讲人伦,要讲理由的。刚刚戴老师讲到,林黛玉的爱情是现代人的个人、自我的个性的追求,的确是。我的老师,夏济安先生,他说贾宝玉是儒家社会最大的叛徒。其实《红楼梦》是儒释道的三家为底蕴,这是儒家跟佛道之间的冲突。《红楼梦》厉害的地方,是以非常活泼的人物,非常鲜活的故事来表现我们那个儒释道的玄思。
贾政跟宝玉这一对父子,贾政代表经世济民的入世的思想,宝玉代表佛道的镜花水月、浮生若梦。宝玉和林黛玉都是因为重情,两个人都是不为儒家系统的社会所融的,所以一个为情而死,一个出家了。
周轶君:昨天我在看青春版《牡丹亭》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戏文就是这样流传下来吗?因为有时候觉得尺度好大。
戴锦华:昨天我坐下来第一个唱段出现以后,就有一个非常久远的回忆出现,原来外婆说这是一出“粉戏”。哈哈哈哈,就是色情记录,就是因为这么清晰的身体的在场,以至于我才第一次的想到现代人会把它读成“恋尸癖”吧,特别清晰的去描述怎么让这个从坟里挖出来的尸身活过来。当然我也第一次开始反省,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有那个肉身登天的道家系统在,是不是其实我们以前也没有机会去认知到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这样一种特别的身体的在场,它不是一个对身体的抛弃,不是一个经过苦行最后脱离肉身,而是始终有一个身体的在场。周轶君:我跟您是同一段感受到那种惊讶的,但是我也在想,那外国童话故事不也有睡美人吗?也有白雪公主?当然没有您说身体在场的这么强烈,但是在当时来说是不是非常超前的?
白先勇:那是晚明的时代,就是王阳明的心学对宋明理学大反动的时候。那时候汤显祖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高举“情”的旗帜,情真、情深、情至。所以我们在《惊梦》两个人幽会的那一场,让那些花神在跳,变成了一个爱情神话,一种仪式性的了。我讲的他们俩人在牡丹亭上面的幽会是宇宙性的做爱。那是一种已经是升高了,所以你不觉得淫邪,因为他那个词句太美了。
周轶君:对,我只觉得震动。
白先勇:他那个时候能够塑造出杜丽娘这个人物,这了不得,一个太守的千金 16 岁就做起春梦来了,就幽会了。
周轶君:而且自证自媒,不需要别人来做媒。
白先勇:其实戴老师,其实我们中国人,中国传统也有这种很大胆、很叛逆的这种爱情。
戴锦华:就提醒我去思考这个面向,不要老说压抑。
白先勇:西方人以为好像中国人都是规规矩矩的,这种是完全误解的,我想。所以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演出,在英国演出,他们真的大吃一惊,他们没想到原来在比他们的歌剧早几百年的时候,我们有这么大胆、这么成熟、这么精微的歌剧形式。我们在美国演出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研究希腊悲剧的加州大学的教授,他说这是我一生看过的最伟大的歌剧。他还说,可能西方人没想到,他们只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我说罗密欧与朱丽叶死了,回不来了,杜丽娘和柳梦梅爱的死去活来,死了之后活过来还要继续谈恋爱。
周轶君:所以现在也有人说王阳明是一段“迷你文艺复兴”,甚至认为他应该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机会。最后希望大家在这个中秋节心中有光明,爱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