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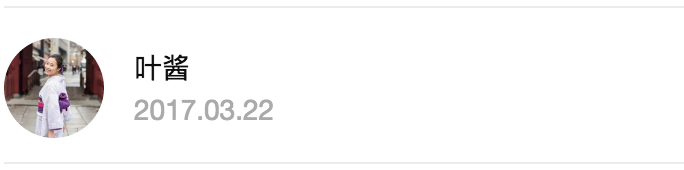
印度就是咖喱吗?相信没去过这里的人,都无条件举手同意。我住过好几次香港重庆大厦,空气里一直漂浮着咖喱味;还有新加坡和日本的羊肉咖喱鱼肉,美味得很;至于斯里兰卡的咖喱大螃蟹?我吃一个月都不会腻!
就是怀着这样的自信心,我胸有成竹地飞到了南亚大陆,准备开启发源地的寻味之旅。
可在印度吃了几天,那点自信心早被碾碎成粉末,无论点什么,全都是一坨颜色可疑的糊糊,而且又油又香又辣,哪怕十几种食材和香料混在一起,最后都能翻炒出一个味来,就是辣椒味!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来到了一个假印度?此前十多年的那些咖喱鱼头、鸡肉咖喱饭大概都白吃了。

路边蔬菜沙拉摊 by 苏岩
事实上,与咖喱牛肉、鸡肉、各种肉不同的是,印度是世界上吃素人数最多的国家,大约四分之一印度人食素,而且种姓越高,吃素的比例越高。比如婆罗门,作为印度四个种姓里面最高等级的一类,他们带有雅利安血统,现在很多是知识分子、宗教职务人员和公务员等。婆罗门认为吃素是高贵的象征,以便于把自己和别的种姓区分开来,孟买滨海大道附近甚至修建了纯素食高档小区,入住者多为上流社会的婆罗门和刹帝利家庭。
印度认为肉是肮脏的、下等人吃的食物,会阻碍精神的发展和个人修行。圣雄甘地都说了,吃肉虽然使人强壮,同时会唤起凶残的兽性,人类只有舍弃食肉减少兽性,才能带来和平。

果汁店
素食也是这片多种族多宗教土地上人们和谐相处的一种方式。
占人口总数80%的印度教徒把牛奉为神圣,不食牛肉已是共识;而信仰伊斯兰教的信徒约有1亿,他们根据教义不吃猪肉;耆那教更极端,有关杀生的东西一概不能食用,好多高级教徒选择裸体,只因为衣服上可能会带有细小的昆虫,肉、鸡蛋甚至不少蔬菜都在禁食范围内。这样下来,已经没剩下多少选择,只有平庸的鸡肉和昂贵的羊肉不与多数宗教产生冲突。
一般来说,素食主义者分全素、锅边素、蛋奶素等形式。
绝大多数印度素食者实行 Lacto (奶素)。也就是说,奶制品全都算素食。他们认为公牛耕地、母牛产奶,神牛供给人们食物,让土地富有活力,自然不能吃。但奶制品在精神上却是纯净的。东亚素食者就依靠花样百出的豆制品,从不缺蛋白质的补给,而在印度,替代品就是 Masala Chai (玛萨拉奶茶)、Lassi (酸奶)、奶酪和炼乳甜点。去餐厅点一盘菠菜奶酪咖喱,尽管名义上是素的,但配着馕吃还是肉欲感满分。

玛萨拉咖喱套餐 by 苏岩
有必要先澄清一个概念,所谓咖喱,即 curry 的音译,实际上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词汇,统称看起来湿哒哒黏糊糊的黄色系菜肴。在印度其实听不到这种叫法,假如你随便跑进一间餐厅翻开菜单,上面写满密麻麻的英文单词,却不会有 curry。
这些词大多来自印地语的发音,直接音译成英文字母,像密码一样排列组合,难道以为转换成字母就能让外国人看懂了?直到我在印度待了一个月后,才终于掌握了一些破译的线索,那个关键核心词汇叫 Masala。
Masala 本意 “混合香料”,没有特定的组合和比例,黑胡椒、姜黄、小茴香籽、罗望子、芫荽籽、小豆蔻、番红花、肉桂、辣椒……有点儿像巫婆举着一把大勺子,在烧得滚烫的大锅里调配神秘药房,最后出锅的玛萨拉咖喱是黄乎乎一团,可能需要打开200瓦的日光灯,再拿一个显微镜才能搞清楚里面放了什么。
可看清放的啥有什么必要呢?印度菜的精髓在于,你永远不能只用眼睛,而是要用舌头去感受它。香料的魔法就是要让平淡无奇的蔬菜焕发出香喷喷的肉感。为此我辗转在印度不同城市尝试 :土豆番茄咖喱、番茄花菜咖喱、土豆花菜咖喱、胡萝卜土豆咖喱、茄子胡萝卜咖喱……

误入的婚礼现场晚宴
我并非无肉不欢的肉食者,但离清心寡欲的苦行僧还差了一大截。我甚至不惜厚着脸皮闯入当地的婚礼现场,很快东道主过来搭话,“你来自哪里?” 他指指台上的歌舞表演,左右摇晃着脑袋,“要不要一起上去跳舞?”
“no、no、no。” 在一群马路中央都能开跳的舞蹈高手面前,我可不敢献丑。
“那请随意享用我们晚餐噢,欢迎你们。” 东道主指指旁边的宴会区域,那里摆着几十种咖喱和小吃甜品。
就等你这句话了,我心想,婚礼上一定能吃到最地道的印度菜,说不定还会有些奢侈的鸡鸭鱼肉。事实证明我想多了,这里根本没啥能吃的东西。婚礼是整个家族大聚会的时刻,无论是东道主还是客人,都想着表明自己的精神修养和身份。跳舞都来不及,谁会在众人面前大快朵颐。

一起下厨的北京大哥
意志薄弱的自己很快放弃了对素食咖喱的尝试,于是我决定,买菜下厨做饭!
旅舍的厨房要优先给点餐的客人做菜,交涉许久,小哥终于同意我们在下午3到4点之间使用,时间和材料都有限,只好做了个胡萝卜青椒土豆丝、黄瓜番茄蛋花汤、蒜末炒绿叶菜,用中国式煮法做了一大盘米饭。看起来全素,但至少菜有菜味,蛋有蛋味。
隔壁桌是旅舍老板和一帮朋友在喝啤酒,花衬衫、太阳眼镜、紧身牛仔裤还有尖头皮鞋,看起来都是见过世面的纨绔子弟。我赶紧分了一点菜过去献殷勤,“尝尝中国菜吧,大家都是素食者么?”
花衬衫老板梳着油光光的飞机头,拍了拍旁边皮衣小哥的肩,文不对题地说,“他之前可是在新加坡的日本料理餐厅工作呢,是很棒的厨师。”
尝了一口胡萝卜土豆丝,大概是难得吃到这么朴素的蔬菜味道,花衬衫老板来了兴致,“美味极了,中国还有些什么有名的菜?明天再给我们做吧!”
“宫保鸡丁、红烧羊肉、水煮牛肉……” 我把流了几天口水的荤菜全说了一遍,“你们能吃?”
“我们什么都吃。” 皮衣小哥咯咯笑着,一大口啤酒灌下去,对大白天喝酒这件事也毫无顾忌,“我最喜欢吃日本的叉烧拉面了!”

街头神牛
印度教不能喝酒,卖酒的小店也搞得偷偷摸摸。我买过一回,跟老板之间隔着一层防盗窗,得把手伸进铁架子里拿酒。一个东倒西歪的醉汉还能认真去庙里冥想么?素食是一样道理,肉吃多了会沉迷于这种口腹之欲,哪能好好修行。
而这些频繁出国的印度年轻人观念大胆开放,在当地开间旅馆、做些生意,打扮时髦的他们追逐的是另一种生活态度 :百无禁忌。
我在火车上碰到的一对年轻夫妇却截然不同,他们来自门当户对的知识分子家庭,传统而虔诚,说着一口没有口音的流利英文,愿意和我探讨深刻的文化问题,可惜最终以我听不懂的深奥单词结束。
女孩对于我提出的素食问题思考良久 —— 也许在此前人生的20多年里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从小家里就吃素,对肉类没什么感觉,有没有都无所谓,也并没有特别去克制自己。”
“杀生会加深罪孽”,这是国内大多数素食者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在印度这反倒是最少听到的理由。
他们对动物的仁爱体现在满大街悠哉生活的流浪狗和圣牛,还有专门被供养投食的老鼠,食素关乎个人修养和家庭传统,久而久之成了习惯。不知肉味,自然不会有念想,欲望只不过因为知道得太多,体验得太多。也许在印度大陆上感受到的那种原初性正来源于此,无论哪个种姓和阶级,欲望都被深深地压缩了。

乌代普尔菜市场 by苏岩
在蓝色之城焦特普尔就没那么好运了,我不小心住进了一间建在印度神庙旁的旅舍。提着鸡蛋走进厨房时,就被旅舍经理拦截住了,“这个厨房是全素的,鸡蛋不可以拿进去!” 平时嬉皮笑脸的印度人,说到宗教时,立刻拉长了一张脸,像一尊神像。
如果放在别的地方我可能还会据理力争几下,但在印度,碰上了宗教和信仰,哪有理可以说?乖乖地回到卖鸡蛋的小摊,让老板给我做了个煎蛋卷安慰自己,此时我还不知道,下一站普什卡是个吃煎蛋卷都难于登天的地方。
普什卡是印度的迷你圣城,城区围绕一池湖水而建,周围拥着四百多座神庙,街小巷里晃着的大多是年过半百的老年嬉皮。问题是,普什卡比瓦拉纳西还自我要求挺高,全城素食,连鸡蛋都禁止。

偷偷卖鸡蛋的 “黑店” 菜单
我在嬉皮士们长待地方,跟煎蛋卷杠上了。一大早,我就开始挨家挨户打听,“哪里可以吃到鸡蛋?” 有的店主对我大逆不道的要求严词拒绝,有的含糊不清地向我推荐远方的另一家餐馆。终于,在靠近湖边的地方,老板神色慌张地把我拉到一边,打开菜单,指着一堆英文字母乱码,朝我得意地微微摇头。
此时我已深谙这门肢体语言,印度人摇头代表 “是”,我惊喜地大叫起来,“真有吗?”“嘘!轻一点。” 面对不知好歹的客人,老板也有些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