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图
父亲是怎么度过他生命中最后两个月的呢?吃不下去,也得吃一点;喝不下去,也得喝一点。每一天他都不敢闭眼,不敢睡着,生怕就此去了。他忍着不死,直到我考完试的那一天。
1980年,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三年,不足16岁的我从一所叫做潘昶中学的农村学校毕业了,同届学生150多人中有3人考大学,我是其中之一,报了文科。结果成绩最好的我距分数线差13分。
复读一年再考,差2.5分;再复读,差6分。
考分年年涨,但总是距那个不断升高的分数线差一点。舍弃,不甘心;继续拼,结果不可预料。
更加悲剧的是,再过一年,高考外语成绩的70%将计入总分,可我一天英语都没学过,拿五门课和别人六门较量,希望更渺茫了。
不断失败的屈辱,身心俱疲的熬煎,还有身后贫困的家庭。好多个夜晚,我独自躺在自家的房顶上,面对深邃夜空和灿烂星河苦苦思索,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
可生产队早就就盯上了我这个劳动力,每年7月9号高考结束,10号就会招呼我出工劳动,与我家素有嫌怨的队长潘瞎子更是在多个场合冷嘲热讽:“鸡窝里是飞不出金凤凰的。”
曾经以我为骄傲的父母在我一连三次失败的打击下,眼中的希望之火也渐渐黯淡了。
哥哥在家务农自不必说,妹妹读完初中,大弟只上了三年学(前者没考上,后者不想上)就都回家劳动了,而十八岁的我还在吃父母的,用父母的,如今甚至吃起了弟弟妹妹的。
这样继续“偏心”下去,做父母的就算没有责备过一句,但肯定也很是为难。
我心中满满地都是“放弃”两个字,但我说不口。整个假期里,我都不再翻书,不再看复习资料,一心想用繁重的体力劳动封存自己那些“非分之想”,用行动让自己臣服于命运的重压。
那年麦收结束后,我带着三个初中生去放着生产队牲畜圈里的近四十头牛马驴,三个小的每人每天记4分工,给我记6分工。开学了,他们都去上学,由我一个人负责所有的牲畜,可工分还是6个。
我觉得不公平,找潘瞎子要求加分,不允;换干其他农活,不许。我和那可恶的村霸大吵了一架,可能父母也在激愤中改变了主意,想让我再去复读一年。
我还是犹豫不决。正巧,我的一位考上中专,毕业后分配回母校当老师的同学来看我,成了父母的劝我再次复读的救兵。
无奈中,我决定再一次背水一战。
这一年,全县教学质量最好的贺兰一中招复读生,我凭借着较高的高考分数插进了全县名师张宪达老师的文科班。
我家距县城大约九公里,三公里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六公里是疙里疙瘩的石子铺就的公路,家里的一辆破自行车是我每天丈量这段路程的唯一依靠。
早晨五点半起床,吃点昨天的剩饭或带个馒头就出发赶路了。每天都是一身大汗,但我总能在晨读之前到达。中午,在街上花两三角钱买个饼子或两根卖剩的油条,勉强充饥后,继续回教室学习。

△学生时代的作者 作者供图
九、十月天气还热,补了又补的自行车残胎,经太阳一晒,动不动在半道上就没了气,我只能推它回家。走着走着,天就黑了,可偏偏有一段路要从一丛坟边经过,黑黢黢的小路上,只我一个人,远处村庄闪烁的灯光是我能找的到,消除内心恐惧的仅有。
进入十二月,衣衫单薄的我又要顶着西北风艰难前行,手脚冻得失去知觉了,只好推着自行车跑着取暖。让我聊以自慰的是,步入正轨的学习后,成绩也在不断提升,这让我每天都信心十足。
● ● ●
可也就是在那个冬天,就像升起于贺兰山头正在酝酿一场暴风雨的乌云,一个巨大的灾难扯天扯地一般,向我和我们家倾轧过来。
自麦收后,父亲的胃就不太好,家人都以为不过是老毛病犯了,和以往一样,吃点中药调理修养几天可能就没事了。可是这一次似乎很不寻常,他熟识的本地有名的大夫瞧遍了,两多个月里吃下了几十服中药却一点未见效,反酸、打嗝、吞咽困难,一天比一天严重。亲友都劝父亲到县里或省城的大医院去看,他坚决不去。
“外人怎知我家锅小碗大?”一家人在一齐说起他的病时,父亲说:“刚给老大定了婚事,还想着借些钱,看年底能不能把婚给结了。谁都知道大医院好,可是我们花不起钱啊!”
于是,有胜于无,父亲的病就这样拖着。家里越来越重的中药味也似乎终于聚集到了一个爆炸的燃点。
十二月初的一个晚上,父亲辗转反侧,他极力压抑着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突然一个侧转,趴在炕沿边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
母亲、大哥和我惊恐万分,手足无措,被吵闹惊醒的弟弟妹妹看到眼前境况也吓得不敢出声。待父亲咳喘稍稍平静些,母亲毅然做出了决定:“套车,上县城!”
那年冬天,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在家乡推广开来,我家分到了一匹马和一辆架子车,没想到第一次使用竟然是为了这个。我和哥哥一阵忙活后,才把马车套好,我们往车厢里垫了些麦草,铺好被褥,垫了枕头,大哥把父亲背出来放好,全家人摸黑出发。
还是每天上学我得走两遍的路。母亲和大哥分坐在车辕两侧,我骑自行车跟在后面。父亲一言未发,赞成也好,反对也罢,都无力表达了。两个多月里,他早已被病痛折磨得面黄肌瘦,大量失血后,几乎是奄奄一息了。
住进县医院后,首先是止血,然后是输血。大哥和我都验了血型,抽了大哥的500毫升后,医生决定视情况再考虑是否抽我的。那时候,我一米七的个头,一百零几斤的体重,艰难而漫长的求学之路已经让我形销骨立了,大哥的血输了进去,父亲看起来稍稍好了些,便坚决不同意再抽我的血。
一周后,父亲出院了。中午放学,我从学校赶过去时,母亲和大哥已把出院手续办妥了。到头来也没查出什么病。
主治大夫和父亲很熟,他特意赶过来叮嘱:“胃出血绝不能有二次、三次,一定要到银川的大医院检查治疗,不得延误。”
1982年,农民开始为自己种地了。和所有村民一样,以往的冬闲在那一年突然就变成了冬忙,每人心中都燃着一团火,就连病中的父亲都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把我家分到的二十三亩多地逐个查看了一番。
进入寒假,白天,我们弟兄和母亲一起平田整地,蓄积农家肥,为春天的到来做准备。晚上,不管白天干活有多累,我总要学到12点以后。
父亲回家后又调养了两三周,病情依然没有好转。他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去银川查病。一周后,结果出来了——喷门癌中晚期。
那时候,“癌”对乡村来说还是个新名词,得了癌症,也就相当于老天爷判了死刑,更何况还是“中晚期”。第一次听到这个恐怖的病名,也就是从父亲口中而来。
然而回到家后,父亲却平静地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他把从医生那听来的情况转述给全家人听,而后,他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春节后去住院,做手术。”
这一年,我家没有春节。父亲忍受着病痛,整夜整夜地长叹。43岁的母亲几乎在几天内,头发就白了一半。
手术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做,时间定在2月12号,由母亲和大哥陪侍。我在家带着弟妹干农活,等待开学。
三十多年前的医疗技术和今天本就无法相比。五叔说,手术前要求家属签字时,大夫再次告诉他:成功率可能不到50%。可是父亲还是毅然把自己送到了生死不可预知的手术台。
三周后,春耕在即,大哥回来了,只留下母亲一个人陪侍。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伤口不愈合,治疗时间延误太久,医生认为情况很悲观。”
● ● ●
三月中旬一个周末,我放学后直接从学校去了医院。一个多月未见,父亲已是骨瘦如柴了。他的伤口依旧发炎流脓血,身上插了两个管子往排积液。然后就是输液,不断地输液。人还清醒着,只是已经要靠注射吗啡止痛了。
我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在卫生间哭过之后,我把自己弃学的想法告诉了父母。
半靠半坐的父亲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瞬间,他的眼泪从眼角涌了出来,顺着瘦削的脸颊流进了好久未剃的胡须。母亲见状,把我扯到了病房外。
原来,这些日子里,关于我考学的事,他们已经不止谈过一次了。父亲觉得他的病影响了我,可能会让我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也因他的病而泡汤。
“他本就自责,你现在提这事,他能不伤心吗?”母亲说完,告诉我他们的决定:“剩下三个多月了,没商量头,必须坚持到底!”
到了四月中旬,麦子开始施肥灌头水,能否及时灌上水,将影响一年的收成。偏偏这时父亲连续病危,哥哥也去了医院,这任务只有我和弟弟妹妹们承担了。
低洼的田块方便引水,她俩白天能解决,靠近大渠的四亩地特别高,要想浇这块地,必须要在渠水多的时候下满闸,才能把水蓄积到足够的高度。
晚上10点我去查看,渠水小,要浇地的多,我们没机会。夜里三点,我和弟弟再去,水大人少,我俩就在闸里插好木桩,填了两捆麦草,水一会就流到了地里。就在我们暗自庆幸的时候,渠北邻村的一个中年人走过来,他扔下肩上的铁锹,就要拔挡麦草的木棒。我好说歹说央求他都不行,一急之下,我直接跳到了闸里,他才无奈地放弃。
那是四月天的后半夜,水冷得刺骨,我从脖子深的水里爬出来,冻得上下牙磕得蹦蹦响。水浇完了,天也亮了,回家换身衣服,我再往学校赶。
在医院的父母得知此事,又是担心,又是心疼。父亲对自己的病情很清楚,他早几天就闹着要回家,听了这件事,更是一天都愿不住了。
这时候,主治大夫也把父亲的病情给母亲和哥哥交了底:“已经扩散,住下去没啥意义了,开些药回家静养吧,也就是这一半个月的事了。”
走着进去,躺着出来。五一前,父亲回家了。一箱要输的葡萄糖和几盒止痛用杜冷丁针剂是医院能给的最后的交代。
为了便于洗脸喂水,也便于插在他身体里的两个排积液的管子能通到地上的瓶子里,父亲被横着安置在正屋的大炕上。他已经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了。这也是父亲的意愿——这样,他可以尽可能多的看看早出晚归的儿女们。
人世间最残酷的事莫过于一家人看着自己的亲人一步步走向生命的边缘,却无法施与援手。疼痛让父亲整宿整宿地睡不着,不断的发出呻吟,他一般都是吃去痛片死扛,实在忍不住了,才会让大哥给他注射杜冷丁。

△作者的父亲 作者供图
这样的环境不要说学习,就连睡觉休息都成了问题。几天后,父亲的朋友,我曾经的班主任王老师来看他时,直接建议父母,让我最后两个月住校。
“五一”以后,天气已经很热了,而那一年,我一件夏天穿的衣服都没有。
一年前,从河北流浪到宁夏的朋友小侯曾借住在我家,后来他在附近一个砖窑打工,得知我的难处,他把自己仅有一件能穿出去的半新的确良黄军衣送给了我。
带了些简单的生活用具,我挤到了学校简陋的大通铺宿舍里,两间房除了狭窄的过道全是床,总共住了15个人。学校食堂一日三餐基本不变,馒头黑,菜汤寡淡清亮。就是这样,我也不敢三餐都吃,仅有的三元五元钱也都是亲戚接济的,父亲的病不仅耗光了本就很薄的家底,我们还欠了医院2800多元。
本就出生于贫寒之家,这样的苦日子算不了什么,但母亲却常常暗自流泪,她最担心父亲不能挨到我考试结束。然而,当全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父亲那边时,我却突然倒下了。
那是六月里,随着考试的临近,我学习越发刻苦了。教室里的晚自习只上到九点,就关灯锁门,宿舍给电也只到九点半,我和几位同学在月亮好的夜晚,常常在空寂的操场记诵。月亮利用不上时,我们就到街边的路灯下,口中念念有词到十一二点。
饮食低劣,睡眠不足,天气炎热,外加高强度的学习,一天中午,我在教室的座位上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醒来时,人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从头到脚全湿透了。怕出意外,张老师安排两位同学把我送回了家。
在家只休息了一天,我就坚持要回校,父母没阻拦,只是叮嘱我别太累了,并把最后的三瓶葡萄糖交给我,“到医院输,或者把它喝了。”
正常情况下,医院开的葡萄糖早该用完了,可是据母亲讲,村医说父亲的身体已经输不进去了。维持父亲生命的,就是水和少量的流食。
看着正凝视我的父亲,我不敢多问,含泪回了学校。那一天,九公里的路,我走了很长时间。
7月9日下午考完最后一门,我心急火燎地往回赶。五点多,我径直走到父亲身边。
夏收已经开始,家里只有母亲陪侍。父亲问考试情况,我给了肯定性的答复后,却不敢直视他的眼睛。我心里真的没底,我知道,这么多年了,他可能也不信。
母亲在一旁赶紧岔开了话题,“天热,你去打盆水,给你爸擦把脸吧!”
父亲病了几个月,我还是第一次给他做这件事。
我看他凹陷的双颊有了些许血色,精神状态也比往常都要好,就说了些安慰他的话。但父亲好像早就盘算好了似的,话题转了个弯,很快就又回到了考大学的事情上了,父亲盯着我的脸说:“娃呀,你考上了,就去好好上;没考上,就好好帮着你妈。你哥的婚事已经订妥,房子有了,该花的钱基本花到位了,迟早一办就没事了。你妹妹过两年就能嫁人,我不牵挂。只是老三老四还小,不指事(不顶用)呀……”
一阵轻微的咳嗽,中断了父亲似乎未说完的话,看上去他已是拼尽所有气力,粗重的呼吸引得炕沿下盛积液的瓶子咕嘟咕嘟地不断冒着泡。
我一边拿沾水的棉球湿润他嘴角脱不掉的干皮,一边使劲地点头。
我知道我必须承诺一切,但无论如何我都想不到,这竟然是父亲的遗言。34年来,那天下午,他对我说的每一字我都铭记在心,那情景在我的脑海中也不知回放了多少次,总觉得这不应该就是我和父亲最后的诀别。
或许,我走出考场的那一刻,父亲也如释重负了吧。
当天晚上12点多,我在昏睡中被母亲摇醒,“快起来,你爸走了。”
按大夫的判断,父亲至少多活了一个月。癌症病人由先前的求生到后期求死,有太多太多的例子了,那种痛苦不敢想象。父亲是怎么度过他生命中最后两个月的呢?我不敢想。
安葬了父亲,顾不上悲伤。二十多亩地的麦子从割、捆、拉运、堆垛到脱粒,再加上抢种晚秋作物,我们一家人像疯了似的起早贪黑忙碌着。要不是别人提醒,我几乎忘了23号是高考成绩公布的时间。
最后一次,我骑上了我的自行车,走过那段渗透着我汗水和泪水的九公里路。忐忑不安中,我走走停停,到了县城已经将近10点,我还是不敢走进校园。终于在进进出出看成绩的同学中,一个高中同学看见了还在校门口小巷里徘徊着的我,喊道:“快进去看吧,你考上了!”
我真的考上了!比前一年高出75分,高出当年宁夏录取分数线27.8分。“从龙门之约,到今天成功,整整四年,我等得太久太久了。”我在心里呐喊着。
我真的考上了!九泉之下的父亲,你听到了吗?
那一天,万里无云。多少日子了,我第一次抬起头看了看县城的青湛湛的天空。
编辑:罗诗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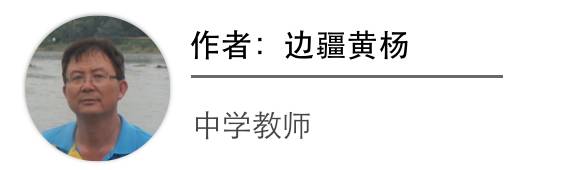

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工作室,可致信:[email protected],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千字500元-1000元的稿酬。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人间,只为真的好故事。
网易非虚构写作平台
只为真的好故事
活 | 在 | 尘 | 世 | 看 | 见 | 人 | 间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回复以下「关键词」,查看往期内容:
祭毒 | 窥探 | 南航 | 津爆 | 工厂 | 体制 | 马场的暗夜
抢尸 | 形婚 | 鬼妻 | 外孙 | 诺奖 | 子宫 | 飞不起来了
荷塘 | 声音 | 女神 | 农民 | 非洲 | 何黛 | 切尔诺贝利
毕节 | 反诗 | 木匠 | 微商 | 告别 | 弟弟 | 最后的游牧
行脚僧 | 北京地铁 | 高山下的花环 | “下只角”的哀怨
华莱士 | 创业领袖 | 天台上的冷风 | 中国站街女之死
褚时健 | 十年浩劫 | 张海超托孤 | 我怀中的安乐死
林徽因 | 口水军团 | 北京零点后 | 卖内衣的小镇翻译

▼更多“人间”文章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