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的生命周期有
三个阶段
:
先通过胞吞或是膜融合,
侵入宿主细胞
;
然后利用宿主的细胞器,进行
转录
和
翻译
,
复制增殖
;
最后
装配加工
,
生产并释放新的病毒
,开始下一个轮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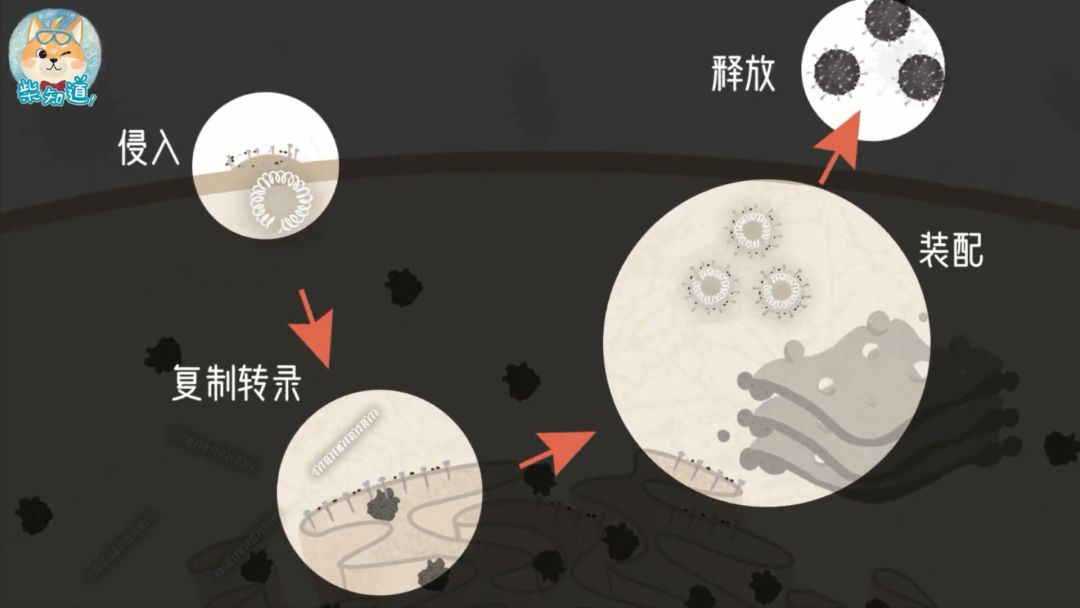
想要杀死病毒,最直观的方案是用
抗病毒药物
,直接阻断病毒的繁殖。
它的关键,是找到药物的
作用靶点
。
理论上讲,病毒复制周期里的每一个阶段都能成为靶点。
比如
恩夫韦地
这样的“
膜融合抑制剂
”,就是把细胞膜融合过程作为靶点,
不让病毒进入细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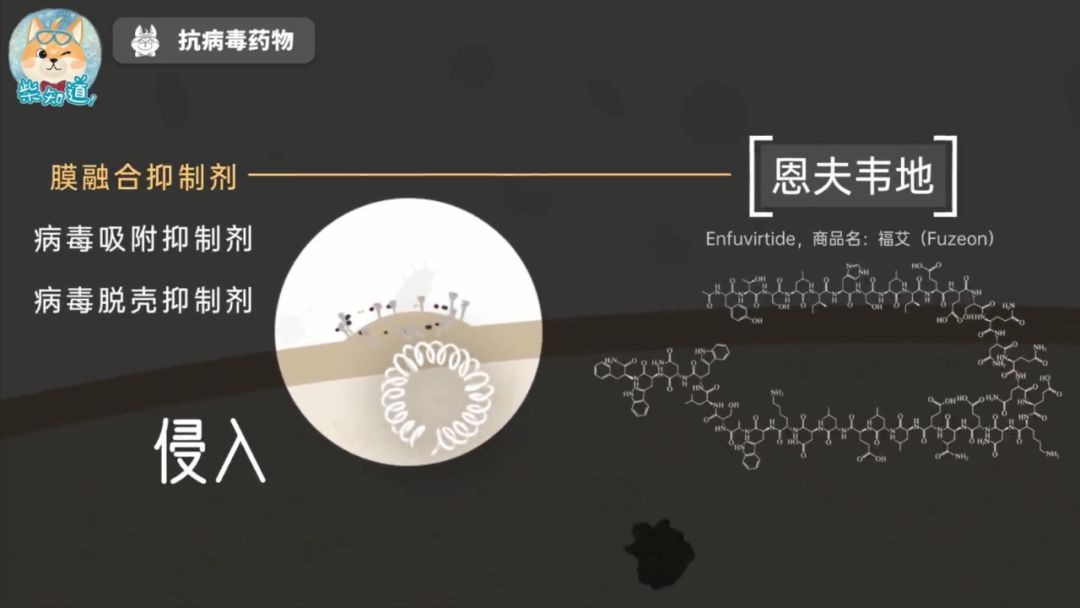
齐多夫定
这样的“
RNA聚合酶抑制剂
”,就是把病毒RNA的逆转录作为靶点,
不让病毒复制增殖
;

利托那韦
这样的“
蛋白酶抑制剂
”,是把新病毒的装配释放作为靶点,
不让病毒跑出细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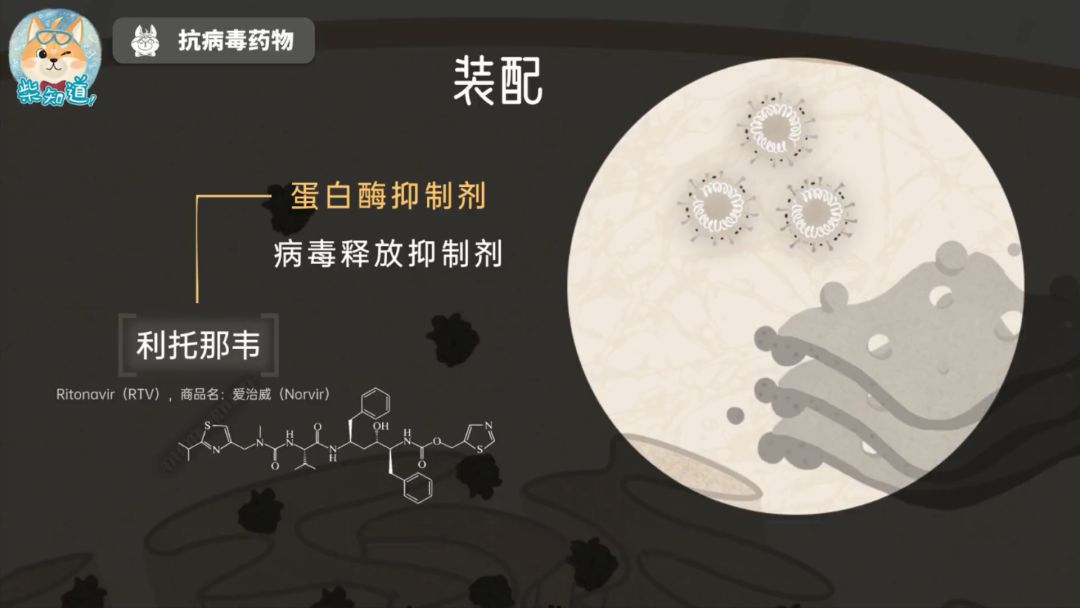
对于那些极难对付的病毒,还需要
多种抗病毒药组合调配
,才能有较好的抑制效果,比如治疗艾滋病时就经常会用到
鸡尾酒疗法
。

但
研发一款新药非常复杂
,需要这一系列复杂的试验,再加上四期临床试验,和一系列审批流程,需要三五年乃至数十年才能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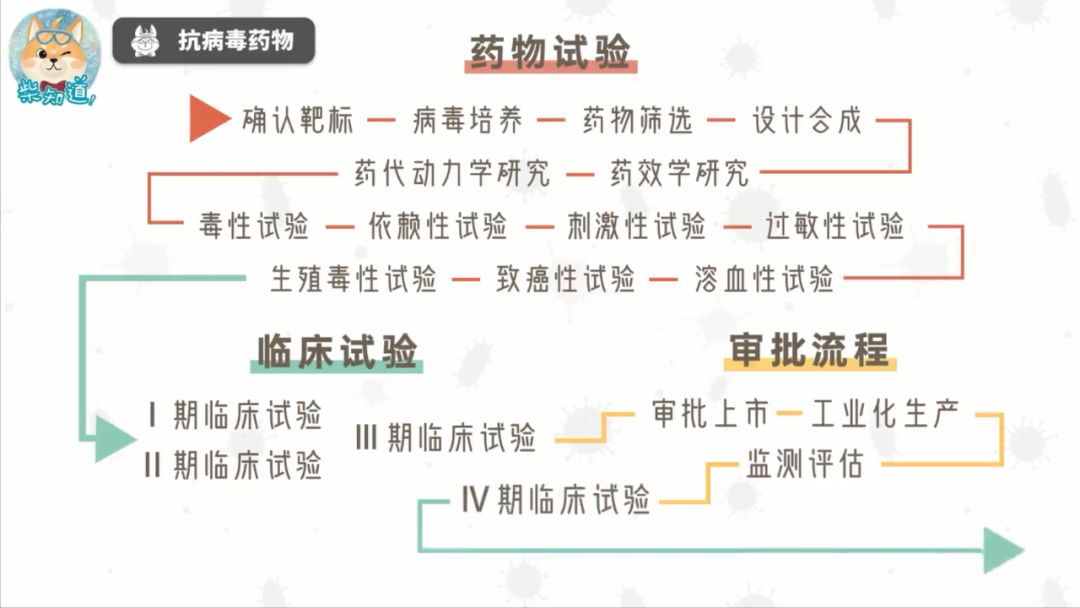
所以面对猝不及防的疫情,更实用的方法是
从已上市的药物中去寻找可能的答案
。
比如第四版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中,就将
利托那韦片
列入了治疗方案。
这款药物属于
蛋白酶抑制剂
,原本用于治疗艾滋病,但此前
对同属于冠状病毒的 SARS 和 MERS 病毒都表现出了抑制能力
,那么也许同样能在这次疫情中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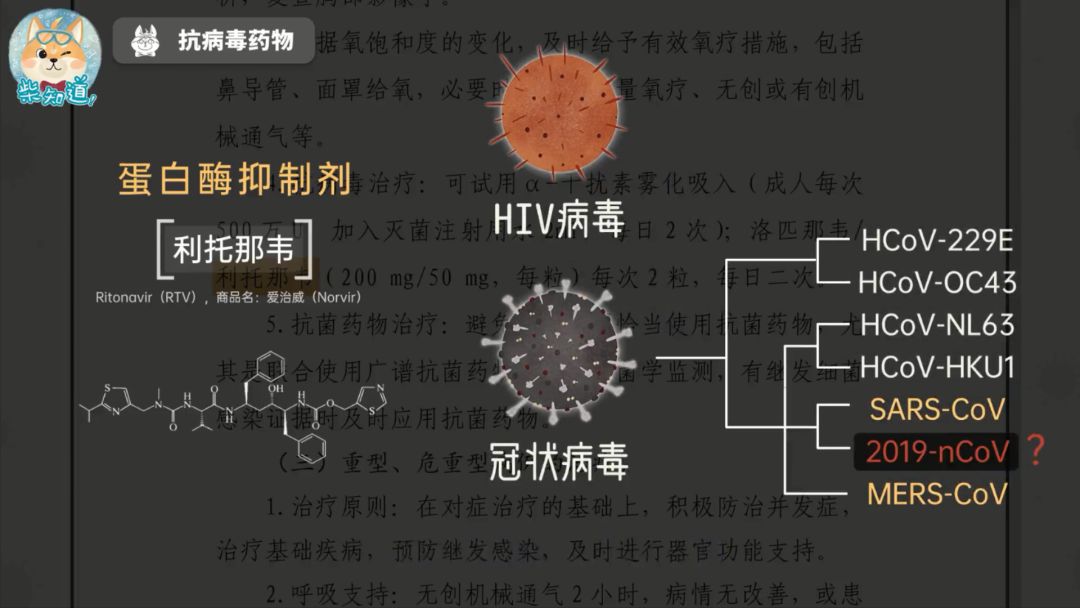
由于
SARS病毒和新冠病毒在两个药物靶点上高度相似
,所以也有论文推测,四种曾用于治疗SARS的药物,或许在新冠肺炎疫情时也能派上用场。
而其中的
瑞德西韦
也确实在美国的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展现出了不错的效果。
于是中国的医疗机构也开始做临床试验。
但由于样本太小,我们
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些药物是不是真的有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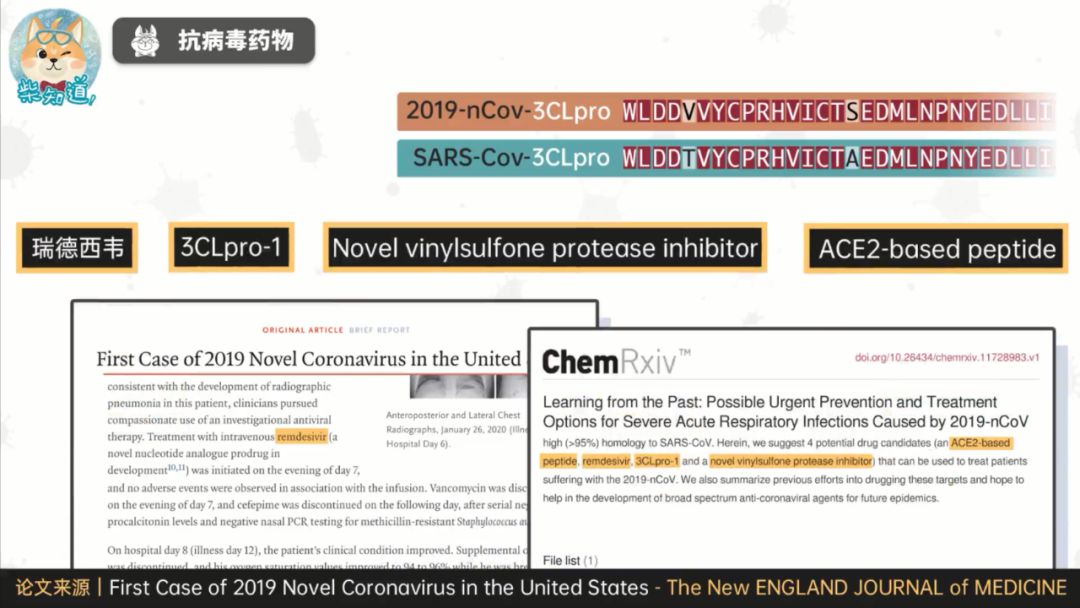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
RNA单链病毒
,
冠状病毒非常容易突变,产生耐药性
。
所以即便研发出了合适的抗病毒药物,也
只能在短期内起到抑制作用
,一旦幸存下来的病毒产生耐药,原有的特效药就失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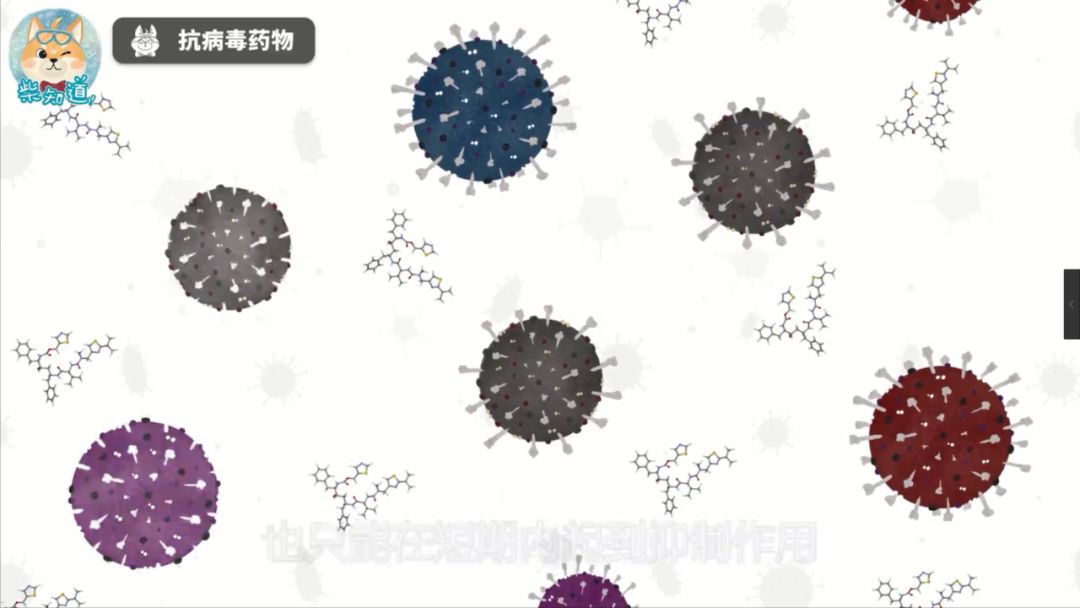
而且对于传染性强的病毒,医疗体系也很难保证所有患者都能得到及时用药,
一旦发生大范围传播,再有效的药物也无济于事
。
实际上直到目前,
抗病毒药物还没有真正消灭过任何一种病毒
,只能尽量抑制患者体内病毒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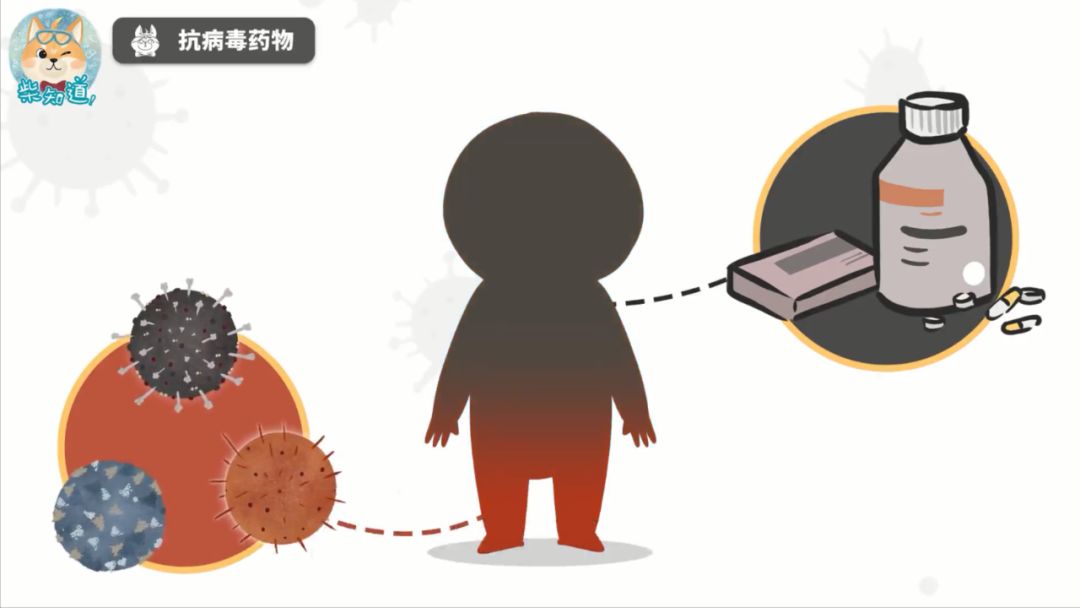
至于
疫苗
,它也和抗病毒药物一样,需要
很长的研发周期
,和
很多很多的钱
,来不及应对迅猛的病毒。
实际上,
在SARS疫情爆发17年后的今天,人类依然没有应对它的特效药
,疫苗也只完成了第一期临床试验。
也许,它们永远都不会问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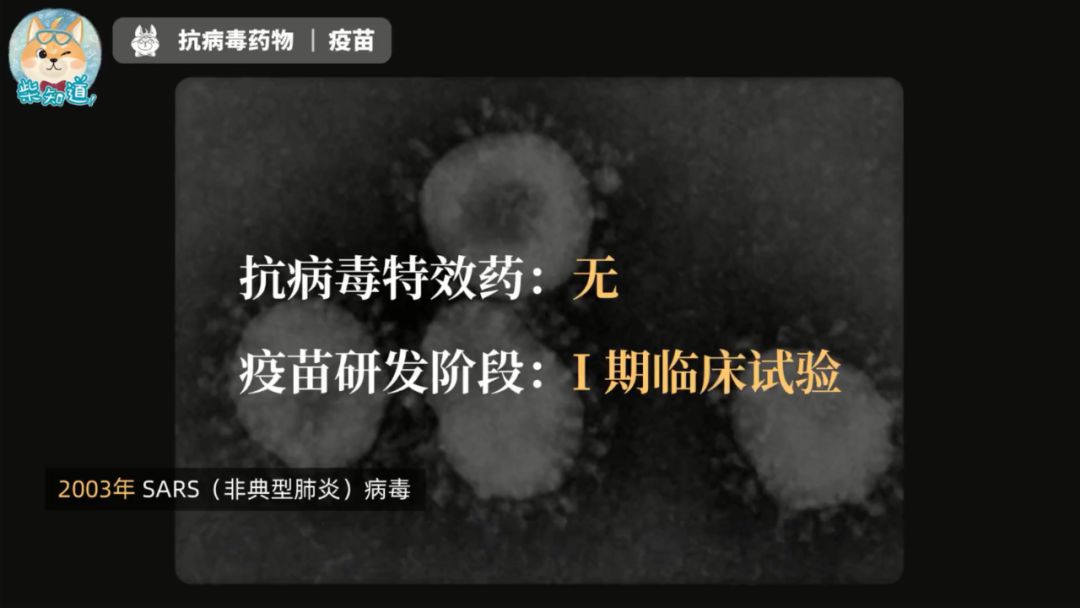
远水解不了近渴,在突发的疫情面前,比药物更管用的是人体自身的
免疫系统
。
翻开SARS肺炎和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你会发现其中最主要的方案是
对症支持治疗
:如果感染者高烧不退,就用
退烧药降温
;咳嗽太狠,就
用药止咳
;
如果呼吸不畅,就
用
呼吸机通气
;
同时
控制其他可能的并发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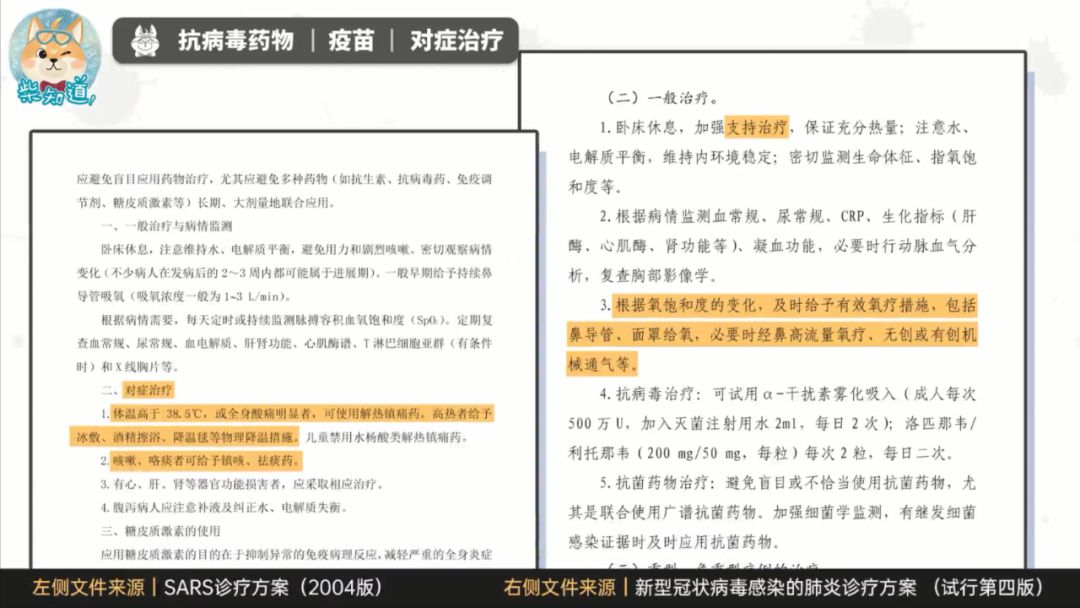
对症治疗
只针对疾病的外在症状,但不直接针对引发疾病的病毒本身
。
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案,是为了维持患者身体的正常运转,
用现代医学来辅助人体的免疫系统
,杀死病毒
。
事实上,
在大部分病毒类疾病中,
对症支持治疗
都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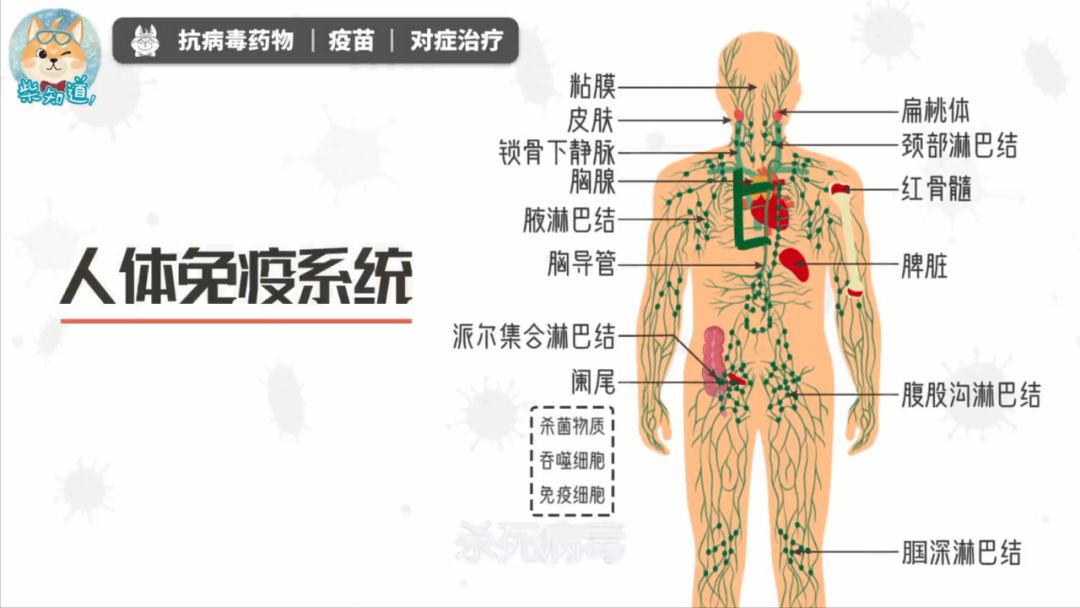
说到底,就像在亿万年的进化中无数次发生的那样,这是人类的免疫系统和病毒的又一场贴身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