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书单
丨
2018年2月-3月书单
丨
2018年4月书单
丨
2018年5月书单
丨
2018年6月书单
丨
2018年7月书单
丨
2018年8月书单
丨
2018年9月书单
本月读书二十本,要想办法看到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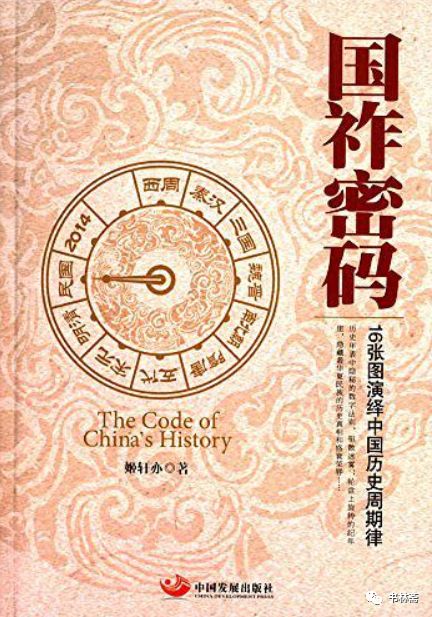
四年来第三次阅读了,本书的结论我拒绝了四年,然后最终开始信服。
当年读了姬喵一个答案去注册了某网站的ID,后来他出这本书时便立刻购来阅读,粗看似乎是看明白了,却怎么也不敢相信。
然后我没有再读过,但这本书的内容却一直在脑海中徘徊,一直在咀嚼,虽然始终在拒绝,但却经常会想到这些东西,直到去年年底遇到姬喵和他长谈了一次后,我重新拿起了这本书。
然后我开始阅读这一年多来所涉及到的两个新领域,终于不再拒绝。
然后我瞬间看到了那个抗争到最后的巨人。
然后我记下姬喵在书中的这句话:「
请在每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都保持永恒的战栗和清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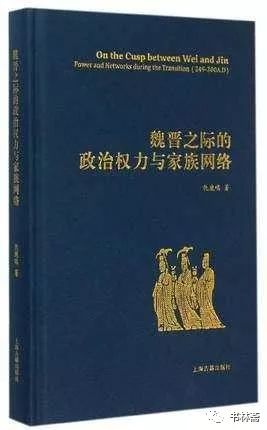
抬头看着满天星,那可能已经是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星星了,那时的它们与这片土地上的谁同在呢?是李膺?是曹操?是司马炎?是拓跋宏?在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舞台上,划过天空的绝大多数只不过是流星。
外面马路上的汽车声和窗外的雨声还在,对面楼里还有好几户没有熄灯。这是一个和平年代。这是一个很难想象那样厮杀血腥的一幕会烧红整片土地的年代。
在政治史已经越来越难做出新意的情况下,仇鹿鸣能像田余庆那样,对着几条大家都看在眼里的史料,不断分析、反复运用,最终得出一个又一个不同凡响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偏偏又很扎实,不像业余爱好者那样剑走偏锋,也不像老派政治史学家那样过于强调意义。
学术兴趣从明清开始慢慢转向魏晋时,会愈发觉得史料的重要性。明清史料甚多,只要能找到,就可以对一个大事件进行翻来覆去的比对,最后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做得好如顾诚,一部《明末农民战争史》和一部《南明史》就出来了;魏晋史料不多,就那几个,偶尔出土墓志铭和其它文物都能拿来大做文章,这种情况下对史料的运用就太重要了。
——仇鹿鸣大才。仇鹿鸣作为一名
80
后青年学者在有限的史料中挖掘出了司马氏从一开始的地域性家族转变到曹魏政治舞台上的闪亮明星,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陈寅恪说的寒族和豪族之间的转换,而是并没有真正地改变社会结构。
个人在历史大势中是不重要的,邓艾可以一直不被平反,贾充自然也可以被污名化,因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斗争是偶然的、薄弱的,但是他们背后所代表的那些就是必然的了。在魏晋的建立过程中,有太多的妥协,这些妥协使得政治遗产永远不会被清零给下一代,只能一代又一代地堆积,直到阻塞了一切的道路。
然后司马伦来到了历史舞台,告诉全天下,这片土地即将崩盘。
这是一个和平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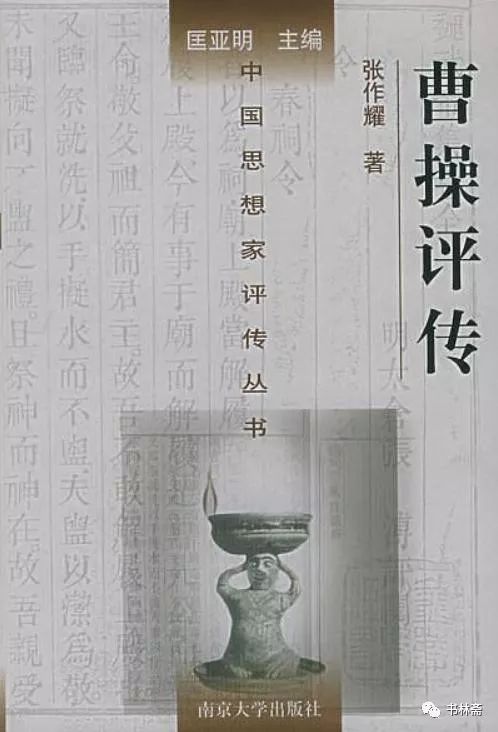
张作耀老师在写作这本书时,也许还没有对整个大历史有一个完整的大局观,因此在具体评析曹操时,只能将问题越写越小,和史料做无休止的纠缠,却又没有田余庆和仇鹿鸣翻来覆去榨干史料的本事,所以这本书与其说是《曹操评传》,不如说是曹操的史料集。
尽管如此,张作耀老师依旧在写作本书时对曹操投入了大量的情感,这样的情感是偏爱,也因此读者也被一分为二了。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从曹操的人生轨迹和一些手法中,其实我们就很可以学习一些东西。曹操为何能爬上去?曹操为何会成为军事家?曹操是怎么用人才的?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
但也仅限于此了,曹操终究无法改变历史轨迹,等曹丕登台后,一切便循着历史的方向,往前行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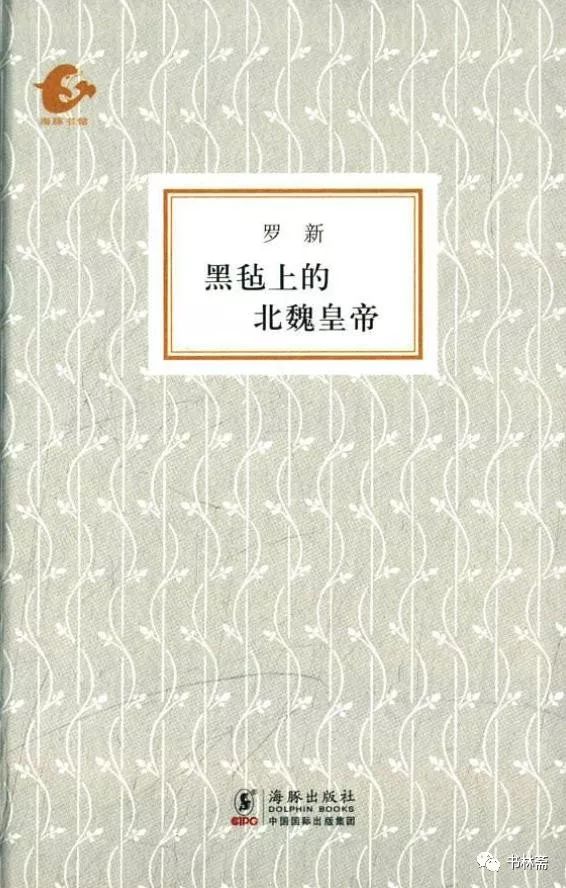
草原上的人们啊,抬头看看满天星,那是我给你们点亮的归家的灯。
永远歌颂这些不说汉语的人们,正如同歌颂这世间象征着血色的一切,血气和血腥是并存的,你永远也无法抹开他们存在过的痕迹。
在南北朝历史中,北朝史会被视为华夏史的一部分,华夏文化是否得到延续是研究北朝史的很多人所关注的重点,但是北朝史同样也是内亚游牧民族史的一部分,而且甚至可能更偏重于此。
当我们研究北朝史时,会发现很多习俗其实并不是承自华夏社会,而是来自内亚的游牧民族,所以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本质上便是如此,我们要脱离华夏本位地来看待这段历史,可以用阶级分析法,也可以试着用内亚游牧民族本位来看。
用这个视角看,那么会有不一样的结论。本书很短,但本书的结论就立足在北魏皇帝的即位仪式上,从黑毡到七人抬,从乌桓到鲜卑甚至到后来的蒙古,这个习俗一直存在着,如果以内亚游牧民族的视角来看,那么这就是一个连贯的历史,而从华夏本位看的话,这可能就是一个时断时续的历史,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对这一行为进行合理的建构。
这让我想起彼得
·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在他这本书里并不曾用观察的东方视角或者西方视角来看世界史,而是站在中亚地区来审视东方与西方,于是世界史以另一种形式自洽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迷雾被破除了,困难不存在了。
这种断断续续不可能被记录的内亚游牧民族的历史,早已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而如若我们无意中捕捉到其中的一丝一毫,那么也许便会看到整个大历史的另一种表述。所以,争论十六国是不是中国、辽是不是中国、西夏是不是中国、金是不是中国、元是不是中国、清是不是中国,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的。
那么,祝所有人都可以在未来平安到家。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
——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

读来收获不小,上个月刚读了赵世瑜老师的《小历史与大历史》,接下来还有一本《在空间中理解时间》,都是社会史的佳作。
虽然赵世瑜老师写了很多理论,但我对案例其实是更感兴趣的,比如刚铁是历史上的失语者群体宦官们的精神投射和建构,比如太阳神的生日三月十九是民间对崇祯上吊日期的一种暗中记忆,对这些民间记忆的追本溯源,能勾勒出一段又一段被正史忽略掉的东西。
福建庙会的神道出巡时,平民百姓可以扮成上层人士为,穿着仪仗一律可以逾越平时的等级森严的壁垒,某种意义上这是在借神灵的力量在反规范、反传统。
但具体表现时,我们会看到当扮演省城隍路遇上扮演瘟部尚书时,城隍的神位要停在路边,然后扮演者要对着停在路中央的尚书神位趋前三叩,表示接驾来迟,罪该万死。这时尚书的扮演者会挺胸凸肚,告慰一番,表示自己不介意。
这个行为很有意思。一方面庙会的作用是让老百姓从现实的束缚中短暂地脱离出来,让他们也可以幻想身份错位,可以做上流人士,甚至可以男扮女装或者女扮男装。但另一方面,这恰恰又是现实的投射,这个行为说明老百姓们永远无法脱离现实中等级森严的壁垒,他们只能完成自身的「逾越」(无论是通过科举还是通过庙会)。换言之,看似是逾越的事物,其实结果恰恰是在维护这一秩序。
几个月前,一个前辈在我面前抽烟,当我提出可否不要吸烟时,他熄灭了烟,而旁边的人则接话说,你怎么能这么跟XX说话呢?
我相信接话的朋友是无心的,不过这种无心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潜意识,一种默认接受了这套价值观的潜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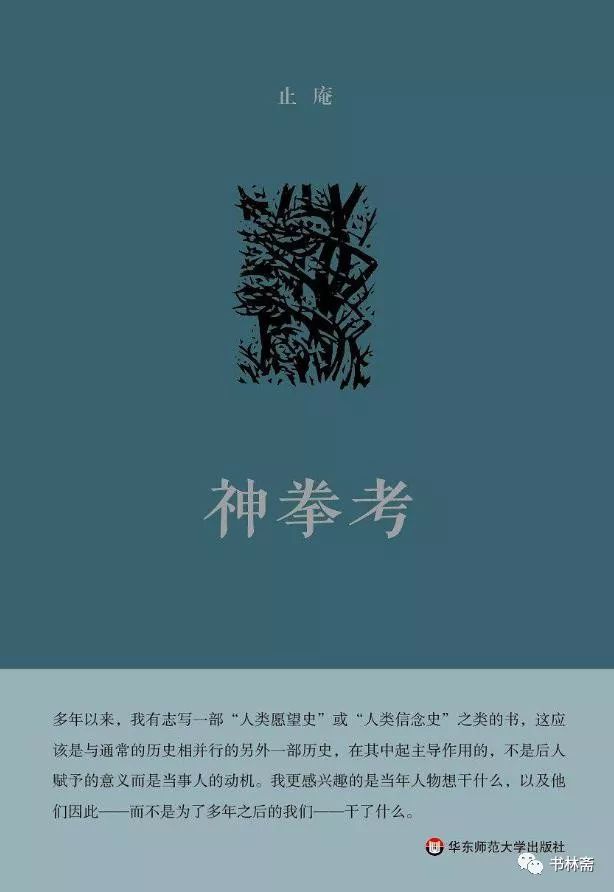
止庵这本书和《万历十五年》很像。
很多人鄙夷《明朝那些事儿》,其实这本书看起来很戏谑,但是质量比起《万历十五年》来更具有科普性质,是真正做到了明史推广的,毛佩琦就十分推崇。对《万历十五年》的争议不是历史观点的争论(《明朝那些事儿》里涉及到观点之争),而是假装是学术论文的伪学术论文。
第一,历史有3+N种。第一历史是客观发生过的历史,包括所有细节。第二历史是各种史料(包括记载、墓志铭、地方志、文集、文物等),并通过这些史料试图还原第一历史的过程,所以第二历史在理论上可以无限趋近于第一历史,但永远不能达到第一历史。第三历史是在第二历史上的建构过程,里面会加上作者对历史的建构,比如《史记》,严格说来《史记》不能算作史料,但因为先秦史史料太过缺乏,我们才会让《史记》成为先秦史史料。而不断的建构形成了3+N。
第二,《三国演义》和《史记》,都属于第三历史或者第3+N种历史。但它们成为历史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它们本身是历史而不是文本。这句话可能比较拗口,所以我们就拿《万历十五年》来看,这本书是黄仁宇对这段历史的建构,但建构还不能构成历史,只有当这种建构被普及并且影响到了其它思想时,它才会成为历史。即便如此,我们研究的也是这本书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这本书是如何影响其它想法的,研究的也并不像第二历史那样是关于第一历史的。换言之,第三历史是用来研究第二历史的,第二历史是用来研究第一历史的。
《万历十五年》的传播,本质上是一个还未成为第3+N种历史的文本在试图影响人们对第一历史的认知,这是一种扰乱,当然这种扰乱势必在很多年后也会和《万历十五年》一样成为第3+N种历史,但是每多一个扰乱,就会多数倍的复杂,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是不可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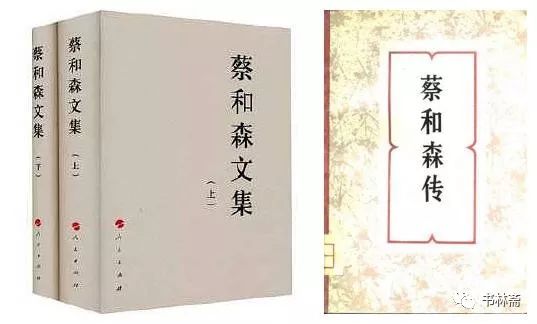
见
蔡和森的牺牲,也许改变了历史进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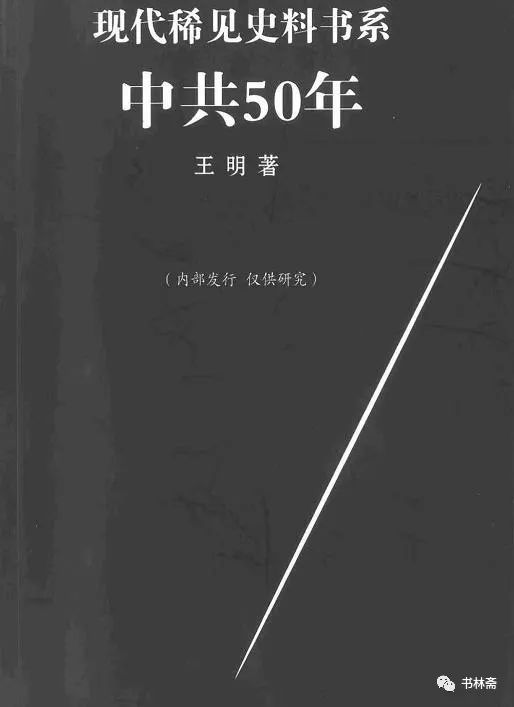
陈绍禹写完这本书后不久就去世了,这本书读来颇像一部同人小说,而只要熟读党史并且看过一些材料的读者,自然都知道这里头提及的大量内容都是陈绍禹的书生之见,甚至是恶毒的谣言了。
确实如此,在书中,陈绍禹表现得像极了一个单纯幼稚的书生,于是陈绍禹从1935年开始批评,一直批到1974年他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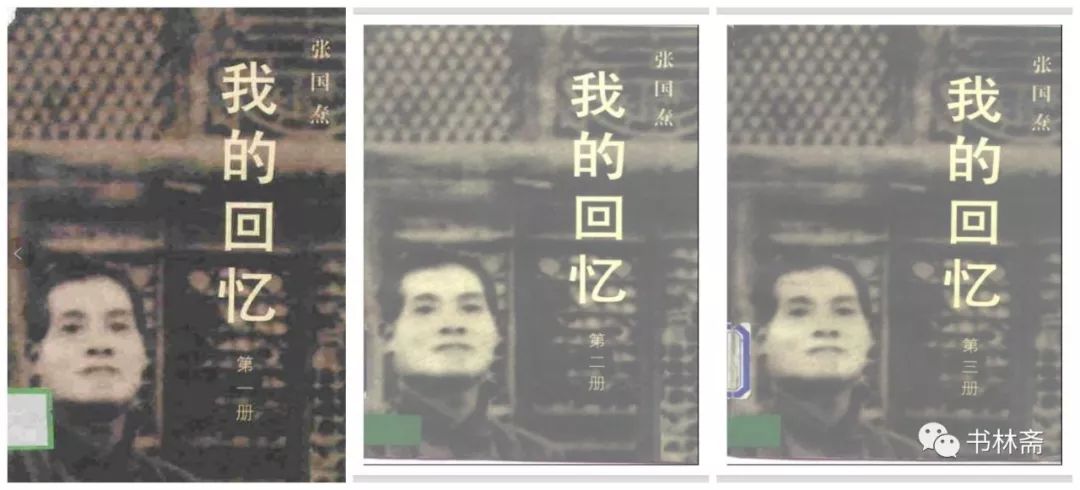
张
恺荫的回忆一开始是让人很舒服的,虽然这个人的心很狠,时常会流露出一种决不妥协的强硬气质与目中无人的自大模样,但是他的见解还是比较独到的,比起萧子升、陈绍禹这种书生的回忆录来,我更相信张
恺荫
是更真诚一些的,所以也比那两位更值得尊敬一些。
这样的人作为老毛事后回忆起的「
平生最险的对手
」,是配得上的。老毛这辈子的对手蒋介石是一个、张恺荫是一个、……。我想,是一个比一个棘手的。
说回张
恺荫
,这位唯一一个见过列宁本尊的昔日党员,对共产国际的态度和蔡和森一样反而很复杂,比起书生们来,确实是位失败的枭雄。
但是尽管如此,张
恺荫
的能力和眼界却始终看不长远,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他就屡屡看错、判断错,并且自以为对。所以自第三册开始,便很自然地沦为与陈绍禹的回忆录一般的水准了,泼妇骂街还至不上,阴阳怪气还是有的。到死都不曾悔过,也难怪最终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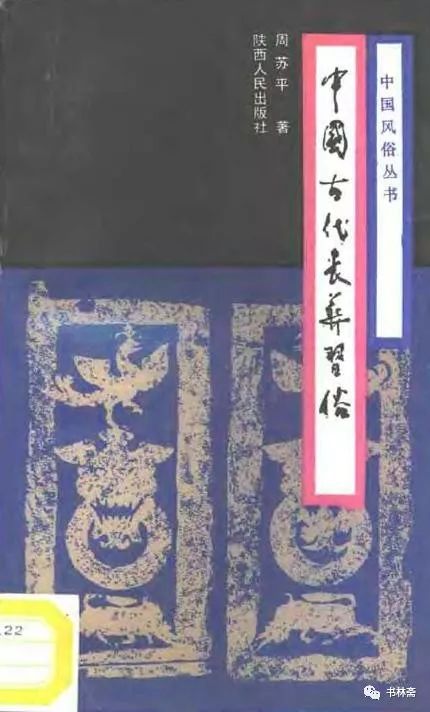
书不够深入,很多东西泛泛而谈,但如果考虑到这是一本八十年代的书,那就要另眼相看了,当墓葬研究刚刚兴起的时候,人们是怎么认识到从古至今、自上而下的墓葬、礼仪是什么样的,这本书可以作为一个范本。
也就是说,对于刚入门的读者来说,它是一本很好的科普。对于后世的史学研究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的墓葬研究史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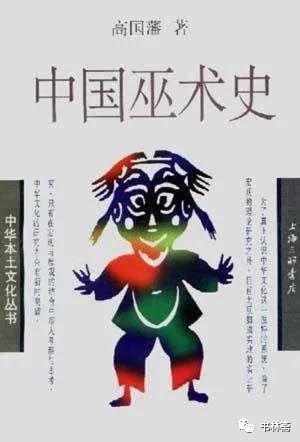
资料很多,可读性不强,约莫算辞典一样的东西,全书没有一个脉络。

《镖门》这部剧,其它的先不论,单是故事背景放在清代山西,就一下子和其它的镖局题材拉开距离了,从武林掌故来看,徐浩峰(《镖门》编剧)确实比很多武侠作者更胜一筹。
因为和大家的认知不同,镖局其实在清代才出现,而且迟至乾隆时期:「
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仍系乾隆时神力达摩王,山西人神拳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嗣由其子怀玉继以走镖,是镖局的嚆失。
」而镖局在山西发源,也是历史必然的产物。
所谓商不离镖,镖不离商,镖局的发展,和晋商的四通八达是离不开的。
晋商从明中期开始兴起,清朝时期达到鼎盛,他们靠着明代始的开中制(食盐专卖权)和矿业发达起来,与此同时山西地理位置很好,往东是北京,往北是蒙古,往西是西安,往南是河南,于是晋商可以行走于祖国各地,甚至走出国门。最早的会馆就出自晋商,清代山西富商,资产百万以上的大有人在,因此山西在清代被认为是「海内最富」。
正因为这么有钱,当晋商在路上行走时,就自然而然会遇到劫匪的觊觎,于是晋商们就必须雇佣一些会武术的人来替他们保驾护航,在这样的情况下,镖局才应运而生。
所以镖局的诞生来自经济的发达,而镖局的消亡则来自地方治安的稳定与货币流通的便捷,这是具有历史性的东西。不能说金庸老爷子《笑傲江湖》就因此写得不好,但是从历史性来看,显然老爷子没有考虑到镖局诞生的土壤,而当《镖门》里将故事背景安在清末山西时,你立刻就能清楚,徐浩峰是个懂行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李金龙的《清代镖局与山西武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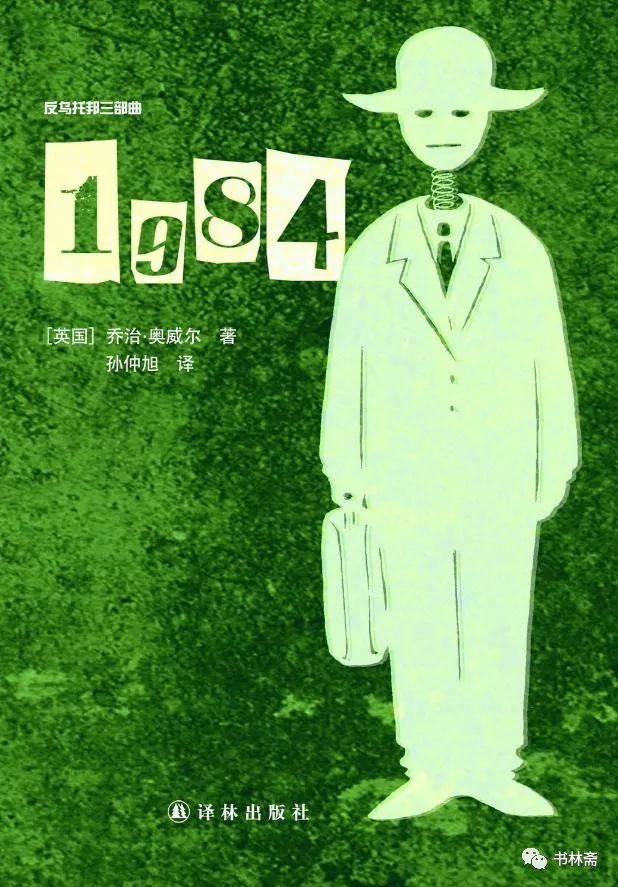
重读这本书是因为我查到作者的死,是因为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看到这个,我开始好奇,作者在这本书里究竟秉持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因为这本书写于作者去世之前不久。
带着这个问题我重读了这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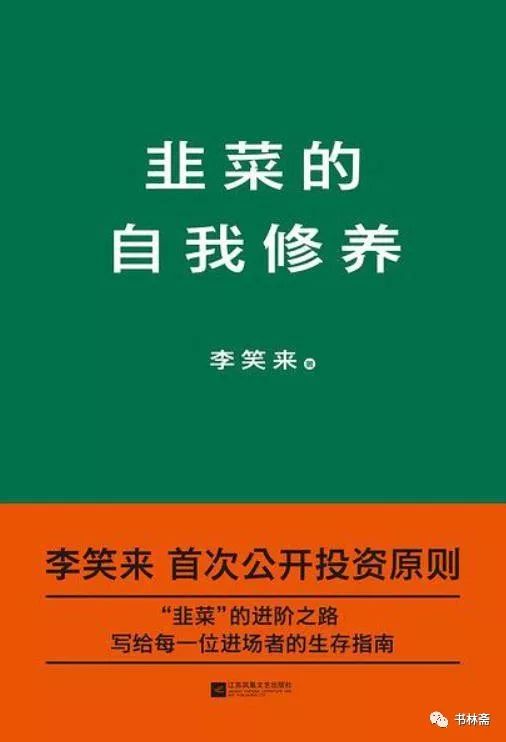
在书店翻到的,小册子,定价还39元,二十分钟迅速读完,虽然作者在前言里一直强调自己没有称别人是「
韭菜
」,但是通篇充斥着作者的高傲和对他人以傻X式的鄙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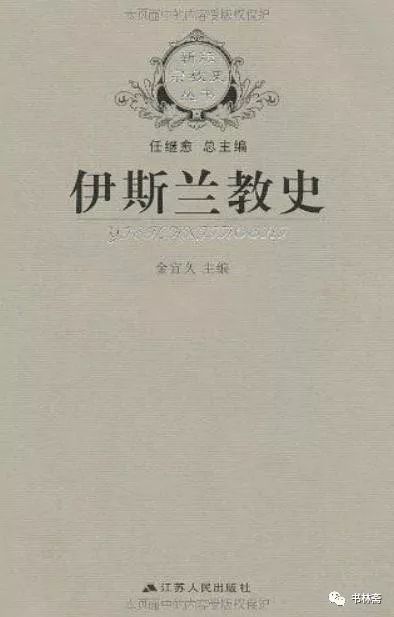
中国事,读三国;世界史,读伊教。这已基本上是我目前给自己定下的方向。不过这本书确实是有门槛的,门槛不在其它,仅在于层出不穷的人名与地名实在对我来说过于陌生,因为并不了解前后的历史,所以读来也并不曾真正记住过什么。
有比较了解的朋友,不妨指点一二。
不过倒是有了一个有趣的发现,阿拉伯地区国家的变更,似乎更多都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争斗,而从不曾像中国这样,不断地发生着农民们的大规模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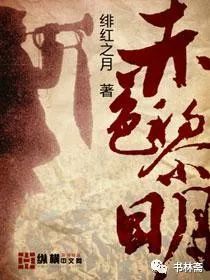
如果你对近代史感兴趣,却看不下去大学教材《近代史史纲》,那不如读一读这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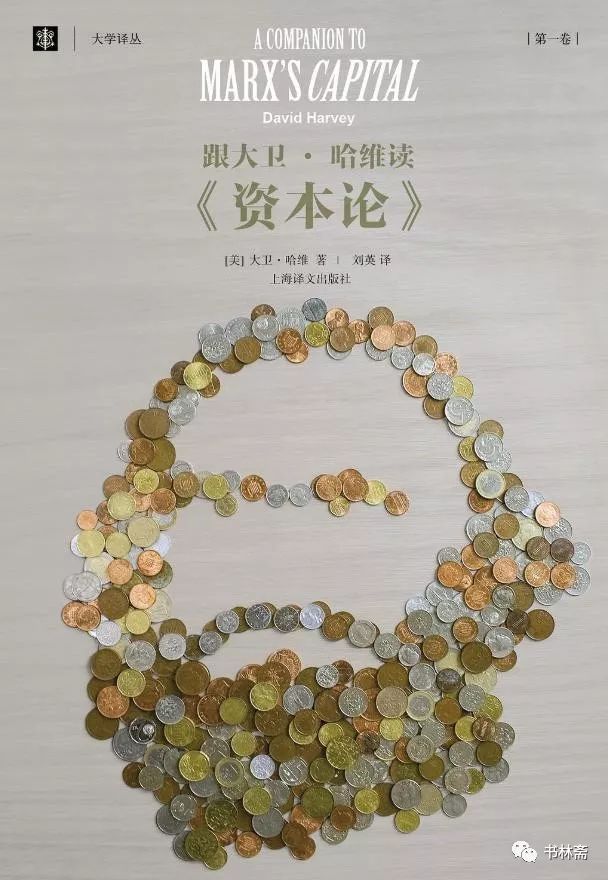
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解读,读来收获还是很大的。虽然作者仍旧提出了一些对马克思观点的质疑,但从字里行间中,很明显能看到作者由衷的佩服。
当马克思先从商品开始讨论时,这些概念是容易被接受的,再由商品引出货币,从而将商品1—货币—商品2的流通过程,变成货币1—商品—货币2的流通过程,但如果货币1和货币2等价,那么就没有必要出现这个流通过程了,于是货币2一定要大于货币1。
到这里为止,虽然马克思的思路别人都没有提及(有的涉及到但是没有这么清晰),但接下来马克思的论述就只能是令人叹为观止了。
马克思靠着这个差量,提出了剩余价值,并且从剩余价值理论里,提到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从而引出工人,并清楚地指出来,剩余价值来自哪里。而后通过对个体工人的讨论,上升到对工人群体的讨论,从而正式将工人阶级提了出来。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
资本家阶级不断地以货币形式发给工人阶级凭据,让他们用来领取由工人阶级生产而为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产品中的一部分。工人也不断地把这些凭据还给资本家阶级,以便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取得他自己的产品中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货币形式掩饰了这种交易。
」
这些想法,在阅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后,也隐隐然有过,不过毕竟郭大力的翻译有些拗口,虽然读完后思路如此,但不能完全理清并概括,不过在读了这本解读后,更清晰了这些念头。
他们的恰同学少年,和他们的法兰西岁月。
阅读原文处可查看文章集锦。
来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微博「孔鲤」及豆瓣「孔鲤」。
我写,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