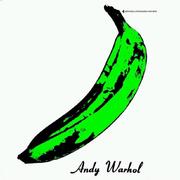正文
关于「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整个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我向来认为是「错误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种问法不符合逻辑,因为所谓「意义」总是就「部分之于整体」而言的,比如我们某种看法或某种做法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们对某个问题或某个事情有帮助,否则我们就会说「你这是废话」、「你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将「意义」这个词用于人生或整个人类这种整体性概念,是错误的用法——除非你假定有来世和轮回,那么人生就不再是一个整体性概念。
近日我读到爱因斯坦给一个学生的回信,他的看法与我不谋而合。
故事是这样的:1950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收到一封19岁的拉特格斯大学学生的长信。这名学生对人生感到困惑,觉得人活着好像「没有任何目的」,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上大学。他问爱因斯坦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并排除了金钱、功名以及助人为乐之类的答案。
收到信几天后爱因斯坦就给他写了回信。回信的内容是:
你为探索个人和整个人类的生活目的进行了如此热忱的努力,这令我深受感动。在我看来,以这种方式提问,是得不出合理答案的。当我们说某个行动有何目的的时候,意思无非是:通过这一行动及其结果,我们想满足何种欲望,抑或想避免何种不希望出现的后果?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个人所属的集体出发,明确说出一项行为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行动的目的也同构成社会的个体欲望不无关系——起码是间接地有关。
如果你要问,作为整体的社会或作为整体的个人有何目的,那么问题的意义就消失了。当然,如果你问作为整体的自然界有何目的或意义,情况就更是如此。因为在这种情形中,人若是硬要说自己的欲望与整体事态发展有关,那是十分武断的,即便不是毫无理由。
尽管如此,我们仍该自问:要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这个问题合理而且重要。我个人认为,答案是这样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满足大家的欲求和需要,并建立和谐美好的人际关系。这就需要大量的自觉思考和自我教育。不容否认,就这一重要领域而言,较之当今的学校、大学,开明的古希腊人和古代东方贤哲们达到的程度要高得多。
显然,爱因斯坦也认为「人生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不恰当的问题。不过最后爱因斯坦仍诚恳地给出了我们如何度过人生的建议:
尽量去帮助别人、建立良好人际关系。
这是很中肯的建议,因为帮助别人、服务社会可以让你人生这个整体的一个一个「部分」持续地获得意义,而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助你确认这种「意义」不是你一厢情愿想出来的、而是被大家所认可的。
对于一般人来讲,这也许是最可行的办法。罗素在《幸福之路》中给出的答案也是类似的,他认为快乐的秘诀在于少一点关注自己,应该让自己的兴趣尽可能广泛,对人和物尽可能友善。
然而,
尽管「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不恰当的问题,但既然每个人都会去问这个问题,那总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于每个人都有「自我意识」,而当我们知道随着肉身寂灭,这个「自我意识」也会消失,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悖论:自我意识知道自己要消失。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悖论呢?因为「时间」的概念原本就是「自我」的产物:用来解释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现在这个时间概念被用到自己身上了。按照逻辑,如果时间概念是由「我」所产生的,那么「我」应该是「无所谓生灭、无所谓短暂还是永恒的」。
可以说,每个人自从知道人会死之后,这个悖论就一直伴随着他,直到真的死去。所谓悖论,就是逻辑无法解释的东西,因此它不仅仅带来困惑,而是带来「荒诞」。一个人越是境遇糟糕,或者感情受挫,当他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减弱之后,可能就会被这种「荒诞感」所吞没,轻则抑郁,重则轻生。
很显然,上述问题是超越逻辑和语言的,除非你能够通过「亲证」破除时间的幻象,否则无法摆脱悖论。这正是东方学问所擅长的,佛家、道家/教是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儒家则说「未知生焉知死」、「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意思是死生如昼夜、知昼则知夜,本无生、本无死。当然,儒也好、释也好、道也好,都要靠做工夫「亲证」,而不是从知解、言说上进入。儒家走的是德行的路子,道家/教走的是性命双修的路子,佛家走的是定慧等持的路子,殊途可以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