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至今,伴随着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日臻成熟和完善,政治传播成为传播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尤其是“规范化”(normative)取向的政治传播成为这一领域的主导范式。但其学科定位一直不甚清晰,常常与修辞学、口语传播、媒介效果研究和舆论学等领域“合体”。直到1973年,国际传播学会(ICA)成立了政治传播分会,并在次年出版了第一本专刊《政治传播评论》,后来发展成为本领域的重要学术期刊《政治传播》,由美国政治学会(APSA)和国际传播学会联合主办。围绕这一领域的理论、方法和主题的建构日趋多样化,迅速成长为传播学领域中的一门“显学”。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解构“欧美中心主义”(Euro-America-centrism)的潮流,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也在“去西方化”的语境下探索理论重建的可能性。但时至今日,政治传播仍然是“西方中心论”占据垄断地位的最后一块“飞地”。
2016年西方政治体制与社会价值体系出现了结构性的“内爆”,政治传播的理论和实践面临着颠覆性的挑战。当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的结果出炉后,深居“常春藤”“象牙塔”内从事政治传播研究的教授和学子们抱头痛哭,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无法正常开展教学研究,成为“精英陷落”的一个有力注脚。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和民粹主义的兴起挑战了既有的西方政治秩序,泛滥于社交平台上的“后真相”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游戏规则”的改写也消解了经典理论和高头讲章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也标志着“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秩序日渐解体,世界进入了“后西方、后秩序”的时代。与之相应,“欧美中心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传播在全球范围内“理论旅行”的过程中遭遇多元本土文化的冲击,以往被各国精英和学者奉为圭臬的“普世价值”所具有的“全能解释力”受到了广泛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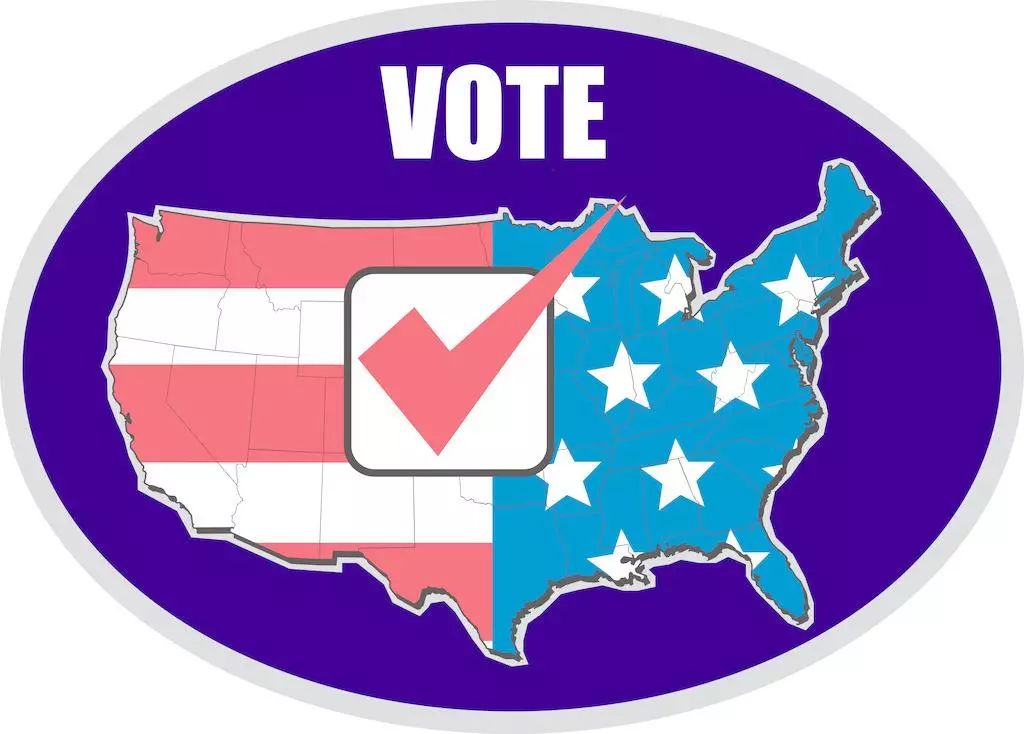
从历史源流看,政治传播研究在其理论框架形成的初始期,就已经处于“西方中心论”的强大影响之下。自从熊彼得提出“选举中心论”的民主观念以来,政治学界普遍认为,只有自由选举才能被纳入民主国家的考量。从这个角度看,西方政治传播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选举制度发展史的梳理与分析。“议程设置”、
“意见领袖与两级传播”、“选择性接触”等大批经典传播理论都是最早针对美国的选举活动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并在其他多党制民主国家进行了重复性检验。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政治传播研究是具有“准入资格”的。只有效仿西方实行多党制和自由选举且拥有“独立”媒体的国家,才有可能进入政治传播的研究领域并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对话。那些选择不同政治制度和运作方式的国家很自然地被打入“另册”,游走于政治传播研究的边缘地带。追溯现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起源,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视角。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相呼应,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传播研究也逐渐形成了一套“中心-半边缘-边缘”的权力架构。
由于研究对象与政治密切相关,政治传播长久以来都是传播学界“西方中心论”或曰“欧美中心主义”的积淀最为深厚的一个领域。西方学者在传播研究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随处安放的学理自尊”,宣称其研究具有普遍性,并总是试图将其他地区的研究边缘化为一种“特殊”或者“例外”。与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相似,在当前的传播研究中,以地域为界限的学术分工体系泾渭分明:华裔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印度裔学者研究印度问题,欧美国家的“白人学者”研究全球或“普世”问题。这一点在政治传播研究领域表现的尤为显著。西方学者基于本国的政治实践进行实证研究并建构理论,处于“半边缘”的其他“后发民主国家”的学者将这些理论进行重复性的验证,而像中国这样的“例外”国家则被排斥在政治传播的“文化想象”和话语体系之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传播学界也加入了学术界以“去西方化”为主线的理论反思和路径重构当中。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在对欧美中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倾向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同时,其学术路径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为了反对西方霸权,建构了某种封闭的“非西方”模式,并且以“非西方”的研究路径占据道德和话语的制高点,形成“西方”与“非西方”研究路径之间尖锐的二元对立。这种“去西方化”的思路一方面将“西方”高度同质化,抹杀了在西方国家内部存在的政治传播实践与研究路径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将“非西方”语境下的传播学研究“他者化”,否认了全球政治、社会与媒体生态仍然处于“西方路灯光影”之中的现实状况。如果全然拒斥西方传播研究的话语体系与学术成果,试图在一种“真空”的本土语境下建构“另类空间”或“替代性话语体系”,同样会陷入到形而上的陷阱中。这一点对于政治传播领域的研究者而言尤为重要。
无论是唯“西方”马首是瞻还是彻底地“去西方化”,这样的研究路径都不能
完整地诠释处在变化之中的全球政治和传播格局。因此,探索新的媒介环境下的政治传播研究,需要建立一种超越二元对立论的思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狄普希·查克拉巴蒂(Diepesh Chakrabarty)提出的“行省化欧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成为解构“欧美中心主义”的重要理论框架之一,对创新政治传播研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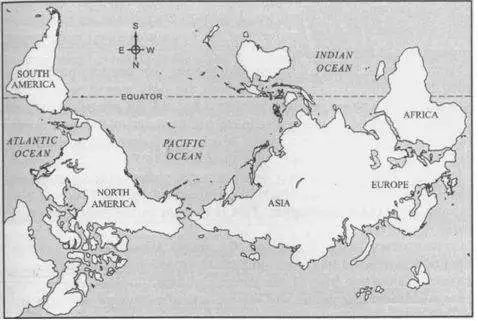
查克拉巴蒂认为,当前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不仅仅是一个现实地理区划,更是一种历史观念,代表着学界对于“政治现代性”(political modernity)的理解。基于欧美学者的历史观,人类历史只有一种标准化的线性演进模式,不同地区之间政治文明的发展差异只能被解释为处在这种演进模式的不同阶段。但查克拉巴蒂认为,欧洲中心的历史观对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国家的文明演变进程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为此他提出,对于欧洲历史的研究也需要纳入“行省化”的视角,即“挖掘历史及其符码的某种局限,从而使其无效的部分公诸于世”(Chakrabarty,2009:96)。
查克拉巴蒂在这里所说的“历史”,即西方历史学家主导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在他看来,从来没有一种历史叙事能够穷尽所有文明和区域的发展进路。即便是在欧洲内部,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现代性的形成路径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因此,经典史学所构建出的“欧洲中心”的传统叙事甚至无法完整地解释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欧罗巴”所经历的政治现代性历程,遑论去涵盖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因此,引入“行省化”的研究视角,不仅是要将欧洲视作人类社会的一个“行省”,而且还要进一步将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欧罗巴”分解成为不同的“行省”,以探寻在多元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下的政治现代化进路。
相较于“去西方化”或者“本土化”的概念,“行省化”提供了在更具包容性的维度审视政治传播研究的视域。去西方化或本土化有意无意地将西方树立为“他者”,从而使研究的出发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行省化”则以更为多元化的视角审视不同地区的政治和媒体语境下的传播研究,关注根植于不同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的本土经验和在地实践,将源自西方的理论视作具体历史语境下的“话语型构”(discursive formation)而非空洞抽象的概念(Zhao Yuezhi,2012:143-177)。在行省化的框架下,研究者——无论是来自西方不同国家还是来自非西方——所提供的理论都是根植于本土视野的产物,理论之间的对话则应当是双向且平等的。
政治传播研究与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行省化”的思路对于彻底颠覆政治传播研究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视角有着重要的意义。如
前所述,越来越多居于主流的学者也逐渐认识到,由于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即便是关于西方国家自身的政治传播研究实质上也是高度“行省化”的。在不同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开展的研究所发掘出来的“在地经验”也从未被证明具有“普世性”。换言之,从“行省化”的思路来看,“欧美中心主义”的政治传播学也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神话”。如果深入到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内部和深层,研究者便会发现在貌似同质化的“西方民主”体制背后也存在多种形态的政治传播体系。
作为“行省化”政治传播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爱德文·贝克(EdwinBaker)和斯科特·奥尔索斯(Scott Althaus)等学者基于“政治责任”(politicalaccountability)的视角,将西方民主体制分为“共和主义”“多元主义”和“精英主义”这三种模式,并提炼出了不同模式下政府-公民-媒体的互动关系形式(Althaus,2012:97-112)。在不同的政治责任语境下,政府-公民-媒体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互动形式。这三种语境下开展的政治传播在方式、目的和效果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例如,在“共和主义”的模式当中,媒体在政治传播中扮演的是“策展人”(curator)的角色,强调媒体运用专业素养整合多元化的信息和观点并提供权威解读;在“多元主义”的模式当中,媒体在政治传播中扮演着“代言人”的角色,秉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媒体构成了“彩虹光谱”,代表不同的社群发声;而在“精英主义”的模式当中,媒体则扮演着“秩序维护者”和“舆论调停人”的角色。

在政治传播过程中不需要通过商业媒体常用的“反常放大”的方式来制造冲突,吸引眼球,而更多的是通过“协商框架”促进社会整合与统一。正如一位参与十九大报道的境外记者所概括的那样,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是“接力赛”,而不是西方式的“搏击赛”(大公报,2017)。这种本质上的差别就使得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需要更多地从自身的历史资源和政治现实中挖掘有意义的内容,以建构“行省化”视域下中国语境的政治传播。在政治传播过程中不需要通过商业媒体常用的“反常放大”的方式来制造冲突,吸引眼球,而更多的是通过“协商框架”促进社会整合与统一。
由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文化积淀和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形成了一套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体制和传播模式。实践证明,采用“西方中心论”的视角无法发掘和阐释中国政治传播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加之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奉行的“不争论”“不对抗”的权宜之计,导致包括传播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陷入了“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话语困境,研究者对于政治传播的相关课题“不敢谈、不愿谈、不会谈”。虽然传播学引入中国已近半个世纪,政治传播对于中国学界而言还是一
块待开垦的处女地。“十九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绘制了明晰的路线图,也为世界
进入“新全球化”时代提供了有力的参照,这也是我国政治传播学科建设和研究体系建设的良好契机。在“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的当下,政治传播的“范式革命”已经成为全球学界的共识。以目前国内外学术资源和话语体系来考量,“行省化”可以成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者加入国际学术主流最为便捷的切入点。我们要按照“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的要求,深入挖掘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本土资源和在地话语,按照“传播”本位的思路重新厘清政治传播在中国演进的历史脉络和现实考量,并结合在“新全球化”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中国政治传播的肌理汇入全球政治秩序重构的体系当中。
具体而言,“行省化”视域下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可以从传统的政治传播思想、革命时期的政治传播经验以及“新时代”的政治传播实践三个维度展开。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在“行省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传统的“天下”观促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模式的形成,提供了那些西方“原典”无法涵盖的在地经验。谏议制度对君主决策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监督模式和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对于遏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和决策失误具有重要意义(陈谦,2006:87-96)。“符命神话”则代表了官方与民间进行互动的一种形态,官方基于民众的普遍信仰建构一系列关于帝王的符命神话,以建立其王朝的合法性地位(白文刚,2014:12-15)。在历史上逐步形成的“华夷之辨”则则成为了历史上最早的公共外交叙事之一(葛兆光,2014)。
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革命话语体系”至今仍在型塑中国政治传播的实践,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模式。动员是中国公共议程设置的重要模式之一,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促进新的政治议程的高效实施,例如,计划生育政策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公共政策都是基于“动员”的政治传播模式而展开的(王绍光,2006:86-99)。又如,“内参”作为一种起源于战争年代的政治传播模式,对全面了解下情、充分搜集信息,有效管理国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尹韵公,2012:4-14)。这种模式完全超越了西方政治传播的研究范畴,理应成为“行省化”研究重点发掘的对象。

在新时代的政治传播实践维度上,研究者一方面需要对互联网和自媒体环境下政治传播所面对的新挑战和新动向加以分析,并形成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例如中纪委、外交部通过微信、微博等主流社交媒体、共青团中央通过知乎、B站等亚文化平
台主动发声设置议程,在青年群体中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政府机构主动适应数字化时代政治传播需要的实践创新值得学者更多关注和分析。另一方面则需要对“后西方、后秩序”背景下中国对外政治传播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随着中国引领“新全球化”时代的角色和路线图日渐清晰,中国领导人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社会引发日益强烈的共鸣,如何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2.0版,提升我国政治文明对外传播的有效性,亦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亟待开拓的领域。
基于上述三个维度,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者应当把握当下的历史契机,找准自身在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版图中的坐标,在新一轮的“范式革命”中完成“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转型。在经典政治传播理论陷入“解释力的危机”,而传播学研究“西方中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倾向遭遇进一步质疑和解构的当下,强调超越“全球-本土”“西方化-去西方化”对立、寻找多元化在地经验的“行省化”视角,无疑对于我们以理论反思和路径重构的方式描绘政治传播研究的未来提供了有力的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