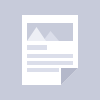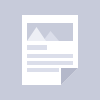年轻时代贾植芳先生
文|李辉
走进复旦大学第一年的年底,我与陈思和有幸遇到贾先生,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开始研究巴金,开始走进他和师母的家,我们都成了他们家里的亲人。
三年的校园生活里,我常常走进他们家里,听先生师母聊天,陪先生一起喝酒,吃花生米,再来一碗面条。现在想想,那是多么愉快的日子!
离开复旦,贾先生连写几封信,告知哥哥贾芝、梅志、牛汉、黎丁等先生,说我一人在京,请他们多多关照,要他们叫我经常去他们家里吃饭……
再次找出先生师母多年来写给我和应红的一百多封信,细细重读。读信思人,感恩在心。
贾先生写来的第一封长信,是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六日的暑假期间。信中他到武汉的一些朋友,包括曾卓、毕奂午等。信中有好多细节,包括陈思和暑假的生活,他都写到。

1980年8月6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1)

1980年8月6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2)

1980年8月6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3)

1980年8月6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4)
李辉同志:
你从家里的来信早收到了,问候你和你的家人们都好。因为事杂,迟到现在才复你。暑假已过去大半,想来你不久也该动身回校了。
读来信,知道你在武汉会到了一些有关人士。田一文同志我无缘得识,只从文字上相交,听说他前年曾入川看过在那里蛰居的胡风,也写了些东西,你路经武汉在碰到他时,请替我问好。我们编的巴金资料已经在南京会印,出书后,当送请他请教。我们也希望能早日看到他写的巴金传。这是件开创性的有意义的工作。
你去看毕奂午先生很好,我在青年时期就读过他写的小说和散文。解放前夕,有个朋友(当时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刘北汜同志)为一个出版社编了一套叫《文化工作丛刊》这样的丛书,那里边收有毕先生的一本散文集,好像题名为《掘金记》(?),同时也收了我一本散文集,题名为《热力》,只是用杨力的名字出版,想必他还记得。这些年听说他在武大教书,但绝少看到他的新作,想来这些年也经受了一番风雨。
曾卓兄近有信来沪,说他已去庐山参加一个什么讲习班了,要收集过去的散文成书,需要查找1947年的《大公报》,你见到他时顺便说一声,等到开学后才能查找,现在假期内,管报刊库的人员正在休假,不好麻烦他们。
文振庭兄前些日子有信来,他已去庐山休假,所以我一直未复信,他寄来的他们编的大众语文论战材料两大册,我都收到了。有些补充篇目,正由任敏抄写中,一俟抄好,我们再写信给他。
他托上海作家协会魏绍昌同志代为复制的几本书,我问过魏绍昌同志,他说,他正托上海旧书店设法补齐文老师需要复制的那几本书,说旧书比复制品便宜,也比较字迹清晰,俟补齐后(现在已有几册到手)再给武汉寄出,作家协会刚买好复制机,还没找到会弄这种机器的人员。
上礼拜内,我和唐老师接见了一个叫金介甫(J.C.Kinkley)的美国圣若望大学助理教授,此人现年32岁,写过一本研究沈从文的著作,弄了个博士。他和我谈到美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他是哈佛大学出身,是费正清的学生。费是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授,也算一个在国外的这一行的权威。
这位金先生也谈到那个写《巴金和他的著作》的Olga Lang,因为他们是同校又是同行。他说,巴金在美国的评价不如在法国高,他的作品“写得太快”,“茅盾写一个字他需要写三个字”,虽然如此,巴金仍不失为现代中国作家中有国际影响的作家之一。(他说,中国有国际影响的作家,当然鲁迅是首屈一指的。)我听他说话,已意识到你们选择了研究巴金的题目,是很有意义的一种事业,是大有可为的领域,值得花些力气,弄出个可观的成果来。这位金先生还说,巴金作品在港台一带仍然很风行。
小陈同志也有来信,他假期在上海电影局看稿,也快要结束,哪里腾出手来搞自己的东西。你们这种努力,使我听了,很受鼓舞,燃烧起我对祖国文化事业前途的热切的信心。
上海这几天在落雨,气温低了些,前些日子却热得怕人,工作生活都受到影响。武汉向有火炉之称,乡间可能好些,但愿如此。望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余容面叙。匆此,顺候
近好!并候你阖家清吉。任敏附候。
一九八〇年八月六日
贾先生信中写到的金介甫,我在北京经吴晓铃先生介绍,从此成为好朋友。金介甫每次来北京,有机会我们总会见面。
初到北京,经常给先生师母写信,告诉北京朋友的一些情况。收到信后,贾先生总是会很快回信。在一九八二年三月三日的信中,先生写道:

1982年3月3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1)

1982年3月3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2)

1982年3月3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3)

1982年3月3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4)

1982年3月3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5)
你抵京后来信,早已收阅,因为那阵子忙乱,顾不上写回信,就由桂英给他回了一信。近来接到黎丁、梅志以及我的哥哥来信,都提到和你相会情况,我已分别复信给他们,希望他们对你多加照拂。你初次进京生活,一切可能陌生,或至生活饮食不习惯,但慢慢会习惯的。
北京是我年轻时代的旧游之地,我很怀念那个朴实的北方大城。现在虽然有许多变化,但它的基本性格却仍与上海有别;再加上那里如今人文荟萃之地,又是全国的神经中枢,你会慢慢习惯和爱上这个城市的。你已去过的那几个与我有关的地方,也总可以给你一些帮助和温暖。
我前嘱晓林代胡先生家里买录音机和冰箱,久未得她回信,不知办理如何。今日接梅志先生信,说是他急需用录音机。以利胡先生工作。她要我介绍晓风(胡先生女儿)去与晓林接头。你在上海和晓林夫妇都较相熟,而这两位女同志却是素昧平生,我们请你便中为此事去找找晓林,催她尽可能先把录音机的事情办妥,一切跑腿接头的事,就让你包办一下。你见到梅志先生时,也把我这个意思传达给她。办理情况如何,来信告我。
前几天接到吴奚如先生信,托你带给他的信笺等他已收到,他身体不行,住疗养所,信上特要我向你致意。毕奂午先生不知你在武汉碰到否,我久未得他来信。
我们全家都惦记你,时常谈到你,仿佛生活中短缺了什么一样,颇有寂寞之感。望你注意身体,注意休息,切不可过于劳累把身体搞垮!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日)
两个月后,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贾先生又来一信,告知我去帮忙买录音机,可以帮助胡风先生录音:

1982年5月9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1)

1982年5月9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2)

1982年5月9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3)

1982年5月9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4)

1982年5月9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5)
今日得梅志先生来信,说阎绪德(晓林的女婿)前几天给她打过电话,说现在有300元一台的录音机可买,晓风姊妹不认识阎绪德和晓林,你可代他们跑跑腿,把具体的交钱取贷手续办妥,以利胡先生的工作。
我们全家的生活节奏如常,我的杂事、闲事仍然极多,真是整日手忙脚乱。你单身在京,仍应多注意身体,必要的营养和休息,要十分安排得当。北方生活与上海不同,过一个时期,慢慢会习惯下来的。
思和托去京友小燕带去的两瓶益母膏,不知送给她否?别忘。她小产在家休息,据说这种药物,对她会有些帮助。
(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

贾先生和朋友们与胡风梅志夫妇合影

2002年,贾植芳与梅志的最后一次合影,李辉 摄
一九八五年胡风先生去世,延期多日,终于在八月份火化,外地的不少先生都来了。送胡先生遗体去八宝山时,我前往医院与胡风先生家人一起前往。我带上一架相机,拍下梅志、路翎……一个个朋友与胡风先生告别的照片。
梅志先生一直很坚强,从始至终没有落泪。可是,当目送胡风先生远去走出告别厅的时候,她还是忍不住落泪了。
回到上海,贾先生于十一月十三日写来一信,最后一句,特意提醒我要“常去木樨地看看梅志他们”:

1985年11月13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1)

1985年11月13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2)

1985年11月13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3)

1985年11月13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4)
前后两信和你与应红打来的电报都收到了,谢谢你们贤夫妇的盛意,时光真快,想不到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已走了70年,并且有幸看到中国的天空出现睛朗的天气。生日那阵,上海地区的50年代的老同学20多人集资为我祝寿,大家热闹了一天,他们也都是50开外,子女成室立家的人了。正生日那天,思和夫妇和一些常来往的同事也在家里热闹了一阵,这些欢乐的气氛,使我们更加认识了友谊力量在人生途程中的作用,它是一种人间源流不绝的热量。
从后一封信中,得悉你们那本论巴金的书,指日可望出版,十分高兴。天津那本书,出版始终无消息,我最近到苏州开会回来,思和说,他在四马路买了一册,我们才知道它已出版。已请思和给责任编者于明夫去信,要他们先把样书寄来,以先睹为快。
8月份胡先生火化,我在北京八宝山那些照片,如已洗好,请随信寄来。
我些日子我仍然极忙,但所幸我们身体都正常,我们亟希望你们夫妇能在春节回家时路经上海,藉以小憩欢聚。
又,你得空常去木樨地看看梅志他们。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几个月过去,贾先生走在复旦马路上,突然被一辆车撞倒,骨折住院。我父亲恰好到上海出差,我写信告诉父亲,请他和在上海的舅舅一起去探望。
之后,先生师母写来一信。他特意提到,思和对贾先生的关爱。住院期间,总是陈思和背着先生去治疗,读信中的细节,真是难忘:
春节我遭车祸后,卧床期间,你父亲在你舅舅的陪同下,带了许多吃的来看望我们,他们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没有机会在一块喝上一盅酒,我们十分遗憾。现在承他又问起我的病况,真是感激!写信时,请代我们向你令尊和令堂致谢和致意。经过四个多月的卧床休养,目前我已能扶杖走路了。
在我卧病期间,你们的关怀和热情令我们全家十分感动和感激。思和近在身边,在我在医院检查时,我脚不能站地,是他把我背进背出。我上月前上外开会到城煌庙吃饭,他又和上外和华师大的同志把我抬进抬出,这些情景,使我永生难忘!
你在晚报上写的胡先生访问记,很好。多利用现在的条件,写些访问记,将来可收成一本书。
我的工作仍然头绪很多,从去年起加上图书馆和教研室的负担,越发事情多了。现在正值学年结束,更是忙上加忙了。好在通过四个多月的疗养,我的身体倒恢复的很好,比以前更健壮一些了。这也算上不幸中的收获吧。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也就在这一年,我开始采访全国各地的受牵连的“胡风分子”,或通信,或面谈记录,最终完成《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
全书于一九八八年秋天先在《百花洲》发表,随后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书名请黄永玉先生题签,书名改为《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贾先生读此书后,写来一封长信,谈他的感受:

1989年3月14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1)

1989年3月14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2)

1989年3月14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3)

1989年3月14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4)

1989年3月14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5)

1989年3月14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6)
《文坛悲歌》在上海知识界有强烈反响,我碰到一些老中青文学人士,都争相阅读。《新民晚报》有两篇文章,评价很高(随信附上),听说,《报刊文摘》也作了介绍。
我觉得这件历史公案,作为当事人,很难避免感情因素,往往看问题失之偏颇,也不排除由于现实环境,某些人还有所顾忌,这都是事之常情,不足为异。你已是隔代之人,执笔写来,必然是客观而全面地观察、分析那些历史现象以及人们的生活境遇与精神世界,这样就比较更接近更真实地反映历史真相。我认为你基本做到这一点。
又由于这宗历史事件,于今相去不算太远,那些主持和参与其事者(即主凶和帮凶),也不免要触动神经,甚至反扑,这都是意料中事,不足为异。总之,你写的是真实的历史,正如某些评论家说,用的是史笔,对得起历史的真实,也就俯仰无愧,由他们七嘴八舌好了。历史终将证实它的公正。至于其中某些细节上,由于事前未经核对,所有失误之处,有再版机会和你补编时更正一下就行了。这关系不大。(或许你写个《书后再记》,提一笔就行了。)
此次北京之会(即你说的由《文学评论》、《百花洲》及人民日报出版社召开的会议),我相信你能冷静对待,无论什么意见,都请以客观冷静的分析态度处之就行了。
4月武汉之会,我们和思和尽可能都去,那时再长谈。
我此次外出在杭州遇见冀汸,他也对你的劳动十分肯定,只是认为像孙钿、胡征这类朋友,以及路翎的夫人余明英应该补写一下。这个意见可供你写《补编》时参考。
等你的书收到后,我将分寄外国友人,并建议他们下笔译出,因为这已是一个惹起国际性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他们并不是单纯从文学争论观点,而是注意于从政治社会角度,藉此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现实。因为这事件本身很有典型意义。
先写到这里。思和职称问题,去年已解决,现在一切正常。
问候应红好!任敏附笔问候你们好。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四日)
不到三个月,北京出现大事,有消息误传我失踪了。其实,我在家中,因为没有电话,未去单位。消息传到贾先生那里,他听说了,当场号啕大哭。
后来听到这个消息,我为之感动。这就是一位恩师对弟子的关爱,在先生和师母那里,我们总是感受到父母一般的温暖。我很快去信,谈到我们的一切均好。贾先生很快于七月二十六日回信如下:
收到你们来信,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因为那件事变之后,我们就惦记着你们,大家都悬着一颗心。得悉你们平安,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