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
二〇〇〇年秋天,在罗马尼亚访问,一天到了一个地方,迎接我们的一位作家对我们说,他们那里前不久刚刚翻译出版了一部中国长篇小说,四大卷,写的是公元三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一场战争。这位作家说,他还没有看到这部书,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当即,我想了想便对这位罗马尼亚同行说:“可能是《三国演义》吧?”这位同行点了点头回答我说:“是的,是发生在三个国家之间的一场战争。”
再后来到一位罗马尼亚朋友家里做客,谈话间,这位朋友骄傲地告诉我们说,他家里保存有一部中国小说,而且这位朋友更以生硬的发音对我们说:“是《将皮迷》。”大家一听,明白了,是《金瓶梅》。而且这位罗马尼亚朋友还告诉我们说,这部中国小说他们一家人都读过。这时,他的岳母大人,一位年近八十岁的老太太立即又对我们说,她也读过这部《将皮迷》。
当然,翻译介绍到罗马尼亚去的中国文学作品,绝对不只是那部描写发生在三个国家之间的一场战争的历史小说,也不只是那部连八十岁的老太太都读过的《将皮迷》,自然还有许多古代的、现代的和当代的中国小说被译介到了罗马尼亚。阅读这些文学作品,使罗马尼亚人对于中国有了一些了解,也在中罗两国人民之间架设起了一座相互沟通的文学桥梁。但是面对着这样的同行,我一点也不想和他探索中国文学的价值,更不想对这些朋友描述这些作品的艺术魅力。

但我依然感到,文学作品的相互翻译,确确实实在不同国家和不同人民之间架设起了相互沟通的精神桥梁,但也仅仅就是桥梁,是站在桥上看风景的桥梁,是一座即使你走下桥来,也无法融人那一片秀丽景色的桥梁。因为,那一片秀丽景色只能植于那一片母语土地,一切从母语本土移植到另一片土地上去的花木,都只能是那一片风景的缩微,或者使用一个科技词汇,叫做一次小小的压缩,你永远无法消除你和那一片风景的隔阂,因为你只是一个站在桥上看风景的游客,你不是在那一片风景中呼吸的生活主人。
时代的进步使我们这一代人过早地接触了外国文学,那时候我们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山不在高”,课堂下听母亲讲“春眠不觉晓”,晚上围着叔叔听他讲《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再回到自己房里偷偷地读《茶花女轶事》。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少年时期典型的读书环境,那真是一个各种思想、各种艺术争夺少年心灵的无情斗争。只是说来也怪,那时候无论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或者是《茶花女轶事》,还有娜拉走后怎样,虽然也打动过我们的心,但到底还是觉得那一切距离我们太远太远,我们最能够理解,也最容易接受的,还是“山不在高”,还是“春眠不觉晓”。至少在我们的心间,只有“山不在高”和“春眠不觉晓”才是属于我们的文学风景,也只有在这一片风景里,我们才能感受自然,也才有属于我们的精神世界。
于是,《一千零一夜》、《茶花女轶事》和《玩偶之家》都只是一座桥梁,我们站在这座桥上看风景,然后回到我们自己的土地,这里有“山不在高”,还有“春眠不觉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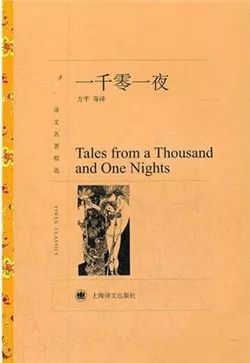
《一千零一夜》
终究,我们生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代不给我们赏析艺术的情境,彼时彼际,那么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来,我们也只能是从那些作品中吸取精神力量。于是一切歌颂英雄的,还有一切歌颂献身的文学作品都被我们当作人生课本,并以此充实我们的心灵。回首我们的读书生活,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中能有几人真正潜下心来体味那些传世作品的艺术情趣?就连《红楼梦》,不也是被理解成“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了吗?如果,在文学这座桥梁上,人们不是看风景,那就是看斗争了。
说到我们和外国文学的关系,再说到我自己和外国文学的关系,实实在在,我们似乎还没有进入到艺术赏析的境地,说是在桥上看风景,也是把我们自己说得风雅了。
难道不是这样吗?
当我们前辈的爱国精英辜鸿铭先生,为了在洋人面前炫耀“中国人的精神”,挺身而出,面对洋人以流畅的英语背诵全卷《失乐园》的时候,谁能说出这位辜老夫子到底理解了多少《失乐园》的精神真谛?倘若他真能理解哪怕是一点点《失乐园》的精神真谛,他也不会于洋人的坚舰利炮早已经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而且一次次的割地赔款更丢尽了天朝威风的时候,居然还大言不惭地站在洋人面前说什么“我们如何如何的时候,你们还在茹毛饮血”。这就是拖着长辫子背诵《失乐园》的夫子圣贤们的世界,他们站在桥上,却不屑于看风景,他们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了!你算是什么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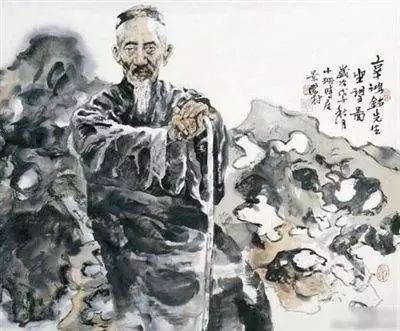
辜鸿铭
心灵上的森严壁垒,使辜老夫子无法走进那一片美丽的风景,最后他只能在“你们有先进的物质,我们有先进的文明”的感叹中愤愤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个人精通几国外语,却不能从西方文化得到一点点启迪,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了。
却又是另一种残酷的惩罚,又一代人,完全没有一点点外语知识,一句英语不会说,连英文字母也不认得,竟然读过几本翻译得令人不敢恭维的外国文学作品,一下子就进入什么流派了,而且大言不惭地标榜进行什么文体实验,将一些于理论上无法界定的主义生搬到写作上来,闭关锁国之后,我们在外国文学的冲击面前失去了理智,更失去了冷静,中国新一代作家于写作上陷进了一个迷乱的误区。
很难再有辜鸿铭老人那样的学者,于深厚的国学基础之外,更精通几门外语;也很难像三十年代作家那样,有充分的创作准备,他们能于写作的同时,再以自己的艺术情趣为读者选择值得向国人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现在的状况是,一些人疯狂“码”字写作,另一些人匆匆“输入”外国文学作品,也就是在疯狂“码”字和匆匆输入的坐标上,才出现了一股一股文体实验的旋风,也才出现了一个一个的写作怪胎。
恕我放肆。
检讨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国作家和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界引发的几次大冲击波,其中很有几次带有极大的盲目性。那些在中国文学界引发冲击波的外国作家,原来在他们自己国家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们或者是
他
们的作品远不是他们国家最高的文学成就。但一被介绍到中国,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一下子就使得这些作家成了世界文学的精英,也使这些作家的作品成了传世的杰作。而当这样的消息传回到他们国家的时候,那才真是使他们自己的国家大吃一惊,使得人家简直不能理解,怎么中国竟出这类咄咄怪事。
大家都不会忘记一部日本电影《追捕》,其中的女主人公真由美,在日本本来并不被人们注意,但一被介绍到中国来,这部普普通通的日本电影竟然成了经典作品,连真由美也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道理呢?莫非中国观众慧眼独具,竟然赏析出了在原出品国不被重视的艺术珍品的艺术魅力了吗?不是,原因非常简单,就是这部电影是在我们打开国门之后最先看到的外国电影。真由美是幸运的,她一举成名,成了中国观众心中最富魅力的电影明星。

《追捕》剧照
那么在文学界有没有这类现象呢?第一个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作家,是否也被中国读者或者是被中国作家奉为杰出作家了呢?而且,前一个月这位杰出作家的作品才被翻译过来,第二个月就看到了中国作家的效颦作品,随之就有批评家出来喝彩,为我们终于参与了世界文学对话而兴奋不已。
在外国文学面前,中国作家是一个不设防的方阵,活像是非洲为找水而不停迁徙的灾民。一个一个的创作口号,大多是在一部什么外国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之后提出来的,而一个一个的文学口号又都是在没有出现一部有价值的作品之后退出文坛的,反省我们这些年的写作经历,中国作家难道不应该吸取一点点什么教训吗?
在艺术创作上,一切的效仿都是可悲的,即使拉丁美洲有过文学爆炸,即使“魔幻现实主义”(且不说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是否准确)产生了重要的作家和重要的作品,但中国作家紧随其后的效仿作品,都不可能进入这个艺术流派的主流空间,甚至于这些作品都带有游戏色彩,至多也就是在圈子里换取到一点儿喝彩罢了。这许多年来,效仿“魔幻”的作家堪称多矣,只是成功的作品并没有见到,结果“魔幻”了一阵,也就没有“魔幻”了。
阅读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欣赏我们中国作家的成功作品一样,于我是一种莫大的艺术享受;这就和读书时背诵《莎翁故事》一样,我们只能是用心灵去感受它,以唤醒自己心中最圣洁的情感。但就算是那样钟爱莎士比亚,我们谁也没有想过将来自己也写一部那样的作品,因为那一切只属于莎士比亚。即使我们阅读莎士比亚,也依然是在桥上看风景,属于莎士比亚的那一片风景,绝不是我们自己的母语大地,有出息的作家,只能在自己的母语大地上开拓出属于自己的美丽风景,按照你在桥上看到的风景复制出来的风景,是没有艺术生命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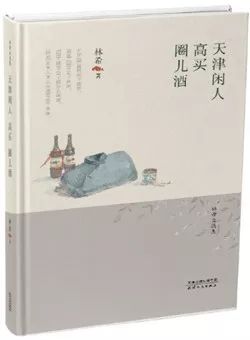
《林希自选集-天津闲人·高买·圈儿酒》
而且任何一位译者对于外国文学的选择也都有自己的标准,当然这还是说“标准”,自然也有一些译者“选择”外国文学作品就是着眼于市场效应,我们还看到有的译者,只能译介他们能够胜任的外国文学作品;于是许多垃圾被介绍到了中国,再加上一些书商不负责任的运作,中国就真成了一个文化大垃圾场。
赏析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享受,效仿外国文学作品则就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了。我自认为是一个开放型的作家,更是一个开放型的读者,我于阅读上所得到的愉悦,有时真的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但我于写作时,从来也没有为自己树立过任何参照,因为我想让我的读者站到我这座桥上来,能够看到他们在别处看不到的风景,至少不要让他们在我的这座桥上看到风景之后,再让他们联想到似是在什么地方也看到过相似的风景,一切的艺术都是个性的艺术,再杰出的作品也只能是我们在桥上看到的风景,它们绝对不是我们自己的艺术领地。
我与外国文学,于赏析上距离很近,于写作上拉得很远,赏析上的亲近,使我能够用心灵去感觉外国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写作上拉得很远,因为我要创造一道属于自己的风景线。我潜心写作几十年,可能没有人能说出我的写作和一位什么外国作家的作品相近,我自己更说不出我受了哪位外国作家的影响;但可以说,没有外国文学作品对我的熏陶,我不可能有这样的写作心境,我也不可能有对于我来说是得心应手的表现手法。我没有存心戒备过外国作家和外国文学作品对我的影响,但我心中总有一道不可逾越的艺术防线,这道防线就是我自己从属于其中的母语大地。
我与外国文学,永远是我在桥上看风景;正是这一道道美丽的风景,激励我去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风景线。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1年第2期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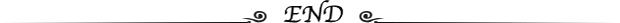
《世界文学》征订方式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银行汇款
户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开户行:工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账号:0200010019200365434
微店订阅

★ 备注:请在汇款留言栏注明刊名、订期、数量,并写明收件人姓名、详细地址、邮编、联系方式,或者可以致电我们进行信息登记。
订阅热线
:010-59366555
订阅微信:
15011339853
订阅 QQ:
3076719982
征订邮箱:
[email protected]
投稿及联系邮箱
: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