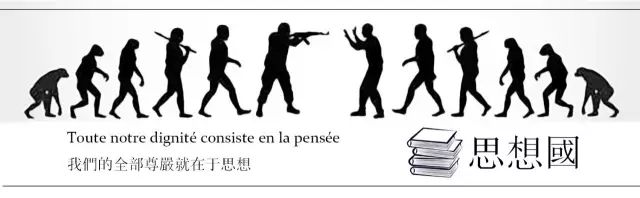

前面说了,由于近日要看的书太多,我不想在批评鲁迅上浪费时间。今日误以为是周一,而实际上是周日,于是便有了种喜从天降、多活一天的错觉。想着公号文章好多天没有写了,不如将今日这意外增加的时间用掉一点。
上篇文章 (
也叹中华文化之花果飘零 | 熊培云
) 只有一小段提到了鲁迅,本意是为了抗议许多公号被封的。没想到大多数留言竟是批评我对鲁迅的看法,有些人就直接开骂了。实话说,这种“太岁头上动土”的感觉并不好。由于历史原因,直至今天,仍有两个人在中国是不能被轻易批评的:一是毛泽东,二是鲁迅。前者毋庸讳言,政治自然是主要原因。至于后者,则要复杂得多。关于这一点,我后面会有文章展开。当然,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在1949年后的中国被圣化。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通盘否定鲁迅,他在文学上是有些成就的,但在其他很多方面,我实在不敢恭维。比如逻辑水平、政治见识、舍本逐末的对国民性的批评等等。而这一些和我喜不喜欢胡适没有一点关系。在我这里,胡适也是可以被批评的。可惜的是,许多研究鲁迅的人,缺少对鲁迅的批评,而只是在解释他何以成为“民族魂”。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我倒是愿意多做一点。
比如我在钱理群先生的讲座文章《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中就读到这样一段话,“……我现在成了习惯,无论面对什么问题都要想起鲁迅。而且每一次都确实能够从鲁迅的研究里面找到新的资源,得到启发。所以这些年,即使在我不讲鲁迅的那些文章里面,还是可以看见一个鲁迅生命的存在。而且我只要面对青年,就情不自禁的讲鲁迅了,因为我从进入学术界开始就给了自己一个定位,就是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我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看来要坚守到我死为止,这已经成了我的历史使命和宿命。”
这段话读来很悲壮,在某种程度上也令人感动,但经不起分析。前者,让我想起马斯洛的话——一个人如果手里只有一把锤子,那么看什么问题就都是钉子。迷信上帝的人相信上帝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迷信组织的人相信组织伟大、光荣、正确……可是,人是不能过于迷信的。不是说吗,就算是一个宿命论者,过马路也要看红绿灯。至于后半部分,我也不认为这是学者的态度。如果钱先生将自己的使命定为让青年人像他一样去迷信鲁迅,我有些不解的是,这究竟是做学问,还是搞宣传?
如果读者反对我的上述观点,容我以后说得更细致一些。
在研究方面,我更喜欢唐德刚先生的态度。我是通过唐先生的《胡适杂忆》开始认识胡适的。后来我通读《胡适文集》,并写了《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算是我的一篇读书心得。唐德刚对胡适从来没有到迷信的程度。在《胡适杂忆》中,他批评了胡适在经济学方面的不足,同时在其他行文方面也多有调侃。
比如唐德刚批评胡适没有在1917年拿回博士学位是因为“花心”:
胡适之这位风流少年,他在哥大一共只读了21个月的书(自1915年9月至1917年5月),就谈了两整年的恋爱! 他向韦莲司女士写了一百多封情书(1917年5月4日,《札记》),同时又与另一位洋婆子‘瘦琴女士’(Nellie B. Sergent)通信,其数目仅次于韦女士(1915年8月25日,同上)。在博士论文最后口试(1917年5月27日)前五个月,又与莎菲(陈衡哲)通信达四十余件!在哥大考过博士口试的‘过来人’都知道,这样一个神情恍惚的情场中人,如何能‘口试’啊?!这样一位花丛少年,‘文章不发’,把博士学位耽误了十年,岂不活该!(《胡适杂忆》,增订本,1999)
作为胡适的入室弟子,唐德刚的这段文字,算是有些随心所欲,也因此受到了来自夏志清先生的批评。夏志清列出了胡适当年的成绩单,英文成绩少时也有80分,多时为96分。更别说与韦莲司写信交流或者恋爱也是有益于提高他的英文成绩的。
这些都不是关键,我想强调的是唐德刚对胡适的这种态度。
这是学者对学者的态度——可以欣赏他、爱护他,但并不仰视和包庇他。
也是因为这种平等的态度,尤其在我将胡适与董时进先生对比时,我很快发现了胡适身上的不足。胡适先生盛名虽然远在董时进之上,但就对中国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董时进有更独到之处。关于这一点,亦容后再叙。
原本想写篇长文批评鲁迅及其研究者钱理群,前些天在路上一共拟了二十个小节,但是实在没有热情和精力一次写完,毕竟手头有更要紧的事做。今天从文本分析上略谈鲁迅的逻辑。
先回到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那场著名的有关文艺自由的争论。当时,一些左翼如瞿秋白、冯雪峰、鲁迅等人从阶级斗争的立场主张将文学一分为二,于是便有了好的无产阶级文学和坏的资产阶级文学(反动文学)。而以胡秋原、苏汶、梁实秋、戴望舒等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文学具有创作与审美的独立性,不为政治左右,不应做政治的留声机。由于不支持左翼对文学的粗暴划分,这些人甘为“第三种人”。
事实上,“第三种人”强调文学的价值时,并不表明他们是“艺术至上主义者”。在苏汶看来,文学作者追求艺术价值,和医生之讲医学,律师之讲法律一样,是他们的本行,这里面决不是定要包含什么“看不起艺术之外的其他一切东西”这种意味的。苏汶反对一些革命者借革命来压服人。因为那些人“处处摆出一副‘朕即革命’的架子”。
与此同时,苏汶特别批评了瞿秋白等人将左翼革命文学视为武器。“而他们之所以要艺术价值,也无非是为了使这种开口作用加强而已:因为定要是好的文艺才是好的武器(实际上应当说,好的武器才是好的文艺)。除此之外,他们无所要求于文艺。”“他们左一个意识形态,右一个意识形态,以要求作家创造一些事实出来迁就他们理想中的正确。”问题是,“整个的革命都可能有错误”,那些文艺指导家们如何保证自己正确?而且,越是在斗争混乱、空前变化的年代,文学越要保持其独立性,其好处在于可以帮助身处其中的人们认识社会。
鲁迅无疑是相信“武器文学”的。他直接否定胡秋原、苏汶、梁实秋等人的“第三种人”立场,认为在阶级对立的时代,想做“第三种人”是不可能的。在《论“第三种人”》一文中,鲁迅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其后,他又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又论“第三种人”》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再次指出做“第三种人”之不可能。
鲁迅打比方说:
“所谓‘第三种人’,愿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
我曾在评论课上和学生们谈到这篇文章。且不说常识告诉我们大自然中并非只有黑白两色,就本文而言,鲁迅的逻辑推理也是漏洞百出的。
按鲁迅的意思,当年的中国有两个阵营,一种是胖子阵营,一种是瘦子阵营。有胖子阵营里住的都是胖子,在瘦子阵营里住的都是瘦子。但是他接着又说了,人与人在一起,总还是可以分的。这不就是“胖瘦相对论”吗?既然如此,那你还坚决啥?
也就是说,无论是在胖子阵营里还是在瘦子阵营,仍可以分出个胖瘦来。胖子与瘦子,因此是相对的。既然是一个相对的比较,怎么得出一个绝对的胖子和瘦子的阵营,并且使他们水火不容呢?又凭什么说瘦子一定好,胖子一定坏呢?更别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人有可能变胖,也有可能变瘦,并没有一个绝对值。在此意义上,原先的胖子阵营与瘦子阵营也就根本不存在。事实上,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而不是一个非友即敌、非胖即瘦、非白即黑的世界。
在我看来,以阶级斗争立场否定“第三种人”,否定社会的丰富性,无异于肯定弱肉强食的政治而否定社会自身的价值。
如果按鲁迅比一比就知道胖瘦的逻辑,这世界上何只有“第三种人”,更有第一亿种人,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在价值观与审美取向完全一致的人。
鲁迅曾经在演讲中说,胡适当年领导新文化运动是穿着皮鞋进来的,而后的普罗文艺是光着脚进来的。对于鲁迅否定存在第三种人的观点,梁实秋引用报章上的评论揶揄说,“鲁迅先生演讲的那天既未穿皮鞋亦未赤脚,而登着一双帆布胶皮鞋,正是‘第三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