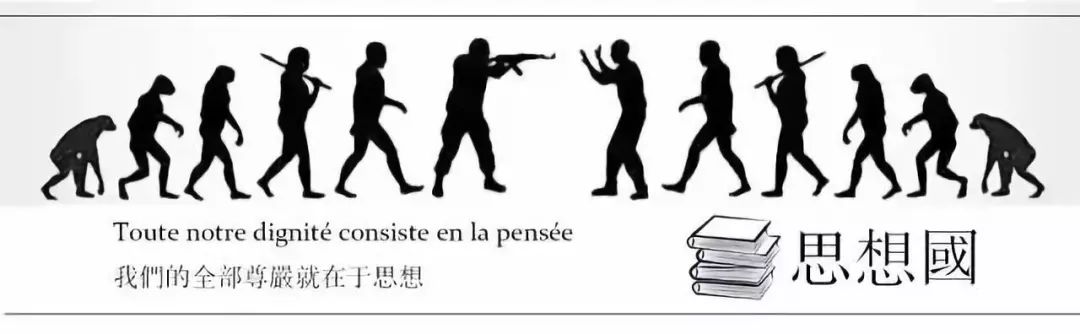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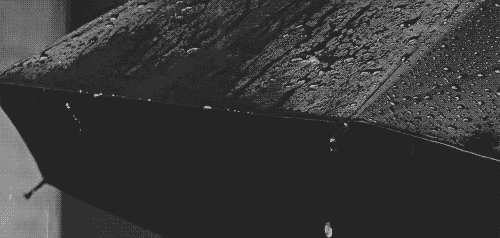
最近又回了一趟江西老家。由于经济上落后于周边省市,有人戏称江西是“阿卡林省”(阿卡林)。大意是说江西没什么存在感。然而,这依旧是我回去最多的地方。迄今为止我最怀念的写作仍是《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转眼间这本保证了“一个字也不删”的书即将出版十年。十年间,说乡村发生了巨变也不是不可以。以最近几次返乡的所见所闻,我决定继续花一些时日来关注并记录这片土地上的变化。
与此同时,对于不断回到故乡我也是有些不安的。昨与一江西籍作家聊天,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不断回到故乡也意味着“
故乡的死亡
”。似乎只有远离故乡,才可能拥有故乡之幻象。
抽空看了张艺谋的最新电影《一秒钟》。影片分几条线索讲述了幻象与实体之间的关系。作为极富想象力的人类,谁能逃离对幻象的迷恋?更别说,幻象常常不只是幻象,还是实体本身。这不仅体现在我们时刻生活在种种幻象的包围之中,而且,
一旦失去了某段爱情或者机会,人就难免像得了幻肢症一样日夜疼痛。
和很多观众一样,《一秒钟》唤醒了我有关童年的一些回忆。可以说,那时候我生活中最神秘的事物除了夏夜头顶上的星河,就是水稻田边的露天电影了。它们一个为我拓展天上的事,一个为我拓展人间的事。若干年后,当我回想起那些露天电影时,恍惚之间,仿佛看一幅幅悬挂着的星空。如果拒绝诗意,当然你也可以将屏幕想象成一块硕大的白色兽皮,只是被裁剪得方方正正地挂在墙上。
必须承认,小时候的我只是一架接受信息的机器,仅以本能之躯,被动地跟着各种剧情走。虽然那时生活中也有忧愁,但精神活动基本上只是条件反射。每日活在一个表象的世界里,对于影象中的光怪陆离,基本上没什么理解。
甚至,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我也都是木然的。

想起祖父过世那年,我不到十岁。按当地风俗,出殡时作为长孙我坐在祖父的棺材上,被几位“八仙”抬到坟地。很难想象,一路上我居然没有一滴眼泪(是不是有点像《局外人》开篇中默尔索的麻木不仁?)若干年后,回想当时懵懂无知的情状,和接受一群大人手忙脚乱地教我骑自行车,其实并没什么两样。
直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内心对人和世界渐渐有了些朦胧的爱意。为此,我写了一首月亮与爱的短诗。如果没有记错,我是坐在村中最大那棵树的树根上完成的。多年以后,我甚至听到了灵魂呱呱坠地的声音。
我猜想自己以前是没有灵魂的,我的灵魂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在那个想象中的月夜偶然捡到的。算是“后天得来的先天”。
太阳教人合群,月亮教人独处。这是我所理解的日月造化。或许可以说,正是从那样的一个月夜开始,我无意间捡到的一粒灵魂的种子,因之才慢慢有了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
大概也是在我开始写诗的那年,有一天晚上做数学题时突然想念起爷爷来。虽然只有很短的几分钟,但对我而言却是一个标志性的精神事件。
由此推想,我灵魂之破土而出,可能源于生命中有两个变化:一是开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关于爱);二是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失去了什么(关于死亡)。
想起不久前偶然读到诗人威斯坦•奥登的一篇文字,其中两段话让我印象尤其深刻。
一段话是关于数学家的——“数学家的命真好!只有他的同行才能评论他,而且评论的标准又是那么高,他的同事或对手如若真能赢得名声,那也是当之无愧的。”
我这辈子与数学研究这个行当无缘,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否则我的生活将会无比简单。
而
意义世界常常让人无所适从,所以有的人将某一种意义视为真理去侍奉,像打清一色一样拒绝一切杂牌。
而我无法接受这种思想上的偷懒。如果是研究数学,直接有货真价实的真理可以追求,又何乐不为?
另一段话恰巧也是有关神秘性的。奥登说,“
每一个有独创性的天才,是艺术家也好,是科学家也好,都有点像一个赌徒或巫师,身上总要带三分神秘色彩
。”
相信每个人的生命都另有神秘,与此相关的常见问题是
我的灵魂来自何方。同样让我不明白
为什么在那一年会爱上了诗歌,甚至沿着这条小径,渐渐爱上了由无数意象构建的隐喻世界,甚至包括深藏其中的苦难。
而现实中的苦难也是真实存在的,包括扰乱、贫穷、饥荒、疾病甚至死亡等等。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苦难生长于人的内心。换言之,
苦难有两种:一种是来自客观世界的苦难,一种是来自主观世界的苦难。
在前一种苦难中,人是客观世界的附庸,必须接受。如果不能接受,那就改变事实,比如消灭上述扰
乱、贫穷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来自群体的努力
。而在主观苦难中,主观世界同样是意义世界,如何面对这种苦难则主要取决于个人内心的决断和意义的赋予。
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昨日午睡醒来时脑子突然有一个声音——“
我
唯一真实的苦难,是对世情与人情的巨大失望”。
这也的确是我过去甚至此刻正在经历的。而如果从一开始就不抱任何希望,视世事与人情如风云草木,也就不会受那么多无谓的苦难(如果信奉“痛苦的深度就是人生的深度”,当然也可以躺在苦海之上晒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