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卫民(吉林集林),吉林人,集吉林币。
涉泉三十载,徒沾两脚泥。所汲无长物,痴心仍未遗。出生至今,尚未发现有比收藏更具趣味的事情。因而,旁无他骛。
工作之余,擎币在手,一切烦杂便烟消云散。虽置身闹世,却如入桃庵,堪为苦旅之中的精神家园。
老高丽卖龙洋——统统一麻袋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吉林币颇有影响的两次批量露市我全赶上了。两次出币都极具传奇色彩,不单币的质量令人拍案叫绝,过程更是让人啧啧称奇。
吉林往东200余里,有座小城名曰蛟河市,听听这名——蛟河,卧虎藏龙啊,不和龙洋有关系才怪呢。事实上就是这样,现存于博物馆的两枚厂平一两,也是当地仅见的两枚一两龙洋,就出自这个地方。要说这蛟河有多么人杰地灵,那倒也不见得,蛟河满语“蛟别拉”,狍子沟的意思。狍子何物?猎人最知道,似鹿非鹿,似羚非羚,打偏一枪都不动地方的主儿,愣呆那挺着。东北话骂人,傻狍子吗。可见以这种动物命名的城市,人也聪明不到哪去。要不咋一件好玩意儿也没留住呢。傻人有傻命儿、傻地儿有傻福,偏偏这样一个地方,被满清统治者划在了柳条编的封禁范围之内,与“吉林打牲乌拉”成为皇家的狩猎围场和进贡土特产品的风水宝地。特别是专供宫里吞云吐雾的一亩三分地儿的皇封烟,更是名贯古今。由此而论,在满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屡出吉林币窖藏就理所当然了。
蛟河当时的古玩市场规模很小,满摊子不足10个人,是由几名集邮爱好者发展起来的“路边倒”。平日靠在路边倒卖些真不真假不假的玩意儿维持,偶尔也能碰上一两件农村人送上来的“大货”。届时,热闹场面溢于言表,各类脸谱粉墨登场。递眼色的、打手语的、敲边鼓的、哄抬价的频频亮相。我也在其中之列,但胆小力薄,从没敢抢过同行生意,怕挨揍。尽管如此,也不能成为消极怠工的理由,我转变战略以守为攻、以退为进,施行曲线迂回战术。我瞄准了最能收货的老弓头果断开火,各种型号的糖衣炮弹轮番轰炸。目的只有一个:拿下他的胜利果实,发动和平演变。实践证明,方针是正确的,效果是显著的,从此不用再较场厮杀劳神费力,尽可坐山观虎斗、摇扇看风景。只要事后加个“吉林价”,便可坐享其成。何谓“吉林价”?就是蛟河的贩子把收来的东西拿到上一级城市去卖,吉林人给出的接货价。这种买卖关系看似简单,实则有其严密的组织纪律。买卖双方达成了一项不成文的供求合同,即接货方不论收上来的东西是真是假、价高价低,都要来者不拒,以保障货源的垄断性;送货方则必须只把货卖给下家,以求得一旦走眼挨蹦,不至于血本无归。能在这种关系网中进行截留,也是冒大不韪的。

这老弓头上上下下是很有些人气的,货能收下来,又能卖出去,所以周围总呼拥着一群收藏爱好者,希望捞点地板价一手货的东西。这其中有一个满口金牙的老高丽,老高丽说老不老,50多岁,玩轮子出身,东跑西颠的见过世面。知道古玩赚钱,便半路出家,整天候在老弓身边长见识。一来二去,两人处的不错,老高丽对神通广大的老弓头深信不疑,并学会了区分什么叫龙洋、什么是袁大头。仅凭这点道行,一锹下去便挖到了他的第一桶金,确切地说,是比金子还要珍贵的龙洋——壹麻袋的吉林银币!

那天早晨,据说是初闯江湖下乡收货的老高丽回来了,满摊子的人各自怀着复杂的心情,期待着老高丽会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出现,可始终没见他的人影。临近中午,一直按兵不动的老弓头悄悄把我拉到僻静处,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你给我看看真假?”,接币在手,我立时两眼放光,天神!一枚深打、全鳞、未使用的吉林庚子中元,在近午阳光的照耀下,发出炫彩的五色光芒。我干咽了一口吐沫:“老大,啥时收的?”,“你就别管了,看看真假吧”。我知道老弓的底细,玩了大辈子邮票的他对币一窍不通。“这得仔细了,现在高仿都绝了,要不我拿着研究研究?”。“完了再说吧,不止这一块呢”,“都是这?”,“都是这”。整个下午,我都在坐卧不安的煎熬中度过。从我手接过币,老弓头就把它大咧咧地揣在了后屁兜里,下他的棋去了,肥厚的屁股不停地在马扎子上拧来拧去。估计那娇嫩的裸币在这粗暴的蹂躏下花残柳败了。我一再提醒他包好放在上衣兜,别坏了品相,他都不屑一顾。径自把棋子摔得趴趴三响,挂满白沫子和食物残渣的大嘴,一刻不停地和对手唇枪舌剑地过招。望着他那一脖颈子的堆肉当时我就想,你要是我儿子,我非把你脑瓜子削放屁了不可!这么个粗线条的壮汉怎么会从事上这高雅的行当的。还好,我没有这样的儿子,摊子上也就少了一出老子暴打儿子的解闷戏。

终于捱到傍晚收摊了,老弓头一使眼色,走。左曲右绕,一路穿行。嗯哏?老高丽的家。“拿给他看看”,老弓头指挥着。老高丽毕恭毕敬引我们到了内屋。天神!上帝!佛主!圣母玛利亚!除了邪教我所有的神明啊!仿佛阿里巴巴念完了芝麻开门的咒语,满满一麻袋冒着亮光的银币呈现在眼前!未及我制止,老高丽扯住袋角哗的一声,把币摊在了地上。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大元、中元、两角、一角、五分!清一色的淡彩币!我靠!老毛子把造币厂给端了吧!我一枚枚捡视,品相都出奇的好!这么多年号集中在一起未流通,令人匪夷所思。从进门到现在,我仿佛置身在神话世界里,头脑晕呼呼地像喝了一棒子60度的烧刀子。亏得是当时那个年龄,如果今天让我经历这种场面,一脑瓜子血管全都得干爆喽。“这老高丽真有电,一下子在他老家抠出这么多。你给看看是真是假的吧”老弓头关心的还是这。“币没问题,准备,。、。啥价出啊?”我懦懦地问,明显感觉到没有底气。“300的整”老高丽脱口而出。我倒#$¥%^&*@!“他一袋子总共300来的,想300一枚卖”,老弓头帮着翻译。我眼珠子都快要掉下来了。“但要一枪打”,我再倒#$¥%^&*@!。一麻袋啊,一枪打是个什么数字啊。“这个也300?”我拿出一枚间杂在里面的小日本圆孔镍币。“亚”,“这个也300?”我举起一个庚子大元。“亚”。“那我给你3000一枚挑几枚行不?”。老高丽决然地摇摇头:“币的我不懂,你把好的挑走了,孬的谁的买”。“我不管好孬,就是喜欢大个的,你随便给我抓几块”我无力抗拒,苍白争取。老高丽嘴一咧,大金牙十字星光恍疼了我的眼。“不要就拉倒,要滴统统一麻袋!”。长春高粱米没吉林高粱米大呀。我知道,这批币蛟河留不下啦。当时的心情可以用悲愤来形容。高调地说,我为省内留不住地产币而感到难过。作为一个爱币者,更为这些即将离开故土远行的百年精灵而担忧,茫茫前路不知将流向哪里,更要遭受多少颠簸和磨砺。有一天重逢,我还能在满目风尘中认出你么……

几十万元在当时的蛟河是没几个人能拿出来的,况且真正的收藏者手中并没有太多的人民币。在中级以上的城市中,驻扎着许多发达地区过来的币商,通过他们的手,把当地人接不住的大货,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京津沪等大集散地。没过几天,老弓头领来了沈阳的一位二传手,包括一块钱一土篮子的日本垃圾币,悉数以每枚300元的价格一枪打了。圆了老高丽统统一麻袋的夙愿。而后的若干年里,老高丽一直沾沾自喜,炫耀他能把日本10钱卖到300元的价格。吉林大元突破3000元的时候,老高丽沉默了。普通的吉林大元闯进万元线的时候,老高丽已不知去向。有人说他去了南韩卖苦力。这倒霉孩子,他赚洋钱的时候,正是韩币比率最低的冰点。

作为牵线搭桥的回报,老高丽让老弓头不重样地挑了一套相送。消息传开后,这仅存的一套币立时成了整个地区币商和收藏爱好者争相挖掘的宝藏。我自然不能让这些遗孤再继续流浪,我的脑海中老是有这样一种幻象:那些被装进麻袋掳走的精灵,临别时眼巴巴地看着我,见我实在施救无望,留下哀伤的嘱托——照顾好这些孩子,让他们永远留在故乡的土地上!
老弓头被彻底整毛了。锲而不舍的挖掘手、频频升高的收购价,每日笼罩着他。让他难以估量出这套币的价值,“明天卖肯定比今天卖还要高”,这是他得出的结论。因而,来了一个我有你没有,就是不出手。不出手,好好搁着也就罢了,他天天拿在手里攒,哗啦哗啦地吊人胃口。麻辣个八字的,再攒几天圆光币就磨成银坯饼了。我必须挺身而出了,他这样不善待这些孤儿,多在他手里呆一天就是对她们多一次的犯罪。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老弓头过意不去,终于答应给我四块中元。乌拉!已经是虎口夺食了。岀币的消息更加刺激了挖掘手的欲望。转年,一个并不懂吉林币,也不为收藏,更加不差钱,却闹腾得最欢的阔佬,以帮老弓办理行政手续为由,挖走了四枚中元,转手卖掉了。同年冬天,又被他买走四枚,不知流散到哪里。至此,凭我微弱的力量,仅留住四枚币在她故乡的土地上。 其中,就有厘改分名版一枚。


厘改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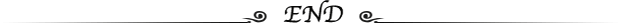
 说明:本文为钱币圈征稿的原创文章,转载请联系授权。
说明:本文为钱币圈征稿的原创文章,转载请联系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