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就说这辈子我就干这个事了,这个事太牛逼了。”
1998年,刚进武汉电视台工作的范立欣,被一本中国纪录片年度会议纪要所吸引,兴奋地读至次日凌晨,那年他21岁。
高高瘦瘦、相貌俊朗的他,经常给人留下“萌大叔”、“长得太帅不像纪录片导演”的印象。但他的镜头,记录的却是最具泥土气息的真实中国。
/ 人生是有计划的自我积累 /
“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远景的规划,我在想,要把一个事情做到世界顶尖的水平。”
发现对记录片的热情后,范立欣学摄影,做剪辑,用他的话来说,这叫“有计划的自我积累”。

2002年,同在武汉电视台工作的陈为军邀请他参与并剪辑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
在河南的一个贫困村里,一些村民靠卖血维持生计,由于缺乏安全的医疗器械,艾滋病在那里悄然传播……
第一次参与纪录片工作的范立欣,以每天16个小时,连续10月的工作量走进这个特殊群体。
面对悲苦的画面,范立欣反复地问自己:“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后来,范立欣去央视做摄像记者,经常飞去农村进行采访。他说,每当从贫穷的农村回到繁华的北京,他的内心都会因为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而受到冲击和折磨。
“对于我来说,回到舒适的生活中只需要两个小时,而对他们来说这太遥远了。”
/ 哪里是他们的归途? /
2006年底,范立欣离开央视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纪录长片,关于农民工的《归途列车》。

《归途列车》剧照
为了寻找合适的拍摄对象,范立欣独自坐火车去广州,一家厂子一家厂子地寻找拍摄对象,同时不断地被人当做骗子、小偷,十次有八次被人直接轰出去。
最终,范立欣遇到了
影片中的张哥夫妇,找到了
最理想的拍摄素材:
16年前,为了补贴家用,张昌华夫妇背井离乡去广州打工。对他们而言,唯一的希望与慰藉就是孩子们有朝一日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然而,由于他们常年在外打工,无暇顾家,日渐成年的女儿以激烈的叛逆行为宣告对父母的抗议——张琴退学离家,成为新一代的打工妹,从广州的服装厂到深圳的夜店,女儿的一次次选择刺痛了父母的心……
2008 年,由于南方大雪灾,范立欣和他的摄制组与几十万返乡人一起滞留在广州火车站,在留守拍摄的三天里,他们被情绪激动误以为他们是记者的群众包围,现场几经失控。
相比于拍摄过程中险些遭遇的踩踏事故,范立欣认为,最残酷的现实还是资金。
和大部分纪录片导演一样,他得自筹资金。范立欣拿出10多万的积蓄,又借了20多万;为了省工钱,摄影师是他同事,录音师是他哥哥。即便如此,到2007年底还是弹尽粮绝。
范立欣当时只觉得,这个题材太重要,承载了很多,砸锅卖铁也得拍。
“我希望用这部影片,以及未来用更多的影片给他们一个交待,因为他们为这个国家牺牲和付出得太多,他们也是这个国家的脊梁,理应被记录下来。”

《归途列车》剧照
3年,每年至少5、6个月的跟踪拍摄,积累成350个小时的素材,最后剪辑为87分钟的电影。
“希望每个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能更多地去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哪怕只是在公交车上给他们让个座。”范立欣说。
/ 站在悬崖边,你敢不敢纵身一跃? /
从对纪录片萌发热情,到以纪录长片享誉国际,这一路范立欣走得很辛苦。
“他是个很坚毅的孩子,但凡不是这么坚毅的性格,人是坚持不下来的。”
他的母亲说。
范立欣的毅力从他为克服伤痛所付出的努力就可见一般。
因为幼年的摔伤手术,范立欣的左腿膝盖只剩下三分之二。为了承受几十斤重的摄影器材,进入央视成为摄影记者后,“范立欣每天早到单位一小时,偷来锁着摄影机的柜子的钥匙,分开双腿,调整呼吸,练扛机器。一年后,他成了电视台里扛机器最稳的人。”

和很多纪录片作品一样,虽然历尽艰辛,虽然拍的是最接地气的内容,范立欣的这些作品还是很难在国内院线上映。
但在范立欣看来,社会需要具有“看门狗”(watchdog)属性的纪录片,这是他坚持和不妥协的理由。

“每次开始拍一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内心里的感受就是站在一个万丈深渊的悬崖上面,脱光了衣服,然后全裸的这么跳下去,自由落体,把自己投向万丈深渊。”
在范立欣看来,只要坚信可以做到,一定会在落地摔得粉身碎骨之前,长出翅膀飞起来。不妥协,就是为范立欣护航的翅膀。

如何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是学识?智慧?还是经验?不,它们只能带给你更多选择。
圆梦的人身上都有自己的特质,正是这些让他们过上了向往的生活。
站在悬崖边,你敢不敢纵身一跃?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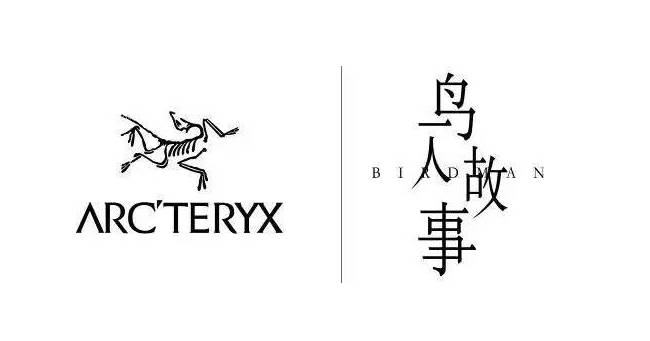
点击“阅读原文”分享自己的鸟人故事,即有机会成为下一位始祖鸟鸟人,前往法国霞慕尼始祖鸟高山学院进阶攀登技巧,更有机会拥有专属的鸟人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