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日晚8时,细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前的寿山石旁,同学们献上一朵朵黄白色的菊花,在这里缅怀
朱锐老师
。
 8月2日晚,学生自发缅怀朱锐。来源:封面新闻
8月2日晚,学生自发缅怀朱锐。来源:封面新闻
8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发布讣告,该院“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交叉平台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朱锐因病医治无效,于当日下午13时1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56岁。
这一天,距离教师节,只有四十天。
朱锐的好友评价,
病魔只是击垮了他的身体,却不曾击垮他的意志——就像那句话,“可以被摧毁,但不可以被打败”。
死亡,反而更凸显了他人格的力量。
 4月16日,授课中的朱锐。来源:封面新闻
4月16日,授课中的朱锐。来源:封面新闻

最后的“好消息”
今年春天,朱锐的《艺术与人脑》课吸引了许多外院及校外人士前来听课。
起因是他的学生胡可欣将他带病上课的内容分享到社交平台上:
第一堂课,朱锐便告知同学们,自己是一名癌症患者,正在化疗,每次需服用大量止痛片才能授课。
那天的课堂上,有医生打电话来,朱锐平静地回答,“你现在正打扰我上课呢!”
胡可欣说,这堂课带给她的切身震撼已超越传授知识的课堂,引她重新开始思考生命与思想的意义。
“如果我哪天倒在课堂上,大家不要为我悲伤,而要为我感到骄傲,我很自豪。因为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朱锐说。
4月16日下午,记者早早来到人民大学立德楼508室,朱锐的《艺术与人脑》于每周二晚6:00-7:30开课。
5时21分,已有二三十位学生聚集在门口,此时上一门课尚未结束。
正式开课时,能容纳60人的阶梯教室已座无虚席,不少人从旁边教室搬来椅子,有的直接席地而坐。
朱锐准时走进教室,穿着却有些不合时宜——四月中旬的北京,最高温26℃,他却戴着厚厚的帽子和手套。
胡可欣解释,戴手套是因为手上有治疗痕迹,担心学生看到不舒服。
上课时,朱锐带来的登山杖静静靠在讲台旁。
他的博士生赵海若说,“接受化疗的身体,疼痛深入骨髓,需要拄着拐杖走路。”
生病前,朱锐酷爱爬山和徒步,但那时的他身手敏捷,从未用过手杖。这支登山杖,是朱锐病重后,他的同事和挚友刘晓力老师送给他的。
“讲究穿搭、注重形象”,是朱锐同事与学生对他的共同评价。
患病前,朱锐留着“爆炸头”,戴圆框眼镜,艺术感十足。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官网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官网
胡可欣回忆,老师最开始做化疗时,不愿回校上课,只通过电话或线上会议联络,“他说脸上有化疗留下的斑,头发也掉了很多。”
去年秋季,朱锐教授上《西方哲学原典》课,戴了一整个学期的帽子,冬天进教室也不摘。
直到今年4月9日,朱锐在上后半堂课时把帽子摘了下来,他高兴地说,“我的头发已经长出来很多了。”
就在一周前,朱锐平静地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化疗停止了,终于可以好好上课了。这不是因为痊愈了,而是化疗已经不起效果了。
 7月13日,哲学院副教授刘畅和同事去医院探望朱锐。来源:封面新闻
7月13日,哲学院副教授刘畅和同事去医院探望朱锐。来源:封面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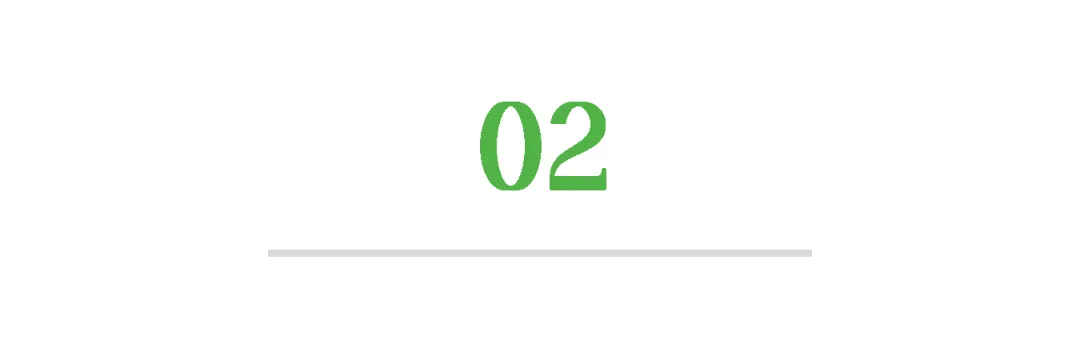
最后的毕业寄语
课上,瘦削的朱锐基本全程坐着,但依然声音洪亮。
他畅谈维特根斯坦与苏格拉底,分析人脑与艺术间的联结奥秘。谈及喜欢的画作——北宋画家郭熙的《秋山行旅图》时,更是流露出喜悦的神情,眼神熠熠生辉。
“我想这门课之所以受欢迎,一是本身的内容,二是朱老师的人格魅力——身体力行践行着他所喜爱的、自由而独立的思考。”
哲学院副教授刘畅说。
刘畅是朱锐的好友,两人因合开一门课而相识,后来经常聊天,约着一起吃饭和散步。
刘畅评价道,
朱锐不断尝试从新的角度进行启发性思考,不是人云亦云、照本宣科,而像是带着学生进行思维探索。
《艺术与人脑》这门课,是朱锐来之后新开的,主题是作为艺术与神经科学交叉领域的“神经美学”,“这门课也只有朱锐能讲”,刘畅告诉记者。
课堂上,朱锐会先讲45分钟到1小时,然后留出至少半小时进行提问、交流与讨论。
 生病前,朱锐在人民大学的课堂上
生病前,朱锐在人民大学的课堂上
(图片转自《哲学家朱锐的人生最后一课》
剥洋葱people
公众号)
“感受最深的,是朱老师永远在启发我们每一个人,鼓励大家勇敢发问与探索”,刘畅说,尽管他和朱锐在很多哲学的基本问题上,立场截然不同,但沟通交流后总会引发新的思考。
“朱老师上课最大的特点,是非常重视与学生互动”,胡可欣说,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我把大家看作和我平等的朋友和学者,所有人都可以在我的课上畅所欲言。”
令她印象最深的,是有关“恐惧”的内容。
朱锐在课堂上说,有很多恐惧实际不属于自己,而是外界所制造的,比如容貌焦虑等。艺术家则能让人注意到现象自身的质感,而非含义。
“追求艺术,本质上是追寻自由的感受,而不被其他恐惧所裹挟。”他说。
在2024年毕业典礼上,朱锐专门录制了一段视频。他鼓励大家追求自己想要的,把欲望和事物的真正价值相连接,从而缓解资源的稀缺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希望大家无论以后发现自己在哪里,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是在中心还是在边缘,是高还是低,是大还是小,是‘扶摇直上九万里,先图南后适南冥’,还是‘振飞不过数仞而落地,翱翔蓬蒿之间,尽显彼且奚适也’的风流或怡然自得,你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并且凭借你的善良、智慧和‘人大人’该有的坚韧不拔,使那片天空因为你而灿烂,因为你而闪烁。”
视频的最后,朱锐这样寄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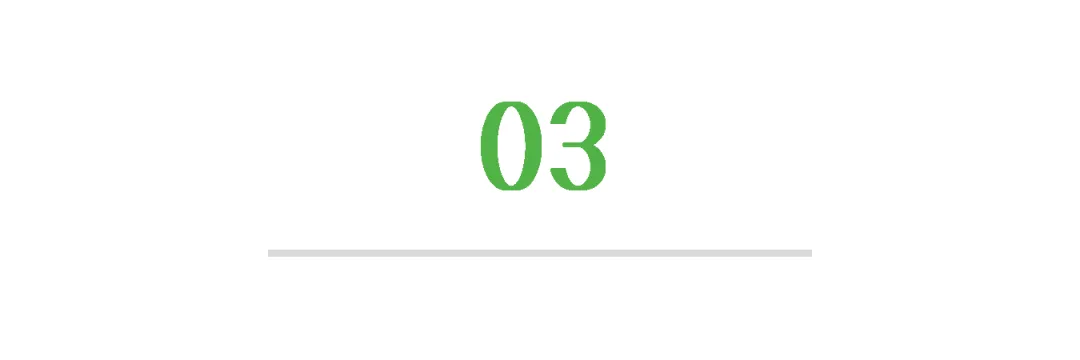
最后的一堂课
2022年8月底,朱锐确诊癌症,之后辗转治疗。
有时学生给他打电话聊学业问题,他说,“我们今天到这儿吧,护士催我过去做化疗了”,学生才知道他在医院里。
2023年秋季学期,朱锐重返校园,并主动承担起一学年的授课任务。
刘畅回忆,去年秋天,他和朱锐一同坐高铁赴武汉参加学术会议,他为朱锐拍下的照片,头发依然茂密,脸上是大大的笑容,神采奕奕。

去年秋天,同事刘畅在武汉大学为朱锐拍摄的照片。
来源:封面新闻
转折点发生在去年冬天。在经历新一轮放疗后,朱锐一下子变得憔悴,体力明显下降,头发几乎掉光。刘畅明显感觉到他上完课已经累到有些说不出话。
下课后,刘畅和朱锐的学生送他到校门口,目送他坐上提前叫好的车独自离开。
胡可欣也记得,去年冬天,有次她在下课后追出去想问几个问题,朱锐说,我们下次再约时间好不好,我现在浑身都很痛。
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表情没有变化,依然挂着跟上课时一样的开朗笑容。
朱锐很少对学生和同事提及病情和痛苦,甚至他的家人都是通过热搜才了解到。
此前,朱锐很自豪地提及过年回了趟家,连父母都不知道他的病情,因为“我表演得很好,每次都吃止痛片,所以没让他们看出丝毫异常”。
6月,朱锐上了最后一堂课。胡可欣回忆,他走路都很抖。课程结束后,朱锐悄悄说,可欣!你知道吗?我今天忘记吃止痛药了!
那时,胡可欣才明白,朱锐并非不会感到痛苦,只是不会表达给学生,他要把最好的面貌呈现出来,
“他更希望自己是以学者、师长的身份被认识、被记住,而不是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
。
 7月17日,学生探视病房里的朱锐。来源:封面新闻
7月17日,学生探视病房里的朱锐。来源:封面新闻

最后的一次探视
6月下旬,朱锐给学生发消息说腹水严重,医生判断只有个把月时间了,他希望在最后的时间见见大家。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出希望得到探视。此前,学生多次提出请求他都没答应。
7月12日,朱锐转入海淀医院的安宁病房。
第二天,刘畅和几位同事一同去探望,他形容朱锐“瘦得像个小婴儿,一丁点,只能缩在床上,但眼神依然坚定”。
他们带去一束鲜花,朱锐突然高举双手接过来,咧开嘴笑了。刘畅说,他就是要证明,“他可以!”
依然乐观的朱锐讲起自己的“双赢”理论:假如明天他走了,就结束了痛苦;假如明天没走,等于又赢得一天,所以他现在每过一天都很开心。
刘畅说,就像朱锐在课堂上讲“哲学家不惧怕死亡”,他真正做到了。病魔只是击垮了他的身体,却不曾击垮他的意志,死亡面前,反而更凸显了他人格的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刘畅由内而外地替朱锐感到开心:朱老师为我们证明了一点,哲学是值得托付的,是可以安身立命的,能够成为一种精神支撑。
“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刘畅认为,《老人与海》中的这句话是对朱锐最好的写照。
7月17日,朱锐的七名硕博生赶到医院,带来一个很大很软的靠枕,并挑选了一盆橙红色的蝴蝶兰,“因为看着温暖,而且能开很久”,胡可欣说。
在学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探视中,朱锐没有说很多关于学习的事,而是嘱托了很多人生道理,
“他希望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好,尤其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胡可欣说。
她明显感觉到,当时老师已经非常虚弱,但还是强打着精神,说了大概40分钟的话。她后来才知道,这也是老师最长的一
次访客接待——医生说他之前和别人见面只聊十分钟。
合照上,朱锐高高举起右手,比了个“耶”。

最后的告别
“整个人处于一种好像被突然扔进水里的感觉,喘不上来气,四肢漂浮在空中,又受到很大阻力,以至于很难随意地乱动。”胡可欣形容她听闻朱锐逝世的感受。
8月1日下午5时,她打开手机发现这个消息,几度退出重进,才确认事情的真实性,她在原地手足无措。
尽管已经提前两年开始做各种心理准备,但噩耗传来依然无法控制内心的波动,甚至一度处于情感隔离的状态——突然会掉眼泪,然后痛哭,几分钟之后又恢复正常。
当晚,她在朋友圈分享了柏拉图的诗:
“从前你是晨星在人世间发光,如今死后如晚星在逝者中显耀。”
8月2日下午,胡可欣登上从上海回北京的高铁,其他同门有的从福建飞回,有的从河北开车赶回……他们决定送老师最后一程。
同日,在《艺术与人脑》课程群中,一名昵称为“猫叔”的学子组织了一场自发的缅怀活动。
晚上8时,阴沉的天空飘起细雨。“猫叔”准备了两大束菊花,同学们来到人文楼前树立的寿山石旁,默哀、重温毕业寄语、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