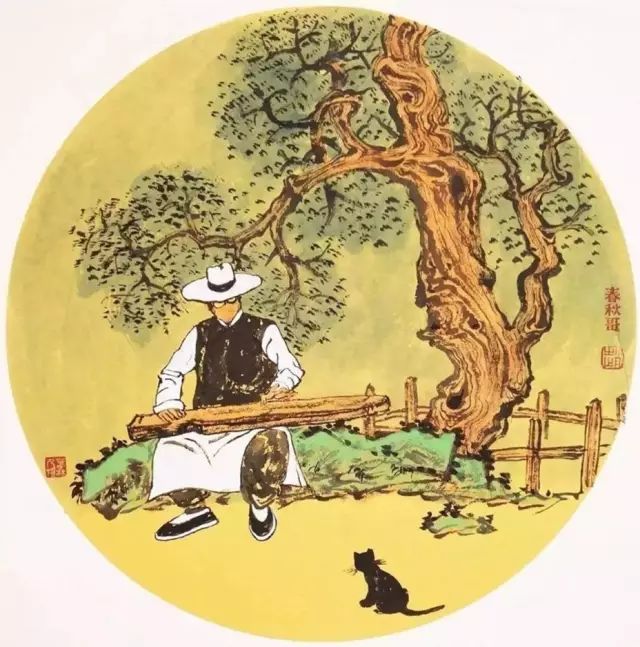夕阳下,一匹白色的骏马载着一位少年,奔腾在空旷的大漠之上,别激动,那不是我。
这是我小时候看的一部露天电影,记忆中精彩的一个画面。后来我用文字表达,总觉与画面不符,当读到曹植的《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我选择了放弃,曹植已经完美地诠释了这个画面,或许导演就是按照这句诗来拍摄的,我再写无异于画蛇添足。
当年崔灏游黄鹤楼,觉得它很适合入诗,回到家查阅各种资料,发现前人写的都很平常,那就让我题诗在上头吧!
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
李白写诗向来很自信,从没服过谁,当来到黄鹤楼,登高凭栏一望,畅然大笑,直接向媒体宣布:
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灏题诗在上头。
李白尚且有自知之明,我这个只读过“床前明月光”和“锄禾日当午”的人还敢与“七步成诗”的曹植叫板吗?
我从此认为,作诗就要像李白一样谦逊。
傍晚,夕阳就要落山了,西边的晚霞就像新娘身上的红色嫁衣,我还没有来得及揭去她的红盖头,就消失不见了。
多么令人惋惜,美好的画面总是留不住,我想用诗表达出来,李商隐突然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来,边走边唱着: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我羞涩了,不好意思下笔了,“李商隐题诗在上头”,我不能在大诗人面前班门弄斧啊。
记得有一天,我正在房间里读一本唐诗的书,天空中的乌云如墨般翻滚,大风吹透每一寸土地,行人匆匆,感觉十分压抑,呼吸都觉得困难,然后我诗性又起。
整理一下思绪,将要落笔的瞬间,一股风涌进来,吹落我手中的书本,俯身去拣时,李贺的一首诗跳了出来:
黑云压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鳞开。
事实证明,一个只活了二十六个春秋的诗人,只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不停的写诗,然后让我无诗可写。
读过的诗词越来越多,看过的风景越来越多,每一次想下笔时,似乎都能找到前人留下诗句。
当我读到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我觉得我和崔灏都被李白骗了,说好的“道不得”呢?我早就该相信,李白骨子里是没有谦逊的。
身边也会遇到这样的人,整天唠叨说:
“这个太难了,做不了”
“不要受虐了,不行的。”
然后你信了,过一段时间发现自己上当了。
我将怀疑转向了李商隐,不错,他是大诗人,撑起晚唐的一片天,夕阳天天有,黄昏人人写,他的未必就是最好的。
读过宋词我才发现,欧阳修对黄昏也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一曲《生查子》,为我们点亮一盏灯。
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
不仅如此,我还发现李贺的黑云,也没能笼罩千年,几十年后就被李浑的一阵风吹散了。
溪云初起日沉阁,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的疑惑开始像山雨一样涌来,只能自己去寻找答案。
二
我去过泰山,五岳之中唯一一座登顶的,多次想下笔写它,最终没有成功。
泰山是五岳之尊,往来登顶的游客叠加起来,不知比泰山高出多少。大大小小的诗人留下诗句可以汇成江河。
站在诗歌顶峰的是谁?毫无争议是吐口吐沫便成诗的李白。李白登上泰山时,荡气回肠:
天门一长啸,
万里清风来。
一位少年,风尘仆仆来到泰山,不管是谁题诗在上头,我来了就要登顶,留下我的诗句。他就是李白狂热的粉丝杜甫。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还有人比杜甫更爱泰山吗?明代王世贞来到泰山,一见倾心,非要和杜甫争一争:
天门倒泻银河水,
日观翻悬碧海流。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用小学生写作文的话来说:“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
我似乎受到了这种精神的鼓励。
我曾几次坐车跨越黄河,看到我们伟大的母亲河,她宽广、辽阔,给我作诗的冲动,内心真实的感动。
王之涣当年骑马来到黄河边,他像一个音乐指挥家,风在吼,马在叫,黄河跟着他的节奏,咆哮!咆哮!
他还自己谱曲,让黄河的名字更加响亮。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不够美,再谱一曲: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我说过,李白写诗从未服过谁,老王,你只不过比我早来了几年,没关系,我才是黄河的主唱。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黄河落天走东海,
万里写入胸怀间。
黄河西来决昆仑,
咆哮万里触龙门。
这样恢宏的气势,这样绝美的文字,后人还有得写吗?还敢再写吗?
王维收拾了几件衣服,跑到黄河边,面对着大漠落日,神情凝重,抽出宝剑在地上写下: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刘禹锡也不甘寂寞,换了身衣服,加入了黄河大合唱的队伍:
九曲黄河万里沙,
浪淘风簸自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