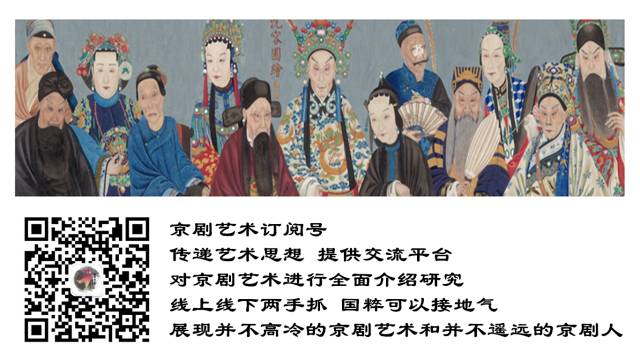↗
点击上方
“蓝字”
关注我们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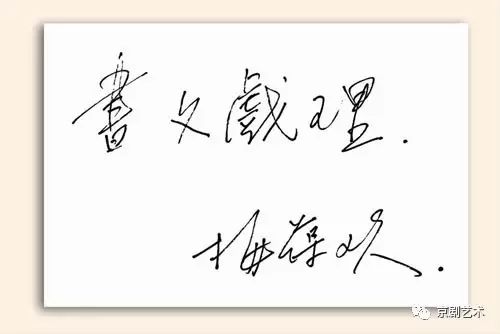
书文戏理(梅葆玖)
我学艺、为人全是在家庭中耳濡目染、向父亲梅兰芳学来的。
父亲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也接受革命,接受新中国,但总的来
说,旧礼教还是深深影响了他。父亲一直秉承一个道理,那就是书文戏理,他常说,很多老一辈
人大字不识一个,但都知道为人要忠、要孝、要义、要勇,从哪儿来的?听书、看戏得来的。
我小时候学戏,父亲要求我们不但要唱得好、演得好,更要知道这个戏讲的是个什么道理。
我们学每出戏,都会讲到礼义廉耻,好人一定是得好报,坏人一定不行;昏君一定要被灭,明君
一定能够长久,这就是书文戏理,在学戏演戏当中给自己处事为人立了一个标杆。
父亲把这些道理融入自己的为人中,他一生的行为就是我们的模范。
父亲有句话,移步不换形,是讲他的艺术主张的,艺术可以发展、创新,但核心和根魂不能
变。其实他做家长、做中国人也是这样。“我到哪儿心不能变,爱国不能变,对子女的教育不能
变,对同仁的爱护不能变”,他一辈子走的都是正人君子的道路,没有说梅兰芳就唱这几出戏,
唱完挣钱走人了,他时时都跟家人子女、跟同仁、跟国家的命运在一起。

我父亲很开明,对我影响也很大。我母亲说学戏就让他光学戏得了,父亲说光学戏,将来没
文化不行,该念法国学校就念法国学校,该念英国学校就念英国学校,要接受全方位的教育。除
了课堂上教的,他指定我学唐诗宋词、写书法,还让我看歌剧、看俄罗斯的芭蕾,听贝多芬、柴
可夫斯基、肖邦,一有音乐会他就带着我去听。父亲还让我学跳舞。我母亲说,可别让他学,明
儿把女孩子都招家里来了怎么管。父亲说不是那么回事,要是出国,一个国际大明星请你跳个舞,
你站不起来,那也麻烦了,所以什么探戈、伦巴,都得会,但这不是玩闹,要作为一种艺术去学。
我小时候在上海长大,那时候法租界、英租界还是半洋的社会,学校里讲民主,不像在北京
时见了祖师得磕头,我父亲说磕头是老一辈礼数,遵守也对,不过新风尚要是有道理,他也不排
斥。后来我们拜年的时候,父亲就说不用磕头了,给我鞠躬就完了。
我母亲可不行,她是旗人,规矩很多,吃饭不能跟大人一起,大人吃饭小孩得坐旁边,等大
人吃完了,你才能吃;吃菜只能挑眼前的,不能过河;大人说话小孩不许搭茬……都是些老规矩,
但我觉得这些也对,是长幼尊卑的礼仪。
我是梅家子女中最小的一个,没有离开过他们,一直在父母身边,他们的言教、身教对我影
响很深,我觉得自己能做多少事情就做多少事情,能传承多少学生就传承多少学生,不坑人、不
骗人、不害人,另外还有爱国,没有别的想法。
我个人对学生、对年轻人的教育也是这样。我常在政协会上说,现在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很好,但这个教育不是背口号,要从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出合适今天社会的来教育孩
子们。
父亲怎么教我的,我就怎么教学生。我要求自己的学生把每一出戏的历史查清楚,把人物的
性格琢磨明白,再演这个人物,就有人物了。演杨贵妃,就要念《长恨歌》;演洛神,就去读《洛
神赋》;演西施,就要把吴越历史看一遍。光唱得好、演得好,漂亮,是个空的、是个模型,不
能感人。
我也要求学生去了解我父亲一生的历史,学会做人。除了让他们反复观摩父亲的演出,我还
把父亲的传记、他写过的艺术感言都送给学生。我说梅兰芳的艺术不是唱几出《霸王别姬》《穆
桂英挂帅》,唱红了就是好角,那是应该的,但其他的,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人,做一个对国
家忠诚的人,这是脑袋里面经常要想的。不是说挣钱了就光琢磨吃喝玩乐,那你的艺术长不了,
自己把自己毁了。你看我的学生没有闹事儿的,没有化妆化得跟猴儿似的,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都是规规矩矩的,让人觉得很干净,很大方。学生们是从心里头遵守这些规矩,不是你压着我,
我就遵守,你一放开,我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我学戏的时候,父亲还在登台演出,那时候抗战刚胜利,父亲在台上唱,每天给我留个座位,
让我在台下看他的表演。他所有的角色都在我的脑袋里头,他没有坏戏,都是好的,都是美的,
都是与人为善的。日本人来了,他不唱戏,就戴起眼镜来画佛,画如来,画洛神,画杨贵妃,也
都是美和善。
我很幸福,我的父亲是梅兰芳,梅兰芳是那么一个爱家、爱民、爱国的人,他是一个正人君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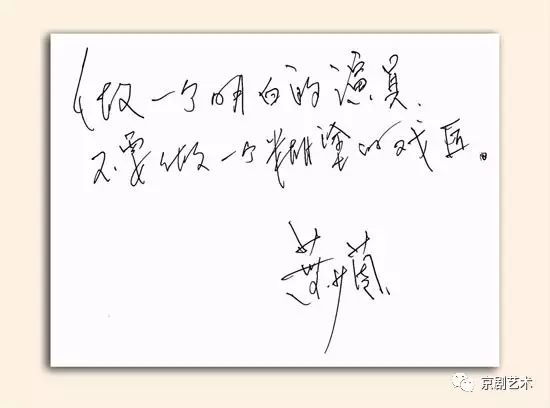
要做明白的演员不做糊涂的戏匠(叶少兰)
我自小学戏,父亲教育我们,要做明白的演员,不做糊涂的戏匠,这就是我们家的规矩。
“明白”的标准很广阔,不单单是明白技术、明白艺术、明白表演,还要明白怎么学艺、怎
么为人。
“明白”要肯吃苦。
京剧演员常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不是一个口号,不吃苦怎么可能成好角儿呢?我们
小时候,8、9岁学戏,无论春夏秋冬、三伏三九,早晨5点钟就要爬起来,到城墙根儿去,到旷野
荒郊去,喊嗓子,喊一个小时,6点钟回来练早功,7点钟吃早饭,开始正课,正课之前还有一遍
早功。一天正课结束,到了晚自习前还要练一遍私功。什么是私功呢?5点钟下正课了,我要回忆
一下,今天老师讲了什么,教了什么,会了没有。自己要找一个角落、找一个教室回忆一遍,练
一遍。我们小时候练功,没有现在的条件,院子里、城墙外,都是土地,最好的就是铺一块很破
的、人家不要的线毯,就在上边翻跌,练技巧,很苦。
今天的年轻人,有的不肯吃苦,我有些担忧。比如说,都说京剧是国粹,要好好传承,可每
次学校招生,报京剧的远远比不过报影视的。为什么?学京剧是要吃苦的,皮肉受苦,学八年还
不一定出得来,有了名气也不能放松,还得用功,唱念做打,都要去练。有人会觉得我唱一首歌
就可以红,上一个晚会就可以成名,拍一部影视剧就可以打开局面,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苦呢?当
然并不是所有歌唱、影视演员都不肯吃苦,但许多人是抱着早成名、早挣钱的态度来看待艺术的,
很多条件很好的苗子放弃学习京剧也是因为吃不了苦。
再看京剧业内,普遍存在着基本功不扎实的问题,也是吃苦不够。
拿一个小小的“走脚步”来举例吧。什么是走脚步?不同的行当、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穿戴、
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格都有不同的走法,都有比较程式化的规定,因为京剧是写意的、夸张的、
舞蹈化的,它把生活艺术化了,把生活提炼扩大了、夸张了,这才总结归纳出这么多种走脚步的
方法。比如同是小生,周瑜有一种走法,穿着蟒袍玉带,走得周正、潇洒;许仙,另一种走法。
许仙为什么穿薄底子呢,他是伙计,没有身份,也不是读书人,但他又是小生,是文小生,所以
他就是一种比较民间化的走法;还有一种穷生,那种怀才不遇、衣衫褴褛、肚中饥饿,很寒酸的
人,这又是一种走法。

我们小时候光走脚步就要走一二年,现在有些年轻演员不肯吃苦,没有下功夫练走脚步,周
瑜这么走,许仙这么走,穷生也这么走,全都这么走,那就没有了标准,还谈什么艺术质量,怎
么会好看?观众说不出你的脚步走得不对,他们只会觉得不像,不真实,不好看。
我父亲常说,文化不能凑合,艺术不能凑合,大概齐不行,艺术是有标准的。
“明白”要严格按照标准来。
说一个最起码的“勒头”,不同的行当有不同的勒法,但都是有标准的。
我们小时候学戏,不管是什么行,都要理发,特别是净行,一定要求剃光头。为什么要剃光
头?因为演员的盔头很沉,花脸为了体现角色特征,尽量要显得脸大,那么就要把脸谱勾到脑门
上面,所以花脸戴盔头就要戴到后脑勺,如果头发没剃干净,很滑,盔头就固定不好。演员在舞
台上不光是唱,还要表演,要有动作,盔头戴不稳,肯定影响演出,一滑就掉了。勒头是很苦的,
小拇指粗的绳子,里边还埋着一条铁条,一个男子汉要很用力地来勒。我们小时候学戏,光练勒
头就要几年功夫,为了舞台上的美,就得放弃一些生活上的美,舞台艺术是有标准的。
今天有的演员学得少、见得少,就不明白这些标准,或者知道标准,不按照做。那我们第一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标准,更要遵守标准。学艺要肯吃苦,要有牺牲精神,要没日没夜,要一门心
思,这是我小时候受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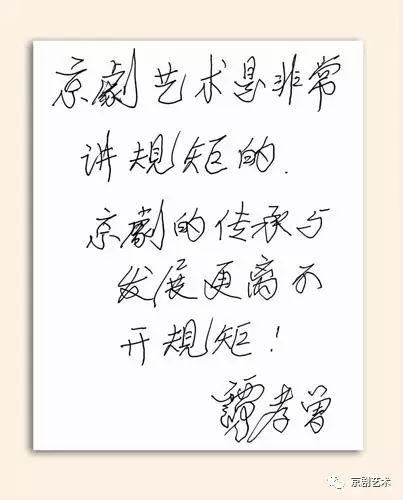
京剧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规矩(谭孝曾)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哪行哪业都有自己的规矩。京剧的规矩太多了,可是恰恰现在丢失了很
多,甚至有的干这行的都不知道这些规矩,这是一个遗憾。我认为,京剧传承除了学艺、修德以
外,还应该学规矩。
我1949年出生,老一辈艺术家如梅兰芳梅先生、马连良马先生、裘盛戎裘先生、我祖父谭富
英先生的演出我都见过。不说别的,就单说他们在后台怎么准备演出的、怎么化妆的,那种规矩、
那种认真严谨的态度,真是值得我们传承。现在提倡“工匠精神”,我觉得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工
匠精神。
化妆对京剧来说很重要,演员一出场,观众看的都是扮相。过去老话讲谭富英的扮相,一块
现大洋一张戏票,还没张嘴呢,一上场就值8毛,那个扮相就值8毛,你说他的扮相多漂亮!我父
亲常说,一个叫讲究,一个叫将就,你将就也能上,观众也能看,可是讲究和将就读起来差着一
个字,就差了很大的距离,这值8毛的扮相就是讲究来的。也有人给他们这种讲究叫“式子”,说
他们穷讲究事儿多,可我认为这种“式子”有道理。
先说到场,过去老戏班有一些很不好的现象,很多演员尤其是名演员爱赶场,这场唱完了急
急忙忙赶到下一场,还有的爱误场,好像晚一点到剧场是一种范儿,我是角儿!在我长辈身上,
这种情况绝对不可能发生,他们都是提前很早就到剧场了,在后台准备今天晚上上场要用的东西
——化妆的、穿戴的,虽然有跟包的做这些事,可是他们还要亲自过一下目,看看准备得怎么样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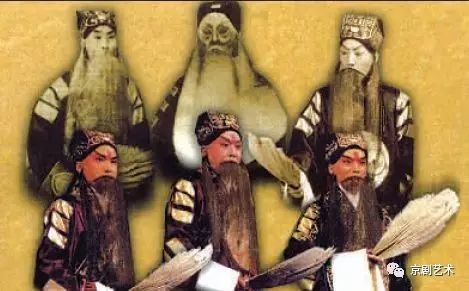
比如京剧演员穿的厚底靴,下边是白的厚底儿,上边是黑帮儿。每到后台,我父亲都要给它
重新刷一遍白,为什么?就为了漂亮,上台一站,厚底儿一定要白。可是恰恰刷这白厚底儿的时
候,容易把黑帮儿蹭上一点小白边,其实这很正常,也难免。那么我就多次看到父亲拿着毛巾来
回擦那道白边。其实这算什么呀,我父亲就不行,就得擦掉。衣服的水袖,上场前一定是在后台
熨得平平的,一定要白白净净的,这才踏实。
化妆就更甭说了,认真之极,且找补呢!化完以后,这儿再加点,那儿再加点,只要没说要
上台了,就一直在找补;穿服装也是,穿完以后,看着镜子,这儿再往上提溜点儿,那儿再往下
拽拽;最后勒头了,反复看那个月亮门,老想如何把这月亮门弄得更圆、更好看,且在那儿改呢,
就这个过程不知道要多少遍,一直到最后戴上盔头了,还在照镜子,所有的都要对称,两边的珠
子、袍子、绒球是不是对称,不能说这个珠子在这儿,这个珠子在那儿。好不容易都妥当了,真
要上台了,我父亲还随手带一面小方镜,让别人给拿着,已经走到台幕边了,迈着步就要上台了,
还要看一看,看自己哪儿还不到位,最后才登台。
守这些规矩也不是死守,自己还要多用心。还拿化妆来说,比如说演一个白胡子老头,胡子
白,脸色就不一定按跟别人一样的底色去抹,就要根据角色调整。再比如,青衣一般是用白粉定
妆,可有时候又擦点黄粉,为什么?擦点黄粉柔和,光白粉太刺眼了。现在有的年轻人化妆,总
觉得那么愣,用力过猛,就是因为自己没在这上面用心。还有勒头,武生要勒得高一点,老生稍
微低一点,小生又稍微低一点。这些都要自己用心体会,甚至可以有细小的改进。
这种点点滴滴细小的规矩和讲究,日积月累,天天做,场场做,在我的父辈艺术家们身上已
经成了一种习惯,正是有这么多规矩,有这么多讲究,在早些年代,虽然化妆条件很差,摄像水
平更低,可是老一辈的剧照,多漂亮,多精神!现在我们有了现代化的化妆设备,现代化的灯光,
现代化的摄像,但照出来却总觉得缺些什么,缺少的是规矩、是讲究。
我看现在有些年轻人演出,一到后台,有正戏、没正戏先聊大天,跟戏不着边,有时候马上
都快开戏了,还不急着化妆,这样即便没误场,化上了,那赶着化的,能好看得了吗?再有一些
配角不用心,化妆马马虎虎对付了事,一出戏,除了主演好,配演也得好,这台戏才好看。你光
一个主演好看,其他龙套都难看得跟掉了面儿似的,勒得也不好,那戏能好吗?
父亲常说,作为演员,自己不自律,不严谨,势必就自己把自己糟蹋了,把剧种糟蹋了,让
观众觉得这个团不行,觉得京剧不好看。
谭家几代人,都受到这样的教育和熏陶,我首先以身作则,也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和学生,
只有这样,在台上才能严谨,才能让人看出你跟别的演员不一样,让人感觉眼前一亮,而不是让
人说“还行、还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