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
青年电影手册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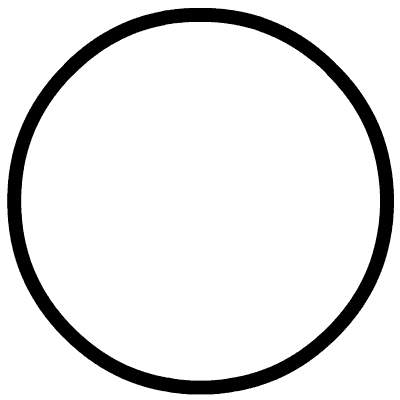
版权声明
5月31日推送文章:
1997年这部华语杰作首映。20年过去,它仍鲜活如昔
转自
奇遇电影(ID:cinematik)
,一向重视版权的小编昨天推送忘记注明出处,特此声明。
70周年的戛纳大庆也结束了,今年似乎一如即往,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了两部官方单元影片,一部出现在主竞赛,一部非竞赛单元,大家似乎已经见怪不怪,当然“请于佩尔做主演就能入围戛纳”的传言依然在海风中飘荡。无疑,关注戛纳电影节便没法避开伊莎贝尔·于佩尔女主人一样的身影,除开2009年担任了评委会主席,曾两度获得最佳女演员奖项之外,她几乎连续数年带着参演的新片来到戛纳,好像戛纳电影宫已是她的第二办公室,每年一次例行巡视,宣示主权,显然对她不是难事。
而在今年的例行巡视后,我们似乎已经可以和她约定下一次的相见是在何时何地——
接下来的六月,她将来到中国各大城市剧院诵读杜拉斯的《情人》
(广州、上海、北京三城具体活动时间,请查看本推送文末)
于佩尔第一次出现在杜拉斯的世界里也正是作家的处女作《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电影改编。柬埔寨籍的导演潘礼德将她直接带回了被杜拉斯的笔端无数次抚摸过的故土东南亚拍摄,在水稻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踏过。在这部杜拉斯自传性极强的作品中,于佩尔饰演的母亲角色也极大吻合着作家母亲的形象,苦涩强硬,冷酷矛盾……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母亲(伊莎贝尔·于佩尔饰)
当人们问起于佩尔要如何去诠释一个“杜拉斯式”的人物,她却否认到,“杜拉斯式”的人物应该是像《劳儿之劫》的劳尔·斯泰因,《印度之歌》的安娜-玛丽·斯特雷特, 应该是为一种纯粹为精神状态做注释的声音,这是一个几乎完全抽象的概念,而她的角色虽说也算虚构,却也摆脱不了杜拉斯母亲真实的形象,因此而带着更多的历史的宏大叙事性,混合着亲密与波澜壮阔。
然而这次十年前的相遇后,于佩尔便再未能出现在杜拉斯的作品中,也就从未真正以一位“杜拉斯式”的人物出现在大银幕或是舞台上。当然我们很难拒绝这位法国国宝演员的形象与杜拉斯世界的联姻,一位揽尽欧洲三大电影节影后,两度戛纳封后,奥斯卡提名在身,一位是属于这个星球的法国女作家,酒精中永远的文字女巫,小说崭新流派的先锋,电影、戏剧、政治多面登陆的旗手。
*《钢琴教师》
(La pianiste,2001)剧照
纵观于佩尔多年来那量大惊人的履历表,其形象的丰富多变也是令人咋舌,更遑论她以这颗星球上可能无人能及的广度和几大洲风格迥异的艺术家合作着。在如此宽广的覆盖范围中,于佩尔在镜头前与舞台上演过写色情文学的修女,弑父毒母的少女,杀死儿女的女巫,活过千百年由男性变为女性的神话奥兰多,以及一系列资产阶级妇女,被性侵的游戏公司老板,用刀划破下体的钢琴女教师,爱上管家的有钱寡妇……以至于人们将她的形象固化为“一位以塑造资产阶级的堕落和痛苦而闻名的女演员”。
*《编织的女孩》
(La dentellière,1977)剧照
法国著名导演帕特里斯·夏侯这样说起过她,“亲切又有距离,聪明,冷淡,炽烈,时刻准备出演一切。为他人献出自己同时又能做到缺席于此,又孤独又多面。当然很多女演员都可以这样,但伊莎贝尔身上有一种似乎已被她所接受的致命渴求,悲剧吗?也许吧,命中注定的渴求。但她就在那里,像我们一直认识的一样,随时准备冒险,无所畏惧,带着自己顽强的劲头在别人的精神中出现。一次又一次。”在她的大多数角色中都有对苦痛的一番极致的表达,或静默再爆发,或冰冷决绝,或尖刻讽刺,在她的角色中绝少有“天使爱美丽”,比起这些她总在灵魂的角落和残渣里寻找人性。这些角色游走在疯狂的边缘,从《钢琴教师》到《维奥莱特·诺齐埃尔》,从《编织的女孩》到《阿马利亚别墅》,更有戏剧舞台上的《美狄亚》《欲望号街车》《女仆》……因为爱得无望的疯狂,因为渴求太过而带来的疯狂,因为失爱迷惘而遁入疯狂……于佩尔在接受过太多媒体问题后,也学会了自嘲,“不演戏的话,我大概是最适合住在疯人院的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而当从杜拉斯的笔下而来,这样的疯狂也是如此顽强地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们的精神里。她疯也似的写了一生,每天坚持写,涉足多界,传奇一生,也只愿说,“我是作家。其他的都尽可忘掉”。她写了那么多,却也有人说她写的这一辈子都是《情人》的变奏、复调、再生、转世。她的故事里充满热带的潮气,风暴,酒,人被压抑至疯狂边缘的不安,突如其来的爱情,不对等的感情,对话,沉默……她童年的影调。这些疯狂来自一个不断被压缩,张力不断扩大的爆炸中心,原子弹与爱,逃离与被抛弃,虐待与渴望,死亡与肉欲,这些都被糅合到了一起。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杜拉斯曾被问起在越南哪里可以找到她童年时代景象,她说没有必要。为她作传的劳拉·阿德莱尔写道,“我知道。
这就是玛格丽特:一切无处不在。没有必要去当地找寻,加尔各答、西贡、永隆、砂砾,所有这些名字都在记忆中涡旋。
”写作之于杜拉斯,是对自己记忆的祭奠,对意识旋涡中每个关节点之间的暗自连结的探寻,是自我揭示之举,也是修复自身的疗愈,一切都可回溯至童年,热带绵长的风里无休无止的童年。
她把真实和虚构的边界逐渐模糊,人生和创作都是如此,在她的世界里,现实和幻想在酒精的调和下创制着独一片的天地,写的是自己的生活,活的是自己的写作。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有的艺术创作将创作者带离囿于其身的小天地,如莎士比亚从未离开过英格兰岛却可以从《威尼斯的商人》写到丹麦的《哈姆雷特》,有的艺术创作将被放逐的创作者再带回他们的乐园,他们再次采摘童年的果实以解在现实世界里无望的干渴,他们的艺术让他们得以贴近自身,以此存活,在一遍一遍的自我印证中生长、扩张。
无休无止的童年不止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当年已初入影坛的于佩尔仍然还不太清楚演戏究竟为何物,她在探寻着什么,然而又并不那么明了究竟想要什么。戈达尔看到了她,请她出演了影片《人人为己》,“一个滞留于少年时代的女人。”他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