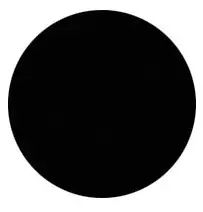“言己”的创办是在2015年3月,两年以前。那时我大二,之前从未了解过非虚构写作的含义,还带着以前在“教育科技”组常常拖稿的沮丧。
与非虚构写作相遇,和范雨素的文章给我的感觉一样,是一个深冬早春的大晴天。那天丽娟姐给我打电话,而我在百讲广场上逡巡,通话中,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做,也值得由北青最先好好做。栏目的名字则被定为“言己”——恰好是“记(記)”的两个部分,表示“讲述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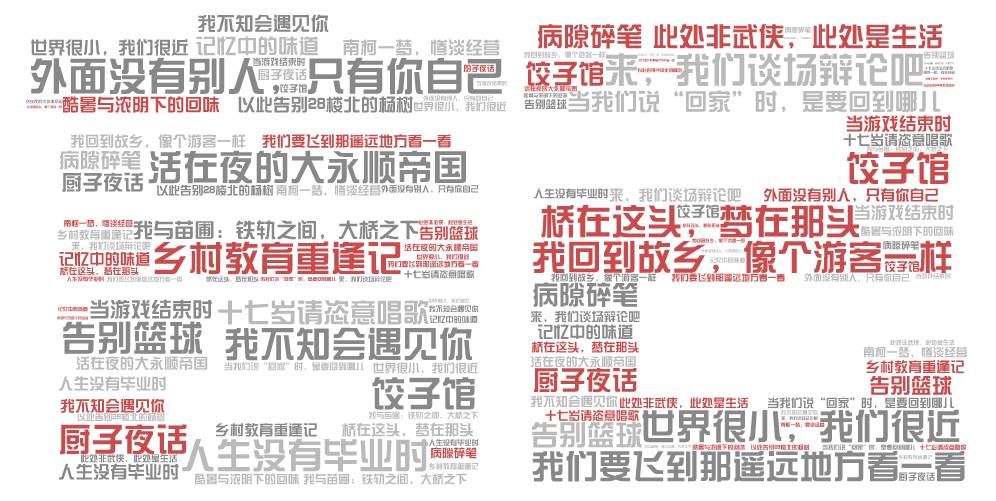
最开始,“言己”栏目在《北大青年》算是一个异类。它不是“调查”那样,拿出一把匕首指正时事,也不是“光阴”那样,浓缩厚重岁月于一碗浓汤,而是搬个小板凳捏把瓜子,给你讲个故事。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言己”在摸索中形成了几条写作路径,如今看来颇有意味。
一类是对于校园热点的关注,比如写毕业季的《人生没有毕业时》。那个时候我们的编辑大部分是大一大二,觉得本科毕业遥不可及,但是自己又非常好奇。我们间接联系到了张一甲学姐,死乞白赖地邀到了文章。文章里写到了几位她所认识的年纪稍长而依然活力十足的人,用以说明毕业相比于人生,只是一个微小的仪式而已。我发现,做媒体的人真是不一样,比如,张一甲学姐会询问在哪天推送,几点推送,在细节方面都特别仔细。
另一类是写个人的兴趣爱好。这种文章写出来很生动,因为那是作者熟悉而且热爱的生活。他们写暑期骑行,写电子游戏,写武术,写钢笔,写做饭。我们做编辑的,透过一篇文章遇到一个有趣的灵魂,也觉得很有趣。
我一直比较认同“人无癖不可与之交”,深深受惠于大学里社团为我打开的一个又一个世界的大门,也写过一篇有关昆曲的文章,叫《我不知会遇见你》。我的感受就像很多作者后来与我谈到的那样,记录一件自己很爱的事,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交代。
还有一类是北大的同学们不由自主地在共同写作的:故乡、故人、故事。这一题材的文章,从题目就能知道写的是哪种感情了。比如《桥在这头,梦在那头》写福建,《世界很小,我们很近》写甘肃,《我回到故乡,像个游客一样》写上海……文章很多,恕不一一列举了。
文章中的感情是很相似的,只是空间不同,你怀念你的那座小桥,我珍爱我的那个小岛。奇妙的是,隔不了多久,就又有这样写的文章,我们拿过来再看,还是感动——怎么就这么丧、这么老气横秋了呢?
我想,或许是因为文学尚未好好书写的我们这代人的时代。我们看起来那么年轻,还得一往无前鹏程万里呢,怎么能这就开始怀旧?
前辈们说,那是“青春里明媚的忧伤”罢了。
其实不是。
我们心里的,就是秋天的怀念、冬天的怀念、春天的怀念、夏天的怀念,很深很深的那种。看来,上一代不仅不相信下一代和他们有不同之处,而且不相信下一代竟然和他们有相同之处。没人懂,没人写,我们就自己写。写下来的文字绕过怀疑和冷漠,直接去呼应“孤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写出来才能使人确信,深沉的感情,岁数不够大的人也可以懂。
后来我交换的时候,离家千里,这种感情格外强烈,我也写了一篇关于故乡故人故事的,叫《床前明月光》。但是这篇文章让我彻底意识到写作和做编辑完全是两码事。这篇文章激起的我生活中的波澜,太让我感到意外了。
简单地说,这篇文章非常间接和偶然地引发了一段未尽的往事,哪知留下的又是令人怅惘的续篇。或许,我可以再把上一段故事引发的下一段故事写下去?但是我有点担心这样做是不是捉弄了命运,所以不继续写。
我严重怀疑,是不是写作这一职业天然地能为写作者带来更多生活上的奇遇?非虚构的书写仿佛具有某种勾魂的力量,往事已经过去,然而它存在于共同经历过的人们的心里,轻轻的召唤就能提起。

2015年4月1日,《北大青年》推送了第一篇言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