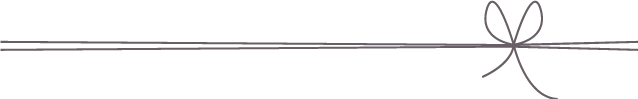走到任何地方,贩卖食物的路边摊都是一道微光。
它们是一个城市公开的秘密,是你永远可以期待的邂逅,是朴实的人们不断微笑后日积月累形成的皱纹,也是汗流浃背的皮肤间隙所同时流露出来的粗糙和活力。
《孤独星球》旅行书系列曾经出版过一本名叫《街头食物》的食谱,来向世界各地的路边摊致敬:“如果你想找到某一地美食的本心本源,那就必须去探索那个地方的路边摊。很多时候,关于食物的文化就深藏不露于那些卖墨西哥卷饼的小车中,那些热气腾腾的面条摊里,那些跳动的炭火和嘈杂的人声中。”
我依然能深深记得那些趣味盎然的路边摊故事。
小时候深夜归家,特别害怕那些伸手不见五指的巷弄口,在那个24小时便利店还未出现的年代里,你所能指望的,可能也就是离家较近的某个烘山芋摊或是茶叶蛋摊,一盏黄亮的灯,几缕看似温暖的白烟。
明明知道家已经近了,仍然要上前去买点什么,光顾一下,其意义也许并没有上升到这路边摊能作为一种安全感的象征,让你心生感激涕零,但小孩子的心里却实实在在地打算着:阿伯,我可是天天照顾你烘山芋生意的,最后到家的50米要是忽然跳出坏人,看在我们都这么熟了的份儿上,你也会拼了命地来救我吧。
又有成年后,深夜唱完K,去吃路边的柴爿馄饨。几个人挤坐在冷风袭袭的馄饨摊的长条板凳上,端着一碗汤烫肉鲜的小馄饨,这时有个一直背着双肩包不离身的朋友忽然放下包包,拉开拉链,从里面抽出一瓶红酒和一把开瓶器来。
一时间我们齐齐骂他做作,却也用一次性纸杯把这瓶酒大大咧咧地喝到很开心。
同样的情况我后来也遇过一次,在广州的某个烧烤摊上,两个正在啃烤鸡爪的女孩忽然变出一瓶酒,傻笑之余忽然惊觉到了什么,随即嘻嘻哈哈故作镇静地问烧烤摊主有没有开瓶器。
面无表情的摊主大叔先是冷冷回答:“开瓶器我有,那你们有开瓶费吗?”话音未落,他已经在两个女孩的桌上丢下一个开瓶器:“骗你们的啦,像你们这种乱讲究又小气的人哪。”
据说能一起去路边摊吃东西的人,必是亲密无间有着不寻常关系的死党。
这也是为什么初相见的男女大都会选在带点冷感的高级餐馆进行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话的原因,只有感情进阶到如火如荼了,才会无所顾忌地在深夜跑来吃热火朝天的路边摊。
在日本有个说法,在深夜居酒屋一起出现的一对非婚男女,那必是有着暧昧关系的,但如果是在深夜“屋台”(日文中路边摊的意思)一起吃拉面喝啤酒的一对非婚男女,就要比前者更进一步了。
就算是暧昧或不伦,那也是到了破罐子破摔、公开了也不怕非议的“真爱”境界。
这说法虽有点戏谑,有点武断,却也一语道出了在路边摊吃东西的那种带点禁忌的温暖感。毕竟,食物的路边摊本身就是带有争议的东西,真心爱吃的人会为它拍手叫好,真心爱你的人却会反复提醒你:“真的没有卫生问题吗?”
我对路边摊的爱恨纠结跟所有人的经历一样,始于父母的“一定不许乱吃路边不干净的东西”和小姨、姨夫的“趁你爸妈不注意我们就带你去吃”。
童年的各种叛逆和冒险中就包括了等夜深人静时自己穿好毛衣外套,悄悄溜出房间,蹑手蹑脚经过父母的卧室,跑到门口跟小姨和姨夫会合去吃路边摊烧烤的经历:黑夜里明晃晃的炭火、加多了孜然和辣椒粉,辣得让我咳嗽的烤肉串、偷喝的啤酒和第二天白天心照不宣的坏笑。
但到了今天,也轮到我接受考验了,出门旅行的时候,女儿和先生总喜欢背着我一起去吃路边摊:“就在这里吃碗炒面,我们不要告诉妈妈好不好?我实在不想吃她订的那家餐馆。”
路边摊食物的魅力,除了来自那些调皮而随意的食物之外,更多来自摊主的个性。
从某种角度来说,食物路边摊摊主的工作跟街头艺人的表演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一己的绝活、年复一年的坚持、行为艺术一般的现场制作、少数人的捧场以及绝对的分享。
但在当下的世界,这样的工作方式显然太过“个人”了,无论有多少人仍心心念念着关于路边摊的味觉大冒险,这依旧是个孤独的、被质疑的,且正在慢慢消失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