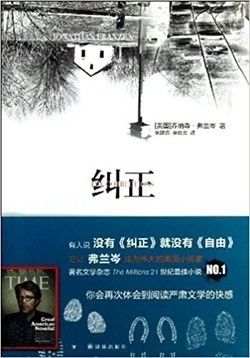
《纠正》 译林出版社
点击下方链接可阅读前文
众家言说|乔纳森•弗兰岑【美国】:论自传体小说(上)
我想用余下的篇幅来谈谈如何才能成为能够写出你需要写的那本书的那个人。我意识到,用我自己的作品和我自己从失败走向成功的经历来说事,我是冒着看上去在自我吹捧或过度自恋的嫌疑来谈论这个话题的。这并不是说作家为他自己最棒的作品感到自豪和花许多时间去审度他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奇怪或不对的。但是难道他非得在大庭广众之中去谈论吗?长期以来,我会对此问做否定回答,可现在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也许很有可能招来某些对我人格的非议。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在这里要谈一谈《纠正》,讲述我变成这本书的作者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一些艰难险阻。我要预先指出,这些艰难险阻大多在于——我认为对浸淫于小说这个难题之中的作家们来说将总是如此——要去克服羞耻感、愧疚感和忧郁感。我还要指出,我做如下演讲时我会感受到新一轮的羞耻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当时的头等大事是要解除婚约。要去破除忠贞不渝的誓言和情感纽带对谁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我娶的又是位作家就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了。我当初只是隐约意识到,要海誓山盟做结发夫妻,我俩年纪还太轻、经验尚不足,但我对文学的抱负和对爱情的理想占了上风。我们是一九八二年秋天结的婚,当时我刚满二十三岁,我俩决计作为两人团队去协力创作文学杰作。我们计划要并肩合作一辈子。当时看来好像没有必要去准备一个后备计划,因为我太太是个天赋高、见识广的纽约人,看上去她是注定会成功的,大概远在我之前,而我知道我总是能照顾我自己的。因此我俩就这么开始写起小说来了,当我太太写的小说没能找到买主时,我俩都感到很惊讶和失望。当我写的长篇小说于一九八七年秋天找到了出版社时,我是既感到高兴又觉得非常非常内疚。
自打那以后我俩在一起无事可做,就开始各奔东西,跨越两个大陆周游多处城镇。不知怎地在周游期间我还设法创作并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面对我自己已小有成就而我太太还在挣扎写她的第二部小说的事实,我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这个世道的不公正和不公平。我俩毕竟是一个团队的——是我们一起去应对这个世道——我作为丈夫的职责就是得相信支持我的太太。我因此对我自己的成就并不感到高兴,而是对这个世道充满了愤怒和不满之情。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强震》就是试图表达我们俩生活在这个令人失望的世道里的感受。回顾过去,尽管我依然为那部小说自豪,我现在能够看出其结局是如何被我对婚姻一厢情愿的想法(被我的忠贞不渝)所扭曲的。可我太太她自己并不这么认为,那就让我更加内疚了。令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回她声称,我从她灵魂里偷了点什么写就了那部小说。她还问过我,这个问题还算公道,为什么我笔下的女主人公老是被一枪毙命或是受了重伤。
一九九三年是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一年。我父亲病危,我太太和我钱财殆尽,而且我们俩变得越来越抑郁了。希望飞快致富,我就写了个电影剧本,讲的是一对年轻夫妇,非常像我们俩,开始一起入室行窃,几近与他人有外遇,但最终幸福地欢聚在永恒爱情的喜悦之中。此时,就连我都能看得出来我的作品被我对婚姻的忠诚扭曲了。但这并没有妨碍我筹划一部新小说《纠正》,讲的是一个像我一样的中西部年轻人替他太太受过、因谋杀罪被判二十年监禁的故事。
幸运的是,在我太太和我自己最终要去自杀或谋杀别人之前,现实出面干预了。这个现实是以几种形式出面的。一是我们不可否认地无法忍受再生活在一起了。二是我终于在婚姻以外结交了几位文学挚友。三是,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我们迫切需要钱。既然好莱坞对充斥着个人问题的剧本(而且跟《新抢钱夫妻》①有致命的雷同之处)看上去不感兴趣,我被迫干起了记者的活儿,而不久《纽约时报》就派我就美国小说的严峻形势去写一篇杂志长文。为写这篇报道去做调研期间,我结识了包括唐·德里罗在内的几位为我尊崇的老作家,并开始认识到自己不只属于我和我太太的两人团队,同时也属于一个规模更大、依然生机勃勃的作者和读者社群。我发现,非常关键的是,我对这个社群也负有责任、也得尽忠。
一旦加在我婚姻上的那个密不透风的封条以这些形式被破除了之后,事情很快就了结了。一九九四年底,在纽约我们俩分居在各自的公寓里,终于过上了我们二十出头时大概就本该去过的单身生活。这本该是个让人开心、令人解脱的事,但我仍旧觉得噩梦般的愧疚。竭尽忠诚,尤其是对家庭尽忠,于我来说是个基础性的价值观念。终身不渝的忠贞一直让我生活富有意义。我猜测,比较少为这种尽忠观念拖累的人,做起小说家来会比较轻松一些;但所有严肃文学作家都会在他们生命的某个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为做人处世和做好艺术之间的矛盾而纠结。只要我结婚有家,我写小说时,就会在技术层面上保持反自传文体(我的头两部小说就没有任何一个情节是从我实际生活里来的)、以围绕心智和社会问题去设计情节,来努力规避这种纠结。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我又回过头来继续创作《纠正》时,我仍在按照一个过于复杂的荒谬情节设计去写,那还是我安分守己地在我尽忠观念的框架内搞出来的构思。我有好多理由想去写一部宏大的社会小说,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我希望自己全知全能、人情世故无所不通,以此来逃避我个人生活的一塌糊涂。我继续尝试了一两年去写那部宏大的社会小说,但最终事情变得很明显,笔下一页页的文字越来越难以抵赖地显得虚伪荒谬,看来我非得变成一个不同的作者才能写出另一部小说。换句话说,我非得变成不同的人格才行。
首先要去掉的就是小说的主人公,一个三十五岁左右名叫安迪·阿勃伦特的男子。自打一开始构思起,他就是个主要角色,我想象他因他太太的谋杀罪替她受过蹲监狱,随后他又经历了无数次蜕变,最后变成了一个为美国联邦政府调查股票内幕交易案子的律师。我先是以第三人称去写他,然后又费尽心力用第一人称去写,结果完全失败。一路写来,我不时跟安迪·阿勃伦特请了长假撇下他不写,而惬意地去写另外两个角色伊妮德和艾尔弗雷德·兰伯特,这两位看上去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跟我父母也说不上不相像。讲述这两位的篇章在我笔下飞快地喷涌而出——跟绞尽脑汁去写安迪·阿勃伦特相比——毫不费力。因为安迪不是兰伯特夫妇的儿子,由于复杂的情节构思他也不可能是他们的儿子,我因而得去设计更加繁复的情节,试着把他的故事跟兰伯特夫妇联系起来。
虽然安迪不属于这本书现在看来很明显,可在当时根本就看不出来。在经历了我婚姻里非常糟糕的那几年之后,我对忧郁感和愧疚感的了解已经非常详尽和透彻,而安迪·阿勃伦特这个人物正是由他的忧郁感和愧疚感(尤其是在涉及女性的问题上,尤其是在涉及女性生物钟节律的问题上)来勾画的,所以如果我不利用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知识把他留在这本书内,在当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仅剩的毛病是——正如我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小说笔记里记下的——我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幽默感。他这人既讨人厌又不自在,既冷漠又令人沮丧。有七个月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拼命要写出几页还能让我自己满意的安迪故事。随后,有两个月时间,我又在笔记里辗转纠结是否把他给去掉。那些月份里究竟我作何想何感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就像我流感过后对病痛的记忆一样。我只知道最终让我下了决心把他去掉的理由是:一、我精疲力竭了,二、我自己已不再忧郁了,三、我对我太太抱有的愧疚感忽然减缓了。我依然怀有许多内疚,但我已和她足够疏远而能认清不是凡事都是我的错。再加上我那时刚爱上了一个年纪稍长于我的女人,尽管听上去有点荒唐,这让我觉得没给年近四十岁的太太生养孩子的机会这件事显得没那么恶劣了。我的新友从加州来纽约在我这儿待了一个星期,在那个极为幸福的一周行将结束的时候,我已准备承认安迪·阿勃伦特在这本书里无容身之地了。我在笔记本里给他画了个墓碑并借用《浮士德·悲剧第二部》里的那句“我们会救赎他的”
②
给他作墓志铭。老实说我想当初引用“我们会救赎他的”这句话时并没意识到其内涵。不过现在就都讲得通了。
去掉了安迪,我就只剩下兰伯特夫妇和他们三个已成年的孩子了,先前他们一直在这部小说的边缘地带出没徘徊。为让故事能写得下去而对稿子做的那几番删减和缩写,我将跳过不讲了,只讲一下为了变成能写出这部小说的那个人,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非得去克服的另外两个障碍。
第一个障碍就是羞耻感。我三十五岁左右的时候,对前十五年内我个人生活里做过的几乎所有事情都感到羞愧。我为结婚过早而羞愧,为我的内疚感而羞愧,为离婚以前那些年里我经历的那一番道德扭曲而羞愧,为我性生活经验不足而羞愧,为我长期与外界隔离而羞愧,为我有一个令人无法容忍、动辄妄下断言的母亲而羞愧,为我自己是个老受伤害、不知设防的人以及没能像德里罗或品钦那样以清高、自若、才华而高于他人之上而羞愧,为我在写一部看上去是想探究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中西部母亲能否让全家团圆最后共度一次圣诞的书而羞愧。我原本想要写一部涉及当今重大时务的小说——结果却像约瑟夫·K那样心焦抓狂,他自己忙于打官司,而他的同事们都忙着往上爬,——我则深陷于我的纯真给我带来的羞耻感。
这种羞耻感大多都集中体现在奇普·兰伯特这个人物身上了。我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想要把他的故事搞顺当,到那一年结束时我手头有大约三十页还算能用的文字。我婚姻行将结束前有一小段时间里,我跟我教课时认识的一位年轻女子有过一段短暂恋情。她不是学生,也从来没听过我的课,而且要比奇普·兰伯特的女友更加温柔、更有耐心。但那是非常尴尬、不尽人意的一段情,我现在一想起来就会深感羞愧坐立不安,出于某种原因似乎有必要将其纳入到奇普的故事里去。问题是,每次我试图把他放到类似于我自己的处境里去写,他都会变得令我极其反感。为了把他的处境写得合理易懂,我一直试图给他编织一个跟我自己有些相似的背景故事,可我又禁不住痛恨我自己的纯真。当我试图让奇普变得不那么天真、更加世故、性生活更有经验时,故事读起来似乎就不够诚实而且无趣。我是被安迪·阿勃伦特的幽灵搞得心神不定,也被伊恩·麦克尤恩早先写的两部小说《无辜者》和《陌生人的慰籍》长期所困扰,这两本书让我恶心到了看完就得去冲个热水澡的地步。这些是我不想去写又好像禁不住会去写的那些东西的样板。每次我屏气凝神数日写出一叠有关奇普的文字,到头来总是让我想去冲热水澡。那些文字开始还算风趣,很快就退化为对内心愧疚的告白了。似乎根本就没有办法把我自己稀奇古怪的经历转化为更为泛化的、颇为宽容的、饶有娱乐性的故事。
我拼命在写奇普·兰伯特的那一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旁人对我说过的两句话。第一句是我母亲说的,当时我们已经知道她的日子不多了,那是我最后一次陪她的那个下午她对我说的话。当时《纽约客》周刊发表了《纠正》的一个片段,尽管我母亲——非常值得钦佩地——执意在她临终时日里不去读它,我决定向她坦白某些我一直没告诉过她的事情。那些并不是什么很阴暗得见不得人的事情——只不过是我想要向她解释,我为何没有按照她为我设想好了的方式去走我的人生路。我想要让她放心,尽管我的生活在她看来有些奇怪,她身后我还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就像《纽约客》刊载的那一段故事里那样,最触动她心绪的是听到我告诉她,我老在夜间从我卧室窗户爬出去,还有我一向就很自信能成为作家,即使在我假装不想的时候也是如此。到了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她明确地让我知道,她一直在听、都听进去了。她点点头,用一种含糊概括的口吻说:“唔,你是个怪人。”这话部分地算是她尽了最大努力认可并原谅了我的人生选择。不过这句话以其含糊概括的口吻——几乎带有轻蔑的口气——主要是她以她自己的方式告诉我,我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对她终于无所谓了。我的人生对我比对她更重要。眼下对她最重要的是她自己行将结束的生命。这是她最终给予我的礼物之一:一个不言明的教诲,让我不要太在乎她或任何其他人会怎么看我。我就该去做我自己,就像她临终时在做她自己那样。
另一个非常有用的意见是数月过后我的朋友大卫·明斯
③
讲的,当时我在跟他抱怨奇普·兰伯特性生活阅历的问题实在让我抓狂。大卫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最有见地的意见往往也是最晦涩、最诡秘的。针对羞耻感这个话题,他对我说:“你不能照直用直笔去写羞耻感,你得旁敲侧击去写才行。”我至今仍是无法给你解释清楚他用“照直”和“旁侧”这一对介词所表达的本意,但这话立马就让我清楚地意识到,伊恩·麦克尤恩早先的那两部小说就是照直用直笔去写羞耻感的例子,而对奇普·兰伯特这个人物我该做的是,摸索出某种把羞耻感纳入故事之内、但又不会被其覆灭的写法:也就是要找到某种写法、把羞耻感作为一个客体与其余的东西隔离开来,最好是把羞耻感当作一个喜剧对象来写,而不是任由它渗透并败坏每个句子。从这一点出发就不难去想象,奇普·兰伯特跟他学生调情时嗑的药,其主要功效是解除了他的羞耻感。我一旦得了这个主意,最终能对羞耻感报以戏谑的态度之后,我只花了几周时间就写完了涉及奇普的章节,一年内就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其余内容。
那一年剩下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我的尽忠观念。写有关加里·兰伯特的那一章时这个问题尤其显著,加里这个角色表面上跟我大哥有某些相似之处。比如,加里有个把他喜爱的家庭相片汇集成册的计划:我大哥也有一个类似的项目。由于我大哥是我们家里最敏感最感情用事的一位,我无法想象采用了他的生活细节而又能不得罪于他,还能保持我俩的良好关系。我担心他会因此发脾气,我对我拿了对他来说并不可笑的真实细节来开玩笑感到愧疚,我对我到大庭广众之中去讲家庭私事感到有不守信义之嫌,我对自己为了专业上的一己之私而去搬用一位非作家的私生活细节而从道德上感到种种不光彩。这些都是我过去一直拒绝写“自传体”小说的理由。可那些生活细节又太富有意义,不用的话可惜,而且我又不是特意不让家里人知道我身为作家在仔细聆听他们所说的一切。我因此踌躇良久,最后去跟我一位年长明智的朋友探讨此事。出乎我的意料,她对我动了气,斥责了我的自恋情结。她的话跟我母亲和我共度最后那个下午时说过的意思类似。她说:“难道你以为你大哥过日子都是以你为中心绕着你转的吗?难道你还没意识到他是个成年人、有他自己的生活、生活里有的是比你重要得多的事情要去忙乎吗?难道你以为你有多厉害,在一部小说里写了点东西就能伤害到他吗?”
所有种类的忠诚,不管是书面上的还是其他地方的,只有在受到考验的时候才有意义。要忠诚于当作家的自己,最难的是在你刚起步的时候——在你当作家还没有领受到足够多的社会收益来证实你忠于职守是值得的时候。跟你朋友和家人保持良好关系的益处是不言而喻和具体确凿的;把这些写到书里去是否会有好处,多半就只能揣测而已。不过,终会到了某个时刻,这两种收益开始持平了。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了:为了继续变成那个我必须成为的作家,我是否甘冒跟我所爱的人疏远的风险?长期以来,我结婚成家期间,我对此问的回答是否定的。即使时至今日,还是有一些人际关系对我过于重要,我因此煞费苦心用曲笔去写而不是照直去写。不过我已领教到,愿意冒险用自传体写作,不仅对你的写作而且对你的人际关系都会有潜在的价值:你实际上完全有可能帮了你兄弟、你母亲、你挚友一个忙,给予他们一个机会去自如应对被写到书里去的挑战——给予他们以信任,相信他们会去爱你的全部,包括你当作家的那部分。最要紧的是你得尽可能地写得真实。如果你采用了某人的生活做素材,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人,那就该在笔下体现出那种爱意。当然还是会有风险,此人没能看出来你的那份爱意,你和那人的关系也许会因此受影响,但是你做到了所有作家到了这个地步非得去做的事情,那就是忠诚于当作家的自己。
最后,我很高兴告诉大家,我大哥和我的关系现在比以前更好了。给他寄《纠正》预印本之前,我在电话上跟他讲,他也许会讨厌这本书,甚至会恨我。他当时的回答我依然心怀感激,他说:“恨你不是个选项。”下一回我们通电话时,他已经读过那书了,他一上来就说:“哈罗,乔恩。我是你大哥——加里。”自打那以后,每次他跟自己的朋友谈起那书时,从没隐瞒过他和加里的相似之处。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有他自己的磨难和乐趣,有个当作家的兄弟只不过是他自己人生里的一段故事而已。我们都深爱着对方。
①《新抢钱夫妻》(
Fun withDick and Jane
)(1977,2005)(香港片名《贼坛新人王》,台湾片名《我爱上流》):借用二十世纪三十到七十年代美国家喻户晓的系列儿童读物的书名,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于1977年拍摄的喜剧片,该片于2005年重拍。影片讲述一对上中产阶级夫妻失业后,靠在上流社会蒙骗行窃维持生计的故事。
②
原文德文。
③
大·明斯(1961—),美国作家,以短篇小说著称。弗兰岑在本书一篇题为《你凭什么如此确信你自个儿就不是恶魔?》的评论艾丽丝·门罗的小说《出走》(或译为《逃离》)的文章里提及明斯的短篇小说。
载于《世界文学》2017年第5期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
(公众号责编:文娟)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2017
年《世界文学》征订方式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银行汇款
户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开户行:工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账号:
0200010019200365434
微店订阅

★
备注
:
请在汇款留言栏注明刊名、订期、数量,并写明收件人姓名、详细地址、邮编、联系方式,或者可以致电我们进行信息登记。
订阅热线
:
010-59366555
征订邮箱
: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