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生活的更多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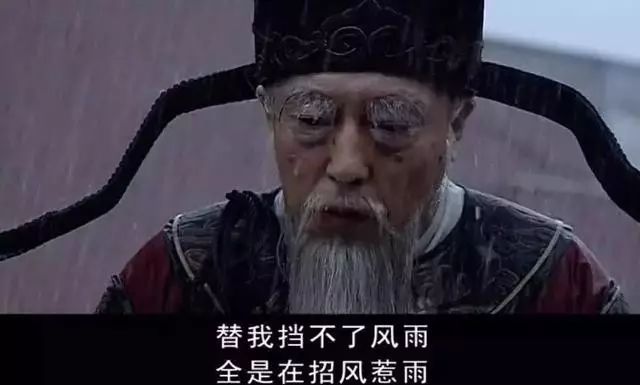
导语
叶底藏花一度,梦里踏雪几回。生活中不敢想之事,在光影圆梦。今天,电影和电视已经走进千家万户,观看热门电影,品评流行剧目,成为了青年人消遣生活的常见方式。那么,这一届青年人,他们对影视剧的看法是怎样的呢?在纷繁不一的声音背后,青年要有属于自己的发声阵地。706放映室是706发起的一个新栏目,在每一期栏目中,我们专门谈论一部影视作品,负责提供属于青年的新意见。
今天是706放映室的第1期,我们来聊聊一部大陆剧,它的名字《大明王朝1566》。
706放映室第一期
《大明王朝1566》并非翻案之作
原文首发于文汇APP
要谈论《大明王朝1566》是否为奸臣昏君翻案,不妨分析一个人物,那就是严嵩。
《大明王朝1566》中的严嵩,和正史里的严嵩相比略有出入,看得出是一个经过艺术加工的人物。正史里,严世蕃聪明狡诈,经常给父亲出主意,而剧中,常常是严世蕃添乱子,父亲不得不出来救场。剧中的严嵩是一个典型的权臣,身居高位,圆滑老辣,不动声色却又心思缜密,是君父手下敛财“擦屁股”的得力助手。


▲严嵩(倪大红 饰)
表面看来,剧中的严嵩确实有他的难言之隐,有他令人同情的一面,但这并非编剧刘和平要为严嵩翻案,他也许只是不愿塑造一个脸谱化的奸臣。
严嵩,是如此老成谋国、严不漏风,仿佛真是一个殚精竭虑、为君操劳的忠臣,但细看其行,其实他是打着顾全大局、顾全君父的幌子,为严家谋利,使严家全身而退。精明如严嵩,若真的是忠心为国,又如何一开始就提出“改道为桑”?个中的利害,年轻的张居正一眼看透,远在浙江的胡宗宪心如明镜,他的拗儿子严世蕃也有算盘,他严嵩真的是老眼昏花?

▲张居正(郭东文 饰)

▲严世蕃(张志坚 饰)
不过是他默许这种暗地里鱼肉百姓的“国策”罢了。严嵩若一心为国,嘉靖为私心损民利时,他为何不敢犯颜直谏?表面为了君父的颜面,实际是维护严党不倒于朝局。严嵩真乃奸滑首辅也。
有意思的是:剧中严嵩的扮演者倪大红其实比儿子严世蕃的扮演者张志坚还年轻。同为张黎剧中的老熟人,张志坚是1955年生人,而倪大红生于1960年,足足比张志坚小五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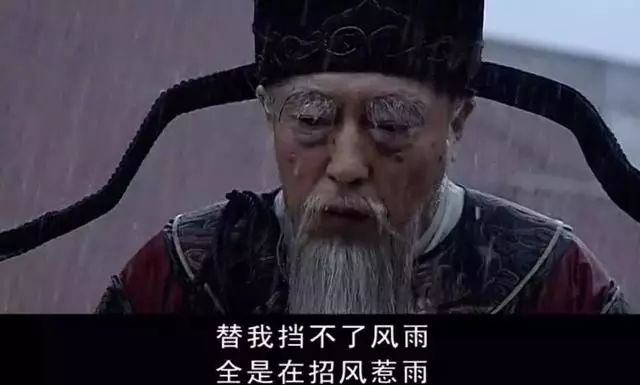
以“新历史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剧,容易陷入矫枉过正的怪圈,比如为奸臣翻案,并批判一把传统史观的“正面”人物。“新历史主义”历史剧,无非是让浸淫传统史观的观众过一把颠覆瘾,但“为颠覆而颠覆”注定走不远。
万幸的是,编剧刘和平并没有让剧中人物成为翻案的工具,《大明王朝1566》既表现出他对传统史观中昏君奸臣的不同理解,也让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民间形象在剧中“活了起来”。一出虚构剧,却像真事一样。

杨金水:我不过是皇上,是老祖宗派到浙江来的一条狗
杨金水,全剧颇为复杂的一个角色。这位宦官坏透了,他阴鸷、狠毒,工于心计。在浙江贪墨案中,他盘剥沈一石,参与毁堤淹田,牵连胡宗宪,肆意贪污,目无法度。可同时,他坚韧、隐忍,令人同情。杨金水对主上忠贞不二,对朋友感激而愧疚,对芸娘,出于情义也颇有照顾。

▲杨金水(王劲松 饰)
杨金水曾说:“做太监,唯一的天,唯一的云彩就是在宫里,太监没家,宫里就是他们的家。”命运不由他,令他打小就是为主子尽忠的奴仆命。杨金水贪,多少银子流进他自己的腰包,又有多少银子,是为了满足主子们的私欲。
被逼绝路,杨金水为何不一死了之,而选择装疯?真的只是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吗?需知道,他若一死,事情就会推到他身后的吕芳,觊觎司礼监头把交椅的陈洪,会不会借机攻讦?清流又会不会趁势弹劾?吕芳是杨金水的恩人,在杨金水眼里,他是父亲般的存在,杨金水不敢冒这个险。所以,他选择了疯。这一疯,江南织造局和内廷的线索也就断了大半,吕芳不会有事,司礼监安稳不变,宫里的体面也就保住了。

就像杨金水自己说的:“我不过是皇上,是老祖宗派到浙江来的一条狗,我得看好这个家!”他只有“半条身子”,很多时候,这“半条身子”还由不得自己。
杨金水、吕芳、陈洪、黄锦、冯保,从这些无根之人踏入紫禁城的那日起,就注定与皇权捆绑在一起,要讨论他们的命运,势必脱不开嘉靖末年的大形势。这是一盘关乎大明运数的大棋,这些太监都是其中的几枚棋子,而下着这盘棋的,正是嘉靖。
《大明王朝1566》中的嘉靖,既非圣君,也非昏君,其实就是个玩弄权术、贪谋私利但善于驾驭、大事不虚的主儿。从一个人事任命可以看出:
严党垮台,嘉靖重用陈洪,逐步将其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同时贬斥吕芳,发配中都孝陵。
这个变动,嘉靖是有私心的。
两方面,一:陈洪挡唾沫。严党倾覆,替嘉靖遮风挡雨的墙瞬间倒了,压抑已久的清流势必群起,唾沫横飞,必须找一个狠角替自己转移仇恨。吕芳、黄锦是温和派,肯定不行。徐阶的威望镇不住百官,更不消说比徐阶位分低的高拱、张居正,唯有阴鸷狠辣的陈洪可担此任;

▲高拱和张居正
二:让吕芳安享晚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嘉靖真的是因为忌惮吕芳才贬斥他的吗?我看不然。吕芳是宦官中的老人,跟了嘉靖四十多年,互相都很明白。嘉靖在这个关头把吕芳发配守陵,是让他远离严党倾覆后清流的压力,以及帝位交替引发的政治斗争,使其安享晚年。所以吕芳庆幸,没有谁会再跟他过不去了。吕芳的结局,这时候已经定了。

▲吕芳
陈洪亦然,但恐怕他的下场会凄凉许多。
表面上,吕芳被斗倒,冯保去了朝天观干苦力,陈洪高居司礼监掌印太监,正春风得意。其实他是最没得回头的一位。他鞭笞百官,得罪了士大夫;他奉命领走冯保,得罪了裕王府;他暗斗吕芳,得罪了吕芳的干儿干孙。他这样的狠角,所有人都得罪个遍,其实就是嘉靖用来震慑百官、制衡权力的一根铁棍,但嘉靖对这根冷冰冰的铁棍没有感情,用完了就丢。嘉靖龙御归天之日,便是陈洪丧钟敲响之时。他的命运无法改变。
再说黄锦。从剧本里对他的描写看,他与陈洪截然不同——他憨厚,有主见,一心一意为主子效劳,若说党派,他属吕芳一党。要讨论黄锦的未来,首先要着眼于嘉靖对身后事的安排。嘉靖之后,很明显裕王是新的主子,嘉靖要筹划身后事,就包括为裕王料理好合适的辅佐大臣和宦官。剧本第750页嘉靖对裕王的评价——“朕御极四十五年,从来是一人独治。你太弱,没这个本事”以及“朕躬德薄,你比朕仁厚”。
海瑞:我海瑞,无党无派
《大明王朝1566》里,真正可说得上为国为民不藏私心的,一个是胡宗宪,一个是海瑞。

▲海瑞(黄志忠 饰)
胡宗宪大事不虚,目光深远。严嵩对他是知遇之恩,也因为他和严嵩的联系,他被清流视为严党。但书里的胡宗宪,绝不是党争之人,相反,他厌恶别人将其视作党争之人。这个清癯的老人,惜名而不贪名,重大事而不争一时之气,你看他的实际作为,就明白他真的是老成谋国,当的起“东南一柱”。

▲胡宗宪
海瑞难演。很多人只晓得嘉靖难演、杨金水难演,因为他们一位是精通驭人之术又利令智昏的孤家寡人,一位是为主子殚精竭虑却要不惜为保全自己装疯卖傻的宦官。殊不知海瑞同样难演。演海瑞,不是抬一口棺材到家里,见谁怼谁,就叫完成任务。也不是光靠敢言直谏,天天一股为君死社稷的架势,就能将角色演出人样。

经过刘和平艺术加工的海瑞,既有自己固有的“狠劲儿”,也有自己清醒的一面。从淳安知县,到审理郑必昌、何茂才,再到改稻为桑案后收到赵贞吉和谭纶保举时的愤而离去,海瑞都在坚持自己一以贯之的原则,也是刘和平为这一艺术形象赋予的最具恒久性的品质——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刘和平笔下的海瑞,同样和历史人物一样,有封建局限的一面,有君父思想,但不同的是,百姓的利益,成为比君父更上一层的行事准则。海瑞不是不顾全大局,他顾全的是百姓的大局。他愤怒,因为一次次,官僚们利用大局的幌子,继续吃着百姓的人血馒头。群臣忙着党争,地方官包庇同侪,皇帝的面子,老师的面子,内阁、司礼监甚至王爷们的面子,每一个都凌驾于百姓之上。官僚们筹措军饷,没有法子,又继续盘剥百姓。海瑞恨自己无法改变这般局面,恨党争不休,盘剥不止,如果他妥协,顺赵贞吉和谭纶的人情,那就意味着,他默认了既定的官场规矩,他低头了。

有明以来,官场上的群臣,清流与浊流之分,看得日益得重。清流者,如《雍正王朝》之李绂,《大明王朝1566》之赵贞吉、李清源等。若说海瑞,却是清流,但倘若将清流以党派看,海瑞又决然不是,天下皆知,他孤身一人,无党无派。
也正因如此,处理浙江贪墨案时,他对赵贞吉心有嫌隙,鄙其处事;李清源策动众御史上书弹劾内阁、通政使司及各部堂官时,他劝止王用汲;群臣共上贺表恭迎嘉靖时,他却备好棺材,呈上一纸《治安疏》……
如果说,《雍正王朝》中,雍正的痛,在于身负骂名,不被理解。那么海瑞的痛,在于虽有清名,虽被理解,却也仅有理解。《大明王朝1566》对《雍正王朝》的超越在于:前者是纯粹的皇帝视角,凡事都以帝王老子的本位出发想问题,而后者别出心裁,设置了双重主角(嘉靖与海瑞),将视角从君本位拉出。

海瑞是君本、民本思想的叠加,代表中国传统中最淳朴的一种诉求,且愚且智,就连对其有所嫌隙的清流之士——泰州大儒赵贞吉,也感慨他是周公孔子所推崇之“朴人”。奈何处格格不入之世,抱负难伸。
但编剧刘和平老师终归是给孤独添了一丝温润。夜幕下,谭伦对海瑞说:“何处无月,何月不照人,只无人如我二人也”而王用汲和李时珍,更是被海瑞视作“交友无不如几者……可以寄心腹托死生之人”。
海瑞与雍正,“一个是最高道德境界上的孤独者,一个是最高权威境界上的孤独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但命运驱引下,那份孤独,依旧不可避免。

沈一石:无路可退
商人是悲剧的,不再是纯粹的“坏人”
在中国的“1566年”,商人是悲剧的,是最值得同情的群体之一。

▲沈一石
沈一石有自己的可鄙之处,苟且织造局、浙江巡抚,当着宫里的差,捞自己的钱!赚钱都赚到皇帝老子的头上。但他到底只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商人,和千千万万中国商人一样,商人不和官僚捆绑在一起,似乎就注定混不开,商人腰缠万贯、富可敌国,朝廷仰仗他们的财富,尤其是末世。且看远征新疆的左宗棠,还没从十余年太平天国之乱缓过来的清廷,又面临海防塞防之争,清廷纵然同意他收复新疆,国库也挤不出多少银子。靠谁救急?还不是商人——大名鼎鼎的胡雪岩。多方疏通才筹来钱粮。可坐拥金山银山的他们,地位又是多么不伦不类,随手翻翻封建官僚呈给君主评议商人的奏折,就足见他们对商人的轻视和鄙夷。
商人要过活、要致富,不看官僚的颜色,便是空话。朝廷拿不出军粮了,找谁开刀?最简单的还不是抄商人的家!商人就是如此尴尬。
沈一石可鄙,比他更可鄙的是腐败贪婪的大明官僚。
附:
父亲—媳妇—儿子,兼谈《大明王朝1566》的两种理想主义
中国的历史剧创作难免面临无奈,看的人少,所以拍十部亏九部,拍历史剧不是过家家,花钱多,尤其是对器物要求高的剧,更需要投资人有一掷千金的胆识。在中国,谁相对不计较亏损?还得是公家。公家出于不同目的,有时候会掏钱做赔本买卖,历史剧就是一种。但国家机关不是慈善机构,它愿意花钱,自然有它的要求,比如宣传宣传某个人物、支持支持某个政策,这就是文化工程、形象工程。所以很多历史剧创作者从一开始就需要妥协,拿人手短,不可能由着你的创作念头拍,妥协一点,整个东西才能留下来。
《雍正王朝》是,《汉武大帝》是,《北平无战事》是,《大明王朝1566》也是。有人说这部剧尺度大,说它借古讽今,甚至曾谣传它被封杀,可该剧最初其实也只是做给官方的命题作文。
2003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到海南视察时专程拜访了海瑞墓,在参观海瑞墓时他说:“海瑞的精神今天仍然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来海南一定要到海瑞墓看看。”(《海口晚报》2008年12月3日载文博专家邱达民口述,中新网2007年3月4日载编剧刘和平讲述)
当时吴官正还留下了一句话:
“为什么你们不宣传海瑞?”
于是,时任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松林找上了张黎和刘和平,《大明王朝1566》最初的目的很纯粹——宣传海瑞。
你也许一看到“命题作文”会感到失落,因为“命题作文”四个字难有崇高感,倒给人一种逢迎苟且的平庸之味。但很多优秀的作品它就是命题作文,或者说:作者创作的初衷并不崇高。也许只是为了养活自己,也许是帮别人忙,也许就是因为创作者的焦虑症,此时不拍,以后就不一定有机会了。初衷宏大的作品未必能拍好,命题作文也不见得差,关键看人如何去做,怎么在一个筐子里做到详略得当。艺术常常是戴着镣铐跳舞。
历史剧不得不挨着公家,与虎为邻,有时候,这只虎会庇护你;有时候,它也会警告你。《大明王朝1566》有中纪委的庇护,和外界的揣测不同,当时负责审片的同志都没太难为创作者。但是,这部剧并不会因此永保平安,今年年初它的重播失败就是一声提醒。一部剧会不会消失,不仅仅看它的内容本身是否越界,还要看它的社会影响、它的投资者、参与者处境。所以冷门的历史剧反而有一个好处,不用太过担心社会影响。如果一部剧火了,影响大了,盯的人就多,自己不能左右的情况也会变多,这不一定是好事。
在中国,很多理想主义者不是像海瑞这样,海瑞很理想,但这种人注定少得可怜,那种为了自己心中的道奋不顾身的意志,那种真正发自内心相信自己的道的执念,很少人能坚持。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更可能像剧里的胡宗宪,这是一个怎样的艺术形象?吕芳说:“他就像个媳妇。上面有公婆要孝顺,中间有丈夫也得顾着,底下还有那么多儿女要操劳。辛苦命,两头不讨好。”
这里需要指出:艺术不同于史实,艺术形象也必然会与历史原型有出入。《大明王朝1566》的胡宗宪,比正史里的胡宗宪更有文臣气质,也更正面些。他是能臣,嘉靖说他老成谋国;他是媳妇,在一个家里充当润滑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最初也许同样有骑士梦,渴望像荆轲一样,为骑士理想而献身。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真正成为骑士的又有多少?留下来的,他们并非泯灭理想,而只是以另一种方式——一种看上去平庸苟且的方式,一点一点构建心中的理想国。
刘和平说:“1566年,封建体制走到了尽头,明朝的特点是家国不分、朝廷不分。具体来说,紫禁城乾清宫是分界处,乾清门以外是国,门以内是家;门以外是朝,门以内是廷。明朝皇帝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直接在‘廷’内、也就是在皇帝家里,将大臣杖毙。嘉靖是在这一年去世的,之后裕王朱载垕继位。几十年来,皇室与文官集团的争斗在这一年结束,朝和廷开始区分了。隆庆帝把权力交给政府机构,起用了徐阶、高拱、张居正。嘉靖一死,他第一个就把海瑞从牢里放出来升官。”
家国关系是《大明王朝1566》的一个核心点,家有大家小家,小家即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各自的家庭,而大家,在皇权社会的背景下,即中央政权。由于皇权社会服膺于父权社会,因此在“家”这个共同体里,父是掌握最高权威的那一极。决定一个共同体内的个体是否为父的不是那人的性别,而是他是否拥有父的气质和地位。而家的另外三极是母亲、媳妇和儿子,不过在《大明王朝1566》的设定中,母亲是缺位的,无论是宫廷还是个体之家,母亲都处于消失状态。即便像海瑞家的海母,她实际上拥有的是“父”的气质和地位,她是海父去世后父的替代者,而代价是母亲这一角色的丧失。
“父亲—媳妇—儿子”,三者贯穿《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有趣的是,这种以父主导、三者并存的情形,在《大明王朝1566》中比比皆是。比如在朝廷之中,是皇帝—宦官—文官。事实上,在正史的记载中,嘉靖朝的宦官中规中矩,并没有大的动静。我们听过魏忠贤、刘瑾,但很少听过嘉靖朝的宦官。刘和平之所以特意在故事中加重宦官的戏份,正是为了达成这种“三者并存”的状态,但三者并非互相制衡,而是以君父为主导,三者互动。
《大明王朝1566》的宦官不像传统历史剧叙事般被妖魔化,他们未必个个都忠厚老实,但也绝非十恶不赦,他们的善是人性的善,他们的恶也是人性之恶,刘和平没有去刻意写极端的非人之恶,也更没有将这些恶强加于宦官头上。吕芳、杨金水、黄锦都体现了人性之善,他们本质上是皇帝的奴仆,但他们没有泯灭做人的本性。
媳妇是这种家庭权力结构中最受气的一方,却也是缓和家庭矛盾必不可少的一方。在“皇帝—宦官—文官”的结构中,宦官是媳妇;而在“皇帝—内阁—其余臣子”的结构中,内阁反而成为媳妇。所以徐阶说:“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百兆生民,就像这一家的子女,皇上就是这一家的父祖。臣等便是中间的媳妇,凡事但按着媳妇的职分去做,能忍则忍,该瞒则瞒,尽力顾着两头。实在顾不了,便只好屈了子孙也不能屈了公婆。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媳妇再能干,也只是裱糊匠,无法打破这一权力结构,而海瑞这样的“子”看上去最接近打破这种不平等的结构,但其实他也无心打破,海瑞并不是超越时代局限性的神,他身处环境之中,又从小受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熏陶,他的一切行为实际上也不是要打破固有结构,而只是以更激进的手段来达到改良的目的,来让这个结构重新转危为安。所以,海瑞依然是一位维护者,而非革命者。
海瑞成为道德模范是他的幸运,但从他的初衷而言却也是他的不幸。道德模范被人敬仰,却无法被托付真正的重任,海瑞的破坏性也会因道德模范的标识而消解。而胡宗宪是一个主动皈依于世俗社会行事逻辑的理想者,他做事并非全为自己、为所属党派,他同样有对国家和百姓的关怀,这是他理想主义的地方。但是他做事不像海瑞,不是直捣黄龙、打破秩序,而是在固有秩序内迂回行驶,寻求渐进改良,尽管这种改良并没有制度保障,而只能靠个人的恻隐之心维持。
海瑞与胡宗宪是两种形式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互相钦佩,在精神上保持平等,但他们知道各自的不同,尤其是胡宗宪,他不欲做海瑞所做之事,但他知道——大明朝需要海瑞。
为了安排两人一见,刘和平特意安排海瑞与胡宗宪营中对谈,在那一段里,胡宗宪吟了两首诗,一首赠海瑞,一首赠予自己:
《封丘作》
高适
我本渔樵孟诸野, 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 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 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长官心欲碎, 鞭挞黎庶令人悲。
悲来向家问妻子, 举家尽笑今如此。
生事应须南亩田, 世情尽付东流水。
梦想旧山安在哉, 为衔君命日迟回。
乃知梅福徒为尔, 转忆陶潜归去来。
————评价海瑞
《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岑参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
平明发咸阳,暮到陇山头。
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
沙尘扑马汗,雾露凝貂裘。
西来谁家子,自道新封侯。
前月发安西,路上无停留,
都护犹未到,来时在西州。
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
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
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
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
山口月欲出,光照关城楼,
谿流与松风,静夜相飕飗。
别家赖归梦,山塞多离忧,
与子且携手,不愁前路修。
————评价胡宗宪
-end-
今日话题
你看过《大明王朝1566》吗?

文字 | 宗城
图片 | 豆瓣
编辑 | 吴宪达
about 706
706青年空间位于宇宙中心五道口,是中国第一家青年空间。706已经举办了上千场活动,发起了数十个创新项目,世界各地有趣好玩的青年人在此汇流。我们试图创造一种新型的实体空间形态,孵化具有潜力的合伙人项目,通过社群式的学习,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教育理念,让青年人探索生活的更多可能性。


长按二维码,关注706青年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