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迷影课」。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是公认的电影大师,也是冷战后期最为典型受到政治压迫的艺术家,他的创作生涯与戛纳电影节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对于分析戛纳电影节在历史上的文化策略具有很高的代表性。
在一九七〇年代,塔可夫斯基开始在苏联国内受到打压,剧本得不到批准,工作没有酬金,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二十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我在祖国没有得到任何报酬或任何电影奖项,也从未参加过苏联的任何一次电影节。」
在这样的境况中,国际电影节成为他最终走出苏联、引起国际关注、继续从事电影创作的重要平台。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创作从最初就与国际电影节有不解之缘,他的长片处女作《伊万的童年》在一九六二年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成为举世瞩目的电影新星。

《伊万的童年》(1962)
这部电影是苏联政府正式选派的作品,塔可夫斯基在影片制作过程之中接手工作,重写剧本后在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Goskino)的授意下拍摄完成。
「《伊万的童年》的主题与美学没有新奇之处,却是一个难得的变体。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将金狮奖颁给了这部影片,以此褒扬一部‘苏联新浪潮’的典范之作。」
从第二部作品《安德烈·卢布寥夫》(Andrey Rublyov)开始,塔可夫斯基开始建构属于个人的电影美学,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他的作品与戛纳电影节发生关系。
这些渊源和纠葛恰好见证了戛纳电影节在一九七〇年代接受和容纳社会主义国家所谓的「问题导演」、「流亡导演」的文化策略,也体现出这个策略带来的阻力和无奈。

《安德烈·卢布寥夫》(1966)
但是,当《安德烈·卢布寥夫》在一九六六年完成时,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对影片的内容很失望。一九六七年,戛纳电影节的代表在莫斯科看过影片拷贝后,正式向塔可夫斯基发出了参赛邀请,但是国家电影委员会以需要重新剪辑为由,承诺影片会在一九六八年参展。
但是到了一九六八年,影片没有被送过来。直到一九六九年,《安德烈·卢布寥夫》制作完成两年后才被送到戛纳电影节,而在苏联官方要求下,影片不能参加竞赛单元,而只能参加「非竞赛单元」。
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用很多理由禁映这部电影,其中一个理由居然是因预算不足而没有拍成的库利科沃平原会战,这场一三八〇年发生在俄罗斯人和鞑靼人的战争最早出现在剧本中,后来因莫斯科电影制片厂预算不足而没有拍出。
事实上,塔可夫斯基一直很渴望拍出这场戏,「但这需要二十万卢布的费用,于是他设计了一个比较省钱的、但艺术含量更为充实的方案:会战后的早晨。」
影片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初剪完成,年底在莫斯科小范围试映,国家电影委员会的批评意见认为,影片对卢布寥夫这个人物缺乏乐观主义,没有充分表达出俄罗斯人对鞑靼人统治的反抗精神,残酷和裸露场景过多,电影语言过于灰色难懂等。

《安德烈·卢布寥夫》(1966)
苏联政府禁映了这部电影,苏联国内媒体的评论也与国家电影委员会相一致,批评影片的残酷和阴暗。尽管影片没有参加一九六九年竞赛单元,但塔可夫斯基当年还是获得了国际影评人协会的费比西奖,这对塔可夫斯基是非常重要的鼓励。
即便如此,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阿里克谢·罗曼诺夫(Aleksey Romanov)居然还打电话给塔可夫斯基,要求他公开拒绝接受这个奖。塔可夫斯基非常生气,但也只好不对这个奖项做任何回应。
从《安德烈·卢布寥夫》被禁之后,塔可夫斯基计划改编波兰科幻小说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law Lem)的小说《索拉里斯》(Solaris),但国家电影委员会迟迟不答复,直到一九七〇年六月,拍摄申请终于被批准了。
塔可夫斯基在给莱姆的信中写道:「制片厂很快就要开拍《索拉里斯》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先生,您想象不出我有多么兴奋!我终于可以工作了!」
《飞向太空》的拍摄很辛苦,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影片剪辑完之后,苏共中央委员会、迪米乔夫办公室、国家电影委员会等审查部门观看了内部试映。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一日,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厂长尼古拉·西佐夫向塔可夫斯基传达了三十三条(实际上是三十五条)修改意见,塔可夫斯基认为这些修改意见「荒谬」、「荒唐」,「不可能做到」,「会毁了整部影片」。但塔可夫斯基参见的创作团队最终还是根据意见进行了调整。

《飞向太空》(1972)
几次修改,都达不到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罗曼诺夫的要求,影片分别是二月二十一日、二月二十五日连续两次送交,罗曼诺夫都不签字。塔可夫斯基决心抵制修改。但是到了三月二十九日,事情有了转机,罗曼诺夫亲自来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通知《飞向太空》无需任何修改就通过了。
原因是尼古拉·西佐夫把《飞向太空》给了三位高层领导观看,影片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四月二日,影片被定为代表苏联参加戛纳的电影,提供给戛纳电影节的选片代表观看。四月二十四日,影片正式定为参赛。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三日,《飞向太空》在戛纳首映,塔可夫斯基第一次来到戛纳并出席了首映式。「我真的不相信会有什么奖,这次有些很好的电影,有佩特里、波拉克、杨索。」影片的放映获得了空前成功,获得评委会特别大奖。
戛纳的成功让国际电影界进一步认识了这位来自苏联的与众不同的电影艺术家,塔可夫斯基被立即邀请担任一九七二年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这种成功不仅鼓励了塔可夫斯基坚定自己的艺术创作,也让苏联当局非常满意,这让塔可夫斯基可以拍摄带有自传色彩、片中大量使用父亲诗歌的半自传作品《镜子》。

《镜子》(1975)
但是《镜子》的拍摄没有满足委员会设想的表达「人物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在拍完之后,塔可夫斯基也不能按照委员会的修改意见修改,所以一九七五年年初,国家电影委员会运用行政权力以极为低调的方式放映了《镜子》,只有两家影院,没有任何宣传,观众很少。也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反响。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戛纳电影节主席莫里斯·贝西(Maurice Bessy)到了莫斯科,他希望看《镜子》,但当时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叶马什(F.T. Yermash)极力向他推邦达尔丘克,拒绝让贝西看《镜子》,最后直接拒绝让《镜子》参加戛纳电影节。
谢尔盖·邦达尔丘克是苏联著名导演,一九二〇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九四八年毕业于苏联国立电影学院(VGIK),一九五九年因改编了《一个人的遭遇》而成为苏联政府认可的代表性导演,并改编了托尔斯泰著名小说《战争与和平》。

谢尔盖·邦达尔丘克
叶马什希望在戛纳电影节这个平台上,让邦达尔丘克取代塔可夫斯基,成为苏联电影艺术的名片。
根据塔可夫斯基日记,叶马什最终不让《镜子》参赛的原因,竟然莫里斯·贝西在邀请《镜子》时担保会获得大奖,而这恰恰是苏联官方担心的。贝西非常生气,威胁叶马什如果不给《镜子》,就不带任何苏联电影去戛纳。
塔可夫斯基也非常愤怒,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厂长西佐夫当面质问,然而这都无法改变结果。但是,根据吉尔·雅各布的回忆,一九七六年,戛纳电影节还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了《镜子》的拷贝,当他们在戛纳电影节期间放映时,苏联外交人员试图冲进放映厅制止放映,但是房门已经被反锁而他们没有能力破门而入。
一九七五年七月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邀请了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做评委,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威胁如果不放映就立即离开),在电影节上重新放映了《镜子》。除了戛纳,《镜子》没能参加当年任何一个邀请它的国际电影节。
影片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在苏联再次公映,受到苏联观众的强烈反响。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的《前言》中记录了当时观众给他写信交流感受的情况。
一九八〇年,当《潜行者》刚刚完成时,威尼斯电影节主席利查尼和莫拉维亚曾向叶马什邀请《潜行者》,但被叶马什拒绝。理由有二,第一,威尼斯是个颓废电影节,第二,塔可夫斯基电影决不能出现在威尼斯,这样会让威尼斯电影节显得比莫斯科电影节更重要。

《潜行者》(1979)
但最终,《潜行者》以「惊喜电影」的身份进入戛纳电影节非竞赛单元,展映之后影片大获好评。塔可夫斯基在五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写到:「所有报纸大幅报道《潜行者》在戛纳。极大成功。隆蒂称之为天才之作,伟大影片。实际上,重复他那些话令人尴尬。总之——轰动了……我现在并非真的在乎报上那些话。但我想不起有哪位导演获得影评人这样的赞誉。」
塔可夫斯基不断听到来自戛纳的赞誉,尤其是应观众、评委会和影评人的要求,《潜行者》在戛纳进行了加映。正式由于戛纳的成功,意大利制片人克里斯塔蒂决定做《乡愁》的制片人,《乡愁》(Nostalghia)才得以很快拍摄。
《乡愁》由意大利人制片,影片在意大利拍摄,苏联政府批准了塔可夫斯基去意大利长期拍摄的申请。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四,吉尔·雅各布(Gillesl Jacob)在罗马见到了塔可夫斯基,他们想邀请塔可夫斯基参加戛纳国际电影节,雅各布许诺说这次第三十五届戛纳电影节会为十二位优秀导演发奖,其中包括塔可夫斯基,同时雅各布邀请塔可夫斯基做竞赛单元评委,但塔可夫斯基当时已答应做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委,所以拒绝了评委的邀请。
最后,雅各布邀请《乡愁》能参加戛纳,塔可夫斯基同意了。

《乡愁》(1983)
一九八三年,《乡愁》顺利入围了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影片讲述一位俄罗斯诗人去意大利寻访一位音乐家的经历。影片在戛纳再次获得极大的成功,法国媒体对这部电影做了很多报道,然而这部完全可能获得金棕榈奖的作品再一次与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不期而遇了。
苏联派出谢尔盖·邦达尔丘克参加评委会,塔可夫斯基从评委会成员、法国作家、记者伊冯娜·贝比(Yvonne Baby)那里听说,邦达尔丘克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抨击《乡愁》,「他对我的电影一贯有敌意,因为以前就派他来戛纳诋毁我的影片,尽管所有来过戛纳的苏联电影官员向我保证,说他起码是诚实的。他们继续如此过分,显然故意派他来戛纳,为了阻止我得奖,因为这会增加我在国外工作的机会。」
最终,今村昌平的《楢山节考》获得了金棕榈奖,英国导演特瑞·琼斯(Teery Jones)的《人生七部曲》(The Meaning of Life)获得了评委会大奖,印度导演莫利奈·森(Mrinal Sen)的《结案》(Kharij,1982)获得了评委会奖。

《楢山节考》(1983)
而《乡愁》则与罗贝尔·布莱松的《金钱》(L’argent)共同获得「电影创作大奖」,这个奖是当年特别给出的奖,相当于历年的最佳导演奖。塔可夫斯基与布莱松都亲自上台接受了颁奖。
然而不可否认,《乡愁》是塔可夫斯基在戛纳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作品,影片还获得了国际影评人协会费比西奖和天主教人道精神奖。
塔可夫斯基对于苏联当局指派邦达尔丘克做评委,以阻止他获奖的猜测,并非没有根据。
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苏联媒体对当年戛纳的评价:「二十一号的《苏联文化》有篇关于戛纳电影节的文章,说水准很低,还说有些印度(!)和土耳其(关于鸡奸者?)的好片,最佳影片是日本片——很人道——而塔可夫斯基与布列松同获评审团特别大奖的导演一项。安娜·西蒙约诺芙娜、我们全家及莫斯科的朋友们都很沮丧,但我告诉她并非如此。越坏的,就越好。」
这里所说的「越坏的,就越好」可能隐含两种解释。其一是,他的作品越是在国际电影界受到苏联官方压力而遭遇阻挠,越能说明他的创作具有意义。其二,另一种可能是含义是:恰恰这次没有获得金棕榈奖(越坏的),让他终于做出放弃苏联、留在西欧的决定(越好的)。
关于一九八三年戛纳电影节与塔可夫斯基决定留在西方、选择流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法国电影史学者安托万·德·贝克(Antoinede Baecque)这样写到:「作为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的苏联官方导演,邦达尔丘克的态度惹怒了塔可夫斯基,而且将会给塔可夫斯基回国带来麻烦。为此,塔可夫斯基决定在西方多停留三年。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于一九八三年六月给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写了那封信,希望能够为儿子和岳母申请到签证。一九八四年七月十日,一年过去了,他没有收到任何答复。于是,他决定和妻子拉丽莎留在西方,并在罗马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了这一决定。」

安托万·德·贝克
安托万·德·贝克在《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中引述了塔可夫斯基这封信的内容,其出处为法文书《尘封的时光:从到》(Letemps scellé: De l’enfance d’Ivan au Sacrifice, 1989),但很遗憾,这封对于塔可夫斯基人生最重要的信(宣布放弃苏联公民权),没有收录在《雕刻时光》和《时光中的时光》的中文版中。
在这封信中,塔可夫斯基痛陈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数年来对他创作的刁难和打压:「我在苏联工作了二十二年,执导了五部影片,也就是说平均每四年半一部。执导一部电影大约需要一年,再加上剧本写作占用的时间,如此算来,在这二十二年之中,有十六年时间我待业在家。然而,就在国家电影委员会把我的影片成功地变卖到国外的时候,而我呢,却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不知道该怎样养家糊口……我累了,因为遭受迫害而累,因为饱受苦难而累,因为你们逼得我一直没有工作而累。」
塔可夫斯基与妻子拉丽莎在流亡期间格外惦念留在国内的儿子安德鲁什卡,但苏联政府始终不同意安德鲁什卡出国,塔可夫斯基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思念的痛苦中,甚至在日记中写「不想活了」。一九八五年冬,在瑞典拍摄完《牺牲》之后,他查出患有严重的肺癌。一九八六年一月,苏联当局决定让安德鲁什卡离开苏联。

《牺牲》(1986)
一九八六年五月,《牺牲》代表法国和瑞典合拍片入围了第三十九届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戏剧性的是,邦达尔丘克导演的《鲍利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v)也正式代表苏联进入了这一年的竞赛单元。
吉尔·雅各布当年与苏联交涉,想要另一位受到政治迫害的格鲁吉亚导演谢尔盖·帕拉杰诺夫(Sergei Parajanov)的《苏拉姆城堡的传说》(Ambavi Suramis tsikhitsa)进入竞赛单元,但苏联坚持要送邦达尔丘克的。
而这一次,《牺牲》以其令人惊讶的艺术造诣最终获得评委会特别大奖,只差一点输给了罗兰·约菲(Roland Joffé)的《教会》获得了金棕榈奖,而《鲍利斯·戈都诺夫》则一无所获。

《教会》(1986)
此外,《牺牲》再一次获得天主教人道精神奖和国际影评人协会的费比西奖,塔可夫斯基成为戛纳历史上唯一获得过三次天主教人道精神奖的导演。安德鲁什卡代表父亲在戛纳领奖。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塔可夫斯基因肺癌在巴黎逝世。
尽管塔可夫斯基的多数作品都在戛纳电影节参赛和展映,可以证明戛纳在一九七〇年代对华约阵营国家具有政治争议导演的发现、包容与支持,并尽可能为他们的创作提供帮助和扶持,但是,戛纳电影节因特定时期的选片方式而受制于政府,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选片,这让处在国际关系敏感地带的戛纳电影节为了获得优秀电影的拷贝而不得不与官方展开谈判、较量和合作,有时甚至要做出让步和妥协,而且难以掩盖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强烈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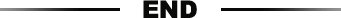
往期精彩内容
推荐一位被严重低估的日本大师
他在法国大师导演的心中,俨然就是电影的化身
这个法国导演的作品挑战所有禁忌,让我看得欲罢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