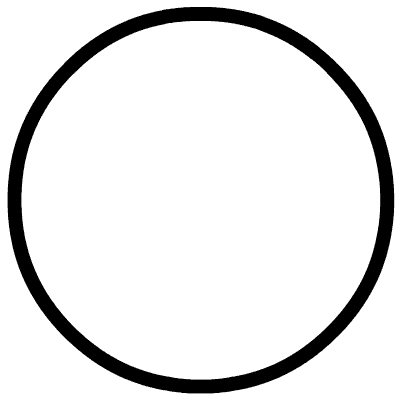来源 | 群学书院(ID:sacademy)
作者 | 朱西润 编辑:学妹

即使大学老师放假了,但过得并不轻松。当然,各行各业也都不容易。
1月14日,周六,距离2017年春节还有不到两个星期。在城市里打拼的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开始心猿意马,即便身体在办公室,心里牵挂的,都是晚上的饭局、淘宝上的年货和假期的出行计划。
然而,在FD大学中文系朱西润老师(化名)的办公室里,你完全感觉不到即将过年的气氛。和过去一年中几乎每一天一样,朱西润一大早就来到办公室,打开电脑,修改他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书。朱西润是刚到FD大学没多久的年轻博士,申请到国家课题,是职称晋升中最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
两周以前,朱西润就结束了所有的课程教学,算是进入寒假状态。中学同学微信群里,总有人时不时@朱西润说,说还是你们大学老师轻松,平时不坐班,过了元旦就放假,不像我们,朝九晚五一直要熬到大年三十前一天。每逢这时,朱西润只能默默地发一个无奈的笑脸做回应。
中学同学不会理解,对于像朱西润这样的大学青年教师来说,身体坐班不坐班,实在只是形式而已。
在授课之外,大学老师最主要的工作是知识创造与生产,这种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永远没有“上班”“下班”的区别
——半夜里突然醒来,那篇没完成的文章有了思路,你是起来挑灯夜战,还是翻个身再睡过去?大年初一,海外审稿人突然来了一封邮件论文修改意见,你是赶紧打开电脑还是歇到正月初七以后再说?……这样的事对于大学老师来说,太司空见惯。
是的,大学老师的身体很少加班,因为他们的大脑从来不下班。

对于朱西润和他的很多同事来说,寒假的开启,只是意味着一段时间相对完整的,更高强度的脑力工作开始了。
在这个寒假里,朱西润要完成社科基金申报书的完善。这通常要修改上无数轮,直到你看着那些文字都想吐了为止。最近几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率大约在15%左右,这意味着每十个申请者中只有一两个人可以入选,而自然科学基金的立项率更低。朱西润说:“前辈跟我们说,拿项目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屡战屡败不一定是水平不行。但如果你熟悉了申请的套路,包括表格填写的规范,会增加很大希望。”。
此外,他还要修改两篇文章,完成课题组一部书稿的部分内容,以及下学期两门课的备课。
亲朋好友常常不理解,你的课都上了五六年了,还需要备课?朱西润心里说,网络化时代,没有站在讲台上的人,根本不足以谈人生!你在台上讲,学生在底下随时百度,任何一个小错误,都很难逃过这些95后的眼神。
在大部分高校,老师讲完课还要接受学生的“用户评价”,评分还关系到教师前程——太靠后的话会影响职称评定。刚进校的前几年,朱西润缺乏教学经验,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既不愿丧失自我尊严与风格,又不得不注意“修辞之术”。在他看来,“老师是雇员,学生是消费者。”
初中时候,朱西润语文老师指定的课外阅读材料中,曾经读到中国土壤学奠基人候光炯院士的事迹,其他都忘记了,只有一点记得:
每年春节,候光炯给自己规定的休息时间,只有大年初一一天,正月初二,他就雷打不动的进入实验室,一直到他91岁去世。
那个时候,朱西润的感觉只有一个:不可思议!连弄堂口那个一年四季不关门的包子铺,过年还要休息一个礼拜,怎么可能有人年初二就开始上班呢?
他万万没有没想到的是,二十年以后,这样的生活,成为自己以及身边大部分年轻同事生活的常态。

2006年,《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一位大学青年教师用“青椒”一词自嘲,从此,这个词成为高校年轻教师的代称。十年来,围绕这个词的,有辛酸、无奈、困惑、重压、挣扎等等诸般心路,这些词汇描画出一幅色彩灰暗的大学青年教师“囧象”——从个人收入、婚恋、住房、职称评定、科研与教学的关系,到学术环境的行政化、市场化、学术不端、人情社会、重理轻文、急功近利,他们受到360度全方位的讨论。
“囧象”之外还有“乱象”。
2016年1月7日,在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会议即将开始时,院内青年教师李思涯突然冲到院长甘阳面前,连扇他几个耳光,声称对方未依时解决他的职称问题。在网上的舆论中,为甘阳愤慨者有之,同情李思涯者亦有之。或指责李思涯有辱斯文、败坏师德,将谋求私利的违法行为美化为以武犯禁的“侠义”之举,刻意制造新闻事件以“青椒”的弱势身份博取同情;或认为是因为当前高校六或九年内“非升即走”的职称制度,公权力者的独断严苛,对“青椒”形成太大生存压力,把原本充满理想的老实人逼上绝路……
大学青年老师的压力,很大一部分源自越来越多的国内一流大学实施的“非升即走”制度。
2003年,为提高大学的业绩,北京大学率先引入西方大学的考核制度来增加教师的晋升压力。当时,人文社科院系的反对声音更加强烈,限时、计量的考核方式被认为不适合人文社科。
如今,越来越多的知名高校采用“非升即走”制。而许多二本院校、非“985”或非“211”大学,并没有这一制度。
对于这套职业晋升体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时胜勋认为,“学者付出必需的心力是应该的,毕竟这是现代学术体制所要求的”,“但学者的本职更应该在于学术精神的培育与提升上,如果付出的心力只是在形式上的,比如经费数额、成果数量、项目多少,这些都是学术的表层和末节,过分强调有悖于学术精神,也不利于学术的正常发展。”
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陈平原教授说的更直接:“
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对人文学的伤害远比对社会科学大。而最受伤害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者,因现在需要的是早出活儿、快出活儿、多出活儿,而不是出好活儿。人文学研究需要厚积薄发,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很容易被边缘化,乃至被甩出轨道。
”

实际上,令朱西润感到“压力山大”的,除了工作和科研负担,还有与此不太匹配的收入。
朱西润今年32岁,去年十月老婆刚刚生了孩子,浙江老家的父母到上海帮自己带孩子,加上房贷,每个月七七八八的花销不是小数。他现在每个月到手的薪水八千左右,和老婆两人基本上都是月光。
朱西润大学时候最好的同学钱木,是法律系的,本科毕业就在一家律所工作,一直干到合伙人,当然也是没日没夜的干,但是收入是朱西润的五倍。“
从硕士到博士,我比钱木多读了七八年书,现在看起来,从收入说,这七八年是荒废了,还要重头来,在可以看到的未来,好像也追不上他了
”,每次想到这个,朱西润总有一种强烈的“知识无力感”。
201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薪酬管理研究分会课题组发布的一项有关高校教师的收入调查显示,高校教师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下的占总人数的85.9%,其中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占47.7%,青年教师中近1/4的人收不抵支。
“以我观察到的情况来看,10万元左右是大学青年教师收入的一个‘天花板’,很难跨越过去。现在很多老师都在学校外边兼职,搞搞培训呀、讲座呀,能额外多赚一些钱,但能做这些的都是拿到副教授以上职称的老师。职称问题解决之后,他们的时间安排会更从容一点。我目前还处于一个‘爬坡’阶段,如果在接下来的三年之内拿不到副教授职称的话,就得离职走人。所以我目前大部分的精力都得放在学术和科研上,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朱西润说。
在朱西润看来,“青椒”这个群体,从收入、福利、社会地位来说,不能算作是“底层”的,但是他们的认同确实有“向下”的趋势。
“跟一些大咖教授聊过,他们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也都没有房啊,即使分了房也是筒子楼,他们觉得是不是你们八零后太娇气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与他们那个年代相比,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他们那个年代的高校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的行政化和量化的考核,他们不用交各种各样的教案、教学日历、项目申报表。而且现在很多高校都开始引入美国高校那种临时合同,两年一签或者三年一签,考核不过就得走人,非常残酷,大部分的女老师在考核期间都是不敢生孩子的。”
朱西润的一位青年同事思考过这个问题:“大学教师本来应该是所有职业里最自由的,现在看来是落差最大的。因为你对公务员、警察、白领不会有太多想象,只有大学到现在仍然是想象最多的。你说医生、律师也有想象,不会有对大学的想象这么美妙吧?”
想象之外的现实,是一道尴尬的夹缝。立于体制内的大学,在“去行政化”改革缓慢前行之时,又需面对市场化的冲击。体制堡垒与市场狂欢的夹击下,他们还能保持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吗?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南方人物周刊》第461期《“青椒”之焦,大学青年教师的现实之困》,特此鸣谢。

诚意推荐 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