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TITUTE|星丛共通体|读/译/写/画/讲
初译|
黎辰
/
校排|
PLUS/
责编|
王家浩

本次推送的
“标题党”
取自于1980年代的事实,
而引起这些事件的
迈克尔·索金
[Michael S
ORKIN,
1948-2020
]是一
位
建筑师、城市学者、教育家和批评家,纽约城市大学城市设计系主任。院外此前推送
《建筑与资本主义》
对谈纪要
时曾经提及过他。
遗憾的是,2020年索金因COVID-19引发的并发症去世。近五年来,国际建筑界有一些塔夫里之后最为优秀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相继去世,迈克尔·索金就是其中之一,其他的还包括我们介绍过的
让-路易·柯恩
,
安东尼·维德勒
等。
标题中的“约翰逊”指的是菲利普·约翰逊。
1980年代,
这位大佬在纽约乃至全球建筑界权倾一方、风光无两,而且刚建成不久的
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楼也作为后现代风潮的标志性建筑广受推崇。索金却认为那只不过是粗鄙不堪生拉硬拽的时髦打扮而已。1991年他在自己的第一本文集中,认为后现代运动是“一场
唯我主义、自恋建筑的狂欢,沉浸在自我参照和装点门面之中。”
而更大的争议在于,索金揪出了约翰逊参与过纳粹政治的黑历史,成为了最早公开讨论此议题的批评者之一,导致了他与另一些建筑评论界大拿们旷日持久的论战。
标题中的“特朗普”就是现在那个特朗普。1980年代,当
《纽约时报》在为唐纳德·特朗普的建造计划摇旗呐喊,赞誉
资本主义的黄金期之时,
索金就已经在《乡村之声》上公开叫板,呼吁抛弃特朗普,抛弃这类项目。
这种
好斗的、公开的社会主义方法进路,
善辩、直言不讳的批评风格,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之时。
国内人文学界(甚至是建筑领域)未必知道索金,但是肯定会对他的同道、同事、好友,写过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马歇尔·伯曼有所了解。我们在这篇短文中也不可能详尽地介绍他的工作,所以集中选取了他从事的建筑与城市批评的部分。
如果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这个时代对于建筑师的创作而言,可能未必是个好的时代。然而,幸或不幸,行动派的批判者
在建筑界
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这些新兴的建筑批评人
对建筑业的审美、还有政治和社会诸多的弊端发起挑战。
他们会利用更为广泛的媒介手段,而不只是建筑类的出版物,在这类批评出现之前,
迈克尔·索金从1980年代起就已经在那么做了。
在跟随迈克尔·索金再出发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地介绍一下索金的人生经历。
1948年,索金出生于华盛顿特区,父亲是科学家。1970年,他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建筑学并获得学位,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获得英语硕士学位。
正是哥伦比亚大学,让他来到纽约并爱上了这座城市,他大部分最好的著作都献给了纽约,尤其是《曼哈顿的二十分钟》(2009年)一书。那是索金写给20分钟通勤时间的情书,他住在
一栋老旧的租金管制公寓里,从格林威治村的公寓大楼到翠贝卡,他在那里创建了他的建筑和城市设计工作室。
他写道:“建筑是在艺术和财产的交汇点上产生的,这是它如此清晰地记录公共生活历史的众多原因之一。”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遇到了他的妻子,琼·科普耶茨[Joan Copjec],她是布朗大学现代文化与媒介学教授。
在公众心目中,索金作为批评家的形象远超过了他作为建筑师的形象。
我们
现在
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向这位尖刻的纽约批评家学习:他在真理流行之前,就已经向权力道出了真相。
如果说迈克尔·索金从1980年代起不断地打开建筑批评的边界,那么反观国内从那个年代起,每过一个周期就会有人跳出来“批评”国内的建筑批评
乏善可陈、隔靴搔痒、朽木枯株,或者诸如此类的话。不过,这一周而复始持续到当下的对批评的“批评”都已经是老生常谈,差不多也可以成为我们所要批判的对象了。
本次推送
并不期盼国内的环境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变,而是为了指出更为危险的问题:这
种所谓的外部理由
恰恰
已经抽空了人们对建筑批评之所是这一内核本身的批判能力。如果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
建筑批评是太少还是太多,是正确还是错误,而是大部分人想要的真的是建筑批评吗?为什么总是有人要求批评者给出所谓“正确的批评”?或者每一个这样的周期来临,对建筑批评应当如何在自身的语境中发生并没有从认识上做出改变,也根本不是为了
向权力道出真相
,甚至恰恰相反,只是为了服务于权力,或者成为新的权力继续扯谎遮掩?等等等等,那又会怎样?
如果真的如塔夫里在“
只有历史,没有批评
”中所说的那样,在这样一个时
代
更深层次的批评就只能是彻底的历史了,那么人们还需
要“
建筑杂志上靠那些建筑师们,靠那些蹩脚的历史学家搞出来的“
建筑批评么?
或者针对社会中的建造活动本身及其外延,人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批评?或许,我们能从迈克尔·索金的经历中寻到一些新的进路。所以,本次推送除了一段历史的介绍之外,我们还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新的阶段建筑批评应当如何展开的一系列原则。
院外还将陆续推出相关的文章和专辑。

Michael SORKIN|1948年
8月2日
-2020年3月26日



让我们回到迈克尔·索金的1980 年,他并不像那些精英文化的中坚分子,想要成为专给《纽约客[New Yorker]》撰稿的“纽约人”,也没有寄身于那些大牌的报纸名下,而是从《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这样的“小地方”开始了自己的写作。
或许有人会说,毕竟迈克尔·索金那些年才三十出头,四十不到,这个年纪对整个建筑业界来说,只能算是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而已。所以他选择从小做起,
也算不上很奇特吧。
不过,如果考虑到索金之后的经历,那么人们或许就不会轻易地得出这样的论断。作为一位批评家,索金更愿意把当地的、建筑或政治的出版物作为自己的发声地,而且
在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延续着这种模式。
也正是因为这段在《乡村之声》的过往,索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批评风格。那种批评并不只是学院研究的扩展,而是来得恰逢其时,因为那是二十世纪80年代,所谓“里根的纽约”的黄金期,那是
一个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华尔街的疯狂时代。
一旦这场疯狂的运动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就会变得华而不实,粉饰太平。它就像裹满糖衣的炮弹,投向了
曼哈顿的各到各处。同时对于建筑界而言,
那也是一个即便没有文丘里,也会有摩尔,即便没有约翰逊,也会有詹克斯的时代。
再来看看当时的
《纽约时报》都在做些什么吧:他们在为特朗普大厦摇旗呐喊,大唱赞歌。正是从那个时代起,
绅士化的城区改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股
浪潮一直持续到今天,
有增无减
。
一段“黄金期”,也可能是一个“临界”的时刻,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应当出现的时刻。
所以,人们完全有理由把迈克尔·索金的批评想成是应运而生,但他当年的抉择更应被看作是
该出手时就出手
。

出手
1980年代中期
《纽约时报》为唐纳德·特朗普的建造计划喝彩,
索金在《乡村之声》上发表了抨击文章。


除了做出必要的抉择之外,想要成为一位出色的对抗者,必须认清楚自己所身处时代的
紧要环节,还要敢于冲着某些人发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迈克尔·索金对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的作品
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楼)的批评便是如此。这座1980年代中期建成的“后现代”标志性的大楼,红透了半边天,颇
受包括业界学界在内的人们的推崇,而索金当年的评论就极为
准狠
:
说得难听点,这栋大楼烂透了(the building sucks)……用来打扮
AT&T的
所谓"后现代"款式,根本就是粗鄙不堪,以为套上那些刚上市的奇装异服,靠着生拉硬拽的法子,它就不再是同一栋老派的房子了吗?
除了对建筑物本身的批评之外,还
值得一提的是,索金也是最早公开讨论约翰逊过去参与纳粹政治的批评者之一。只要稍微回想一下,约翰逊当年在纽约的文化势力是如何的权倾一方、风光无两,也就不难想象,索金这一揭开了圈内人心知肚明之事的批评,会被不少人看作是冒失的举动。
果不其然,索金的义愤导致的结果是另一些建筑评论界大拿们的强烈反击。《纽约时报》评论家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曾经就此说过一句名言:“(索金的写作)之于深思熟虑的批评,就像阿亚图拉·霍梅尼之于宗教宽容。”
但是,索金并没有因此退却,反倒
愈战愈勇
。
向来偏好带点挑衅的他,
在第一本文集《精致的尸体[Exquisite Corpse, 1991]》出版时,干脆把这句话印在了封底上。正是在这场分别以索金和戈德伯格为代表的建筑派别之间旷日持久的争吵中,索金写下了他最具论辩性的批评。

愈战愈勇
Exquisite Corpse
1991
索金恶作剧地用评论家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侮辱性的话
Was ever a man more preoccupied with getting it up in public?
宣传自己的第一本文集。


索金的写作姿态当然不是出自个人或江湖小团体的意气。他自己将这种
好斗的、公开的社会主义方法进路,归功于一位对他产生过主要影响的思想同道——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这位2013年去世的批评家、也是城市学院杰出教授。众所周知,伯曼写过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文之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1982] 》。
除此之外,索金作为建筑与城市的批评者,与一般意义上的学者最大的也是更为重要的区别在于,他
从生活中不断地汲取着营养。他在那间租金管制的小公寓里度过了数十年,这套公寓一直保留到了2010年代中期。因此,他也目睹了身边的纽约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在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的领导下,而且这些变化的结果往往是越来越糟。
于是,这位从民主党转成共和党人身份的911之后的纽约市长,这位通过修改任期限制法而连任了三届的纽约市长,成了索金经常抨击的敌人。这不是两位差不多同龄的“迈克尔”之间的斗争,而是迈克尔·索金
不知疲倦地倡导
城市权利的过程。
只有真正深入地了解到索金的写作以及这些时代背景之后,人们或许才会意识到,大多数所谓的批评在政治上是多么的中立,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尽管索金针对审美方面的写作,与他自己那些并不太为人所知的设计创作同样的令人愉悦,但很显然,他对建筑的理解已远远超出了审美的范畴。

倡导
1990 年以来曼哈顿无家可归的困境


索金常常会问,究竟谁可以占据(occupy)空间——无论是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往往正是这样的写作才会让人感到紧迫感,而且
比起针对一时一地的审美辨析来,
这种紧迫感就算到了几十年后,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因为其中常常包含着某种希望,某种对行动的呼吁。
2018年他在《发生了啥:城市的是非[
What Goes Up:The Right and Wrongs to the City, 2018]》中写道:
有没有
一种感知的设备,可以将资本主义的城市变成它的另一面,
把它翻转过来,成为真正的 “异轨”?
让我们继续寻找,偶遇陌生人,上演随机事件。
成功总是转瞬即逝的,尝试就是结果,
失败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横穿城镇的每条路线,最终都把你带去麦当劳,那么这玩意铁定是出问题了。
这或许是现阶段一位
好的批评家应当做到的一点,如何
巧妙地描述问题,还要在这种巧妙中不乏幽默。不仅如此,他
还能让人们感觉到问题就在身边,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是可行的,而且这种可行性是在地面上、在街道上或者在占据着空间的普通人可掌握的范围内,可以用来反对所有那些阻碍他们那样去做的诡计和设计。
这些是建筑批评中最难传达,所以也是最该传达的事情之一,因为建筑批评所针对的是艺术中最具空间性和支配性的实践——那是一种常常感觉是在未经人们同意的情况下强加的实践。
索金能够
把建筑与政策、与日常生活、与公园、与麦当劳、与低劣的阿斯彭公寓联系起来,为他所有的读者提供一个可以抓住的立足点,而这一立足点常常是那些能够激发起美国人义愤的对象。这是在
塔夫里声称“只有历史,没有批评”之后,一位优秀的建筑批评人面对城市、建筑物及其周遭的
直接发问
。

直接发问
What Goes up: The Right and Wrongs to the City
2018


索金还是一位技术专家治理的思想者,这是他的另外一面。城市规划和建筑领域的实践经验给了他特殊的权能,让他在撰写有关住房和城市化的文章时,能够做到
既简洁又严谨
。
他对城市化的信念相对较为标准,主张增加绿化和步行区,但他对住房的主张在既有的现实面前,就显得要基进得多。他从来没有忽视过这样一个事实:住房是一项人权,不过通常现如今的建造更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人;建筑不能用金碧辉煌的新外墙来掩盖这一事实;住房政策应当优先地考虑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住房是城市生活中明确的阶级政治的载体。
有关最后一点,在《国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最好的展现。在那篇文章中,索金谴责了在包容性分区政策下为低收入租户在华丽的新建公寓中建造的
“穷人入口”:"城市中分配伦理的理念需要一个分配规划的过程,它不仅包括使用,那是规划传统的关注点,而且还要包括社会准入。当
社会产品的分配进入到
空间领域,棘手的问题就来了”。
他最具挑衅性的构想计划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非建成的巴勒斯坦首都,他还专门以那些激烈的争论和经常受到审查的巴以冲突为主题出版了几本书:《
下一个耶路撒冷:共享分裂之城(2002)》、《反对墙:以色列的和平障碍(2005)》。
2005年,索金还创建了左翼的城市智库Terreform,这一智库致力于城市正义问题的研究,并分发有关分区规划、环保主义、城市更新等主题的出版物。除了在索金工作室和各种教职的工作外,
直到去世前,
他从未停止过写作
。

既简洁又严谨
纽约市建设经济适用房的提案
2019


回到当下,我们仍然可以从索金的写作中学到不少。比如,他告诉我们,一个好的评论家不会担心惹毛别人,也不会害怕对权力说真话,无论面对的是约翰逊、MOMA、布隆伯格、特朗普,还是戈德伯格。
想当年,在对资本主义的赞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响亮的时候,他敢于指出资本主义是所有城市和建筑弊病的根源。这种批判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基进的。然而索金并不止于批判,无论难题的规模有多大,他总是要找寻能够带来希望的关节点,并用它来解释和分析自己所选择的主题。
正是由于他的政治信仰和时不时流露出来的民粹主义倾向,索金的写作并不是为了吸引其他的建筑师,或者其他的评论家的目光。他的杂文之所以有着尖刻的机智、犀利的言辞、激烈而富有挑衅性,是为了吸引所有人,能够切入有关设计和城市本身的辩论,而不是制造障碍。
这种信念也体现在他对出版物的选择上,建筑批评不应被大牌的报纸和学术界把持。或许正因如此,他不可能像许多同样著名的当代建筑评论家那样,得什么普利策新闻奖——问题并不出在索金这一边。
能否被奖项认可并不是最重要的,现实中有不少写作者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发的保守,并逐渐融入到各自领域的各种机构中,但是索金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一如既往地像80年代那样,仍旧是一位好争论的社会主义者。正如评论家约瑟夫·乔瓦尼尼[Joseph Giovannini]在《纽约时报》上索金的讣告中写道:
在他的职业生涯之初,索金因为能对权力说真话而声名鹊起;当他获得一定的权力之后,他继续说真话,就好像他
一直是个局外人
。

局外人
Open Gaza: Architectures of Hope
2021


▶
版权归
译者所有,译
者
已授权发布
。
原文来源
|
Architectural Review
未完待续

▶
部分出版物
▂
1991 Exquisite Corpse
▂
1992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editor)
▂
1993 Local Code
▂
1999 Giving Ground: The Politics of Propinquity (editor, with Joan Copjec)
▂
2002 The Next Jerusalem: Sharing the Divided City (editor)
▂
2002 After the World Trade Center: Rethinking New York City (editor, with Sharon Zukin)
▂
2003 Starting From Zero: Reconstructing Downtown New York
▂
2004 New Architecture with Local Identities
▂
2005 Against the Wall (editor)
▂
2007 Indefensible Spac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National Insecurity State (editor)
▂
2009 Twenty Minutes In Manhattan
▂
2011 All Over the Map
▂
2018 What goes up: The Right and Wrongs to the city
▂
2021 250 Things an Architect Should Know
▂
2021 Open Gaza: Architectures of Ho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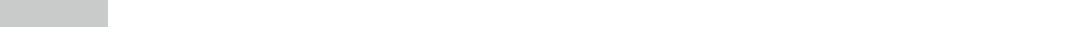

▶
院外
自从2017年4月试运行到2018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推送千余次原创文章,形成五个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

▶
作为激励师生共同研习的方法,各板块的定位不同,形式与进路亦有分担:
BAU学社
探根究底,以“重访包豪斯”遴择同道中人,整饬包豪斯人的文献材料,主持系列丛书的出版,由此推扩到“世纪先锋派”;
星丛共通体
回溯源起,以译介瓦尔堡、塔夫里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文本为重心,毗连上世纪的艺术、建筑与视觉文化研究,置于批判理论的讲读中砺炼;
回声·EG
形与势俱备,从“美学与政治”这一矛盾情境出发,以批评式导读与导读式写作,次第引入空间政治、媒介政治、生命政治,共构审美论域;
批评·家
教学相长,深入个例以梳理历史的特定脉络,转换视角以突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持续组织线上的文本庭审以及线下的共读活动;
BLOOM绽
言与行贯通,以“都市状况”为核心议题,以展示与策动为支撑,辩证地介入建筑、城市、艺术、技术相互联结的当下语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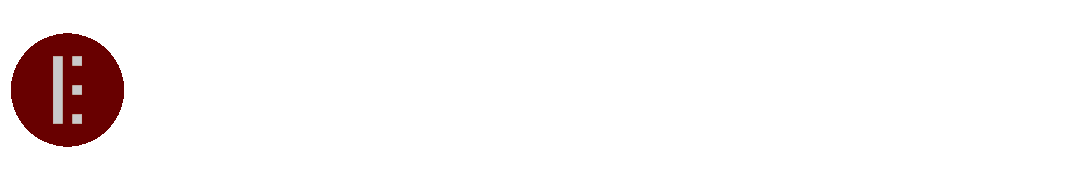

▶
院外计划
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
汇集、
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
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
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
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
这一目标。

▶
星丛共通体
/
回声·EG
|
专题 ▶
辩证能量:瓦尔堡的图像研究与历史想象
|
先锋派,一场世纪对话
|
包豪斯十四年:先锋派的临界点
|
共读 ▷
启蒙辩证法
|
走向新宣言
|
美学理论
|
装饰与罪恶
|
艺术与生产
|
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
|
计划与乌托邦
|
空间的生产
|
帝国与传播
|
理解
媒介
|
地堡考古学
|译-写 ▷
瓦尔堡
|
阿多诺
|
最后的马克思
|
塔夫里
|
后革命与世界体系
|
列斐伏尔
|
现代性与日常生活
|
麦克卢汉
|
生产方式对信息方式
|
居伊·德波
|
排场社会与地理主体
|
技术网络与人器纪
|
朗西埃
|
山寨现代性
|
画讲-图说 ▶
建筑物与像
|
论坛
▶
空间生命政治
|
美学与生命政治
|
美学与政治
|
媒介批判
|
都市魅惑与图像
|
建筑
批判
文献阅读
|
城市危机与空间政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