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明间乡里制度演变的单线条式叙述与阐释,忽略了乡里制度及其演变的北南方差异,以及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族”因素的影响。北南方地区乡里制度的形成及其变化,是以乡村聚落形态差异为基础的:在北方地区,“里”作为行政管理单位,与自然村相对一致;在南方地区,一个“里”往往包括几个自然村,形成地域单元。唐至明期间,北方地区乡村基层管理单位均在“村”的层面,南方地区乡村基层管理单位表现为包括若干村的地域。唐-明间乡里制度变化的总趋势,是以户口控制为基础的唐代乡里制,渐次向以村落、田亩控制为基础的乡村制演变;同时,契丹、女真、蒙古都将其固有的户丁控制制度引入北方汉地乃至全国的乡里制度体系。明代洪武十四年(1381)实行的黄册里甲制,融合北南方两种乡里制度传统,将户丁控制与田亩控制结合起来,而以户丁控制为主。在实行过程中,渐次向以田亩控制为主导演变。

“乡里制度”是由“乡”“里”构成的乡村控制制度。它是王朝国家立足统治需要而建立的、县级政权以下的、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乡村民户与地域的制度。这种制度以最大程度地获取人力与物力资源、建立并维护乡村社会秩序为目标。它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管理乡村社会的制度体系。乡里制度,是王朝国家乡村控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与乡村社会组织及其演变密切联系在一起。
一般说来,有关中国古代乡里制度及其变化的叙述与阐释是单线条式的,即从秦汉为始,止于明清,中国古代的乡里制度呈线性发展变化。就本文所要讨论的中晚唐至明初六百余年间历代王朝所实行的乡里制度而言,其变化轨迹也是如此。隋重新统一中国之后,经过唐初的调整,终于形成了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并由里正共同负责乡政的唐代乡里制度。中晚唐以后,随着两税法的实行,“村”逐步取代“里”成为乡村基层行政管理单位,唐前期的“乡-里”结构向后期的“乡-村”结构转变,到五代时期,乡、村乃成为县司下属的基层组织。北宋前期,在乡与村之间增加了管和耆两个基层单位,并增设户长、耆长。熙宁、元丰变法之后,实行保甲法,逐步形成了都—保制;到南宋时期,又演变为都—图制。金代与元代实行村社制,以五十户为单位,编排村社,设立主首和社长,负责征发赋役和劝课农桑。明初建立黄册里甲制,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管摄一里之事。里构成明代集户口管理、赋役征发与社会治安为一体的社会基层单元。简言之,由中晚唐至明初,乡里制度演化的基本轨迹是:由唐代的乡-里制,经过宋代的都-保制、金元两代的村社制,发展到明代的里甲制。
然而,以上关于乡里制度的叙述与阐释,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首先,它假定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家具有绝对权威,其颁行的乡里制度(以及田制、赋役制等)会得到较全面的实施,从而实现乡里制度及其实行的“一致性”或“统一性”。然而,每个朝代都“制定”并实行符合当时社会情况的乡里制度,所以,各朝代的乡里制度是相对独立的、不连续的。这一假设既夸大了王朝国家的集权力量和权威,又忽视了不同朝代之间乡里制度的异同。实际上,各王朝颁行的乡里制度未必能在全国各地都得到落实。在实行的过程中,各地区也可能因为地方经济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差异而做出调整,即“因地制宜”。其次,它假设中国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基本同步的,乡村社会组织也是同样的,因而乡里制度以及乡村社会组织的演变也是基本一致的。但事实上,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的进程各不相同,与之相适应,乡里制度的演变轨迹也各不相同。特别是在中晚唐以后,直至明初,北南方地区(大致以秦岭-淮河线为界)经历了不同的政治进程,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过程表现出很大差异,乡村社会组织与乡里制度的变化也走上不尽相同的道路。第三,它假设中国古代乡里制度与乡村社会组织及其变化主要是为适应农耕社会生活而制定并调整的。可是,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为北方地区乃至全国的统治带来了若干社会控制的“北族”因素和方式,并凭借其统治权力,将之贯彻实施到乡里制度中,从而影响到农耕地区的乡村社会组织及其演变进程,并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有关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与乡里制度的研究大多是根据不同朝代展开的,得出的认识往往是关于某个特定时段的认识;勉强将有关不同时段的认识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关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及其乡里制度演变的单线条式叙述与解释。所以,本文试图在历史变化的时间维度基础上,加上空间维度,揭示此一较长时期内中国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在乡里制度及其演变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并分析其产生原因。
唐代乡里制度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北方地区村落规模较大,在唐前期编组乡里时,多以自然村落为单位,一个村即编排为一个里;但也有一个里包括几个村,或一个村分成两、三个里的情形。总的说来,唐代乡里制度虽然以户口控制为基础,但在实行之初,北方地区的里与村相对应,形成一村一里的局面。到唐中后期,以户口原则编排的“里”渐次崩解,“村”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县实际上越来越多地直接与村庄打交道。这一变化的实质,是聚落与地域控制的原则逐步取代了户口控制原则。“乡”的功能逐步“上移”、集中到了县衙,“里”的功能又“下移”到了村庄,县与村之间的中间性地域控制环节愈发薄弱,乃至渐趋缺失。两税法实施之后,赋役以田亩为主要根据,户等评定、征纳两税等乡村实务遂以村庄为单位进行,乡-里制逐渐被乡-村制所取代,“乡”又被弱化,“村”逐步取代“里”,成为乡村基层行政管理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
中晚唐、五代、辽、北宋、金时期北方地区乡里制度的变化,首先是围绕“村”展开的。中晚唐以后,北方藩镇逐步强化对于镇市、村店的控制。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规定各村的“有力人户”充任村长,负责征收两税。开宝七年(974),“废乡,分为管,置户长主纳赋,耆长主盗贼、辞讼”。户长按管设置,每管包括若干村;耆长按村设置,多被称为“村耆”。“村”完全取代“里”成为赋役征纳、治安管理的基本单元。北宋中期实行保甲法,以大保为核心,试图将大保建设成为自保、互助、互相监察的基层社会组织。在北方特别是京畿地区,最初规定以五十家编为一大保,后改为二十五家,而北方自然村落的规模大致就在二三十家(主户),五十家(主户)就是很大的村子。所以,大保往往就是按村编排的,一个村就是一个大保,故称为“村保”。
在辽(契丹)统治下的燕云汉地,延续唐中后期华北地区的发展趋势,“村”已取代“里”,成为实际运行的乡村社会管理与组织的基本单元。虽然有的“村”就是由“里”改称而来,但它并非单个的自然村,而是包括若干的自然村。在辽中京、上京以及东京地区,为安置不同来源的迁移人口,建置了城、寨、庄、务、店等居住单位,并同时发挥着社会管理与组织的作用。辽(契丹)在燕云及中京、上京地区设置的寨大抵以统领三百户为标准,亦有领五百户者,其管理的户口规模大致相当于唐代的乡。
寨(“蒲辇”)是金代女真人的居住单位与社会组织单元。女真猛安谋克户以“伍”为最基本的编组单位,十个“伍”亦即五十户编为一个寨。一个女真寨(“蒲辇”)的规模和北方汉人居住的较大的集村相似。金代徙入华北地区的猛安谋克户(包括女真人、契丹人、渤海人等),亦以寨(村)为基本居住和社会管理单位。金代曾试图将女真的寨制推行到华北汉地,县下置寨,以寨统村,寨在行政管理层级上大致相当于唐代的乡与契丹统治下的寨,然其管理的户口则超过三百户。到海陵王时期,以唐代乡里制为基础,结合女真传统的寨(“蒲辇”)制,正式建立起金代的乡里制度:县下仍分置乡,乡置里正,主管户籍赋役帐册,是县役;以五十户置一村社,各置主首,主赋役治安,是乡村职役。金代虽然仿唐制,分置乡、里,然在乡村实际层面上,以五十户编为一个村社,村社主首被认为等同于猛安谋克部的寨使,这样的规定,主要源自女真固有的寨制。换言之,金代的乡村村社制,沿用唐制只是其“形”,女真寨制才是其“实”。
在金代村社置主首的基础上,元代在村社增设社长,主管劝课农桑,从而形成村社主首-社长制。它主要沿用金代的村社制度,但又有所变革。“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无论主首,还是社长,都是以村落为基础、以五十家为单位设置的。主首负责征发赋役,属于职役;社长负责督促生产,具有村庄自治首领的性质。在村庄中同时设立主首与社长,村社在制度上成为北方地区乡村社会的控制、管理与组织单位。
明清时期,随着人口增加,北方村庄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明代的“里”和清代的“保”也大抵以110户或100户为标准编组。但无论怎样变化,村庄一直是北方地区基本的行政管理与社会组织单位,并在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的变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其次,人丁控制一直是北方地区乡村控制的重要方面。它主要表现为对户口的严密控制和对人力资源的征发。在辽(契丹)统治下的燕云汉地,虽然表面上沿用唐代的乡里制度,以五百户为一乡,但实际上是以乡作为征发乡丁的单位,每乡征发一千丁(按户发丁,每户二丁)。所以,乡事实上成为征发、编排乡丁的一种单位。乡丁制度是辽(契丹)征发汉人兵力和劳动力的制度。乡丁就是乡兵,他们在战争时作为辅助兵力参加作战,在平时则作为地方武装维护社会治安,并参与公共工程建设。在辽中京、上京、东京地区,对于迁移而来的汉人、渤海人、高丽人,契丹也主要采取半军事化的社会管理方式。在辽朝前期,对于上述民众,大多设置寨作为安置和管理的单位,每寨三百户。辽圣宗(983—1031)以后,在中京、上京、东京地区又按照五百户、一千丁为一个乡的标准,编排乡、里,而原来的寨制也没有完全废除。这样,就形成了乡里制与寨制并行的局面。无论按乡里编排户口(每乡五百户、一千丁),还是按寨编排户口(每寨三百户、五百丁或六百丁),都是以人丁控制为目标的。
契丹的寨是安置、管理新迁移人口的单位,而女真的寨(蒲辇)则是女真固有的居住单元与社会组织。女真人居住的寨(蒲辇),规模一般在三五十家左右。以寨为基础征发兵丁,每个寨就编为一个蒲里衍(以五十夫为标准),两个蒲里衍编为一个谋克(百夫)。所以,一个五十户的寨(蒲辇),是与由五十人组成的一个蒲里衍相对应的。作为社会控制制度的女真寨制,也是与金代的兵制相对应的。金初在华北汉地推行寨制,也就是试图以这种准军事化的人丁控制的方式管理当地民众。后来虽然改行村社制,但仍以五十户为标准编排村社,其人身控制的功能与目标,实际上得到了延续。
元(蒙古)据有汉地之初,无论城乡居民,均按身丁抽丝,同时按户、丁征收财产税。因此,掌握户口乃成为征收户、丁税的依据。故蒙古据有金国故地后,即进行大规模的户口清查与登记。而检括户口,则必然要以村社为基础。虽然元代建立后赋役制度复杂多变,但总的说来,北方地区的民户赋役,仍当以按户纳税、按丁应役为主,而丁役又往往折纳。户部定例,亦以“户丁税”为称。课税既以户丁为单位,而人户仍就依照居住地原则定籍,故元(蒙古)统治下的北方地区,乃沿用金代村社主首制度,以掌握户口,催征赋役;社长之立,则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的村社组织。所以,在元(蒙古)统治下,对北方地区人民的人身控制,是进一步强化的。
总之,在北方地区,中晚唐以后,“村落”渐次取代“里”,乡-里制逐步演变为乡-村制。北宋时期,多以村落为基础编排耆或大保,以村落控制为中心。辽(契丹)治下的汉地,则以户丁控制为中心,将寨制与乡里制相结合。金(女真)曾在部分汉地州县推行“寨”制,其“村社”制亦与女真“寨”制有密切关联。元代在北方地区实行的乡里正-村社主首、社长制,亦将户丁控制与村落控制相结合,而以户丁控制为核心。所以,中晚唐以后,北方地区乡里制度演变的总体特点乃是以“村”作为社会控制、管理与组织的基本单元,而在“村”内则以户丁控制为基本原则。
为了适应平原水乡稻作农业和山区农林经济的生产与经营方式,南方地区(秦岭—淮河线以南)自然村落的规模一般较小,形成分散居住的状态。因此,当唐前期根据一里百户的规定编排乡里时,南方地区的大多数“里”遂不得不包括若干村落;同时,为了管理的方便,在里正之下,又不得不在一些村设置村正或村长,从而事实上形成乡-里-村的格局。这样,唐代南方地区的乡里制度,从其起始阶段,就表现出与北方地区不同的特点来。两税法实行后,南方地区的乡-里-村制并未发生较大变化,只是在五代时期的吴越国、南唐、闽国一些地区,依托自然村,又设立了保,形成乡-里-保(村)制。此时,包括若干村的“里”一直发挥着基层赋役征收和社会管理单元的作用。
北宋中期实行保甲制,由于南方地区的村落规模较小,较少达到二十五户(主户),更遑论五十户(主户),所以一个大保就可能包括若干村落。按规定,二百五十户编为一个都保,但在实际的编排过程中,往往以原来的“里”为基础,将“里”直接编为“都保”。这样,不仅“里”得以保存下来,甚至形成了整齐划一的“一里十保”的格局。在有的州县,“都保”是在原有“里”的范围内分划的,一个里分划为若干都,每都又包括若干大保,同时,乡的分划仍然保存下来。这样,就形成乡-里-都-保的格局。虽然根据规定,都保、大保都是按户口数编排的,但在实际的编排过程中,大保、都保、里均表现为不同范围的地域单元,而且表现出明显的层级(里-都-保)。有时,“都保正”被称为“都里正”,“都”就直接变成了“里”。到南宋时期,虽然各地情况颇多差异,但较为普遍实行的制度是:乡书手以乡为单位设置,负责编制户口赋役籍帐;都保正、副以都为单位设置,掌管地方治安,兼管催征赋税;大保长(户长)以村落为基础设置,负责具体催征赋役。这就是南宋时期的乡-都-保制。其中,包括若干保的“都”,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唐与北宋前期的“里”。
灭亡南宋后,元代政府试图将原在北方地区实行的乡里正-村社主首、社长制推行到南宋故地。但南方地区固有的乡里控制体系乃是宋制,与北方地区的金制相比,最大的差别就是“都”早已成为实际负责赋役征发的地域单元;同时,保(图)也包括一个或若干个村落。因此,当元代将北方地区的乡里正-村社主首、社长制推行到南方地区时,就不得不做出若干调整:乡里正被乡书手所取代,里正与主首均按都差充(一般每都一名里正,若干名主首),社长则在村落的基础上设立。各都分差的主首可能负责催征若干社的赋役,并不与社长存在对应关系。这样,就形成了乡书手-都里正-都分主首-社长的复杂体系。后来,在一些州县,停差都分主首,又形成都里正-社长的格局。在未停差都分主首的情况下,主首与社长相分离,乃是元代南方地区乡里控制体系不同于北方地区的明显特征;停差都分主首后,社长的作用大为突显,兼括了都分主首实际负责催征赋役的职能,却又与北方地区同时设置村社主首、社长不同。而无论是否轮差都分主首,均置有都里正。所以,在南方地区,乡村控制体系一直是乡、都、社三级,不同于北方地区的乡、村社两级。
总的说来,南方地区的里、都、图、社包括若干个自然村落,是范围大小不同的地域单元。通过控制大小不同的地域单元,实现对乡村地区的控制,是南方地区乡村控制的基本原则。而地域控制的核心,在于田亩控制。
田亩控制根源于两税法。根据两税法,征发赋役均以人户的居住地和其所耕作的田亩为主要根据:征收赋税和差科,原则上是根据人户所耕作的田亩及其拥有的其他资产;评估各户的资产,确定其纳税等第,则需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换言之,官府必须控制村落,掌握其所耕作的田亩,才能征发赋役。而在南方地区,由于居住分散,毗邻自然村落耕作的土地往往交错在一起,很难按村落分别开来,所以,确定田亩归属、评定户等、确定各户的纳税额,就不得不在“里”的层面进行。在南方地区,一个“里”大多包括若干村落及其田地,构成相对稳定的经济与社会单位(与此相对照,在北方地区,是“村”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这样,以田亩控制为中心的地域控制原则就逐步取代户口控制原则,成为南方地区乡里制度的基本原则。
北宋中期实行保甲法,试图重建户口控制原则。可是,在实行过程中,保甲法的户口控制原则也不得不逐步适应两税法按田亩征发赋役的原则,从而使都保、大保逐步由户口控制单元,演变为地域控制单元。至南宁绍兴十二年(1142)起在部分州县渐次推行经界法、按都保丈量土地、按乡均定两税。由于田亩图、帐均按大保编制,“每保画一图,凡田畴、山水、道路、桥梁、寺观之属,靡不登载,而以民居分布其间,某治某业,丁口老幼凡几,悉附见之”,遂以“图”指称大保所辖地域。这样,都-保制遂在部分地区演变成为都-图制,都、图(大保)作为地域单元的性质乃更为突显。
元代南方地区的里正、主首大都按“都”设置,“社”则多根据“图”(大保)设置,一般也包括几个自然村。由于社长既负责催征赋役,又负责维护当地治安,在图的基础上设置的“社”就越来越具有地域性社会单元的意义。同时,在共同承担赋役、共同维护水利等过程中,都内各社、村之间也逐步加强内在联系,其地域性质不断得到强化。
总之,在南方地区,中晚唐以后,乡-里制较稳定地保持下来,并在宋代,与保甲法、经界法相结合,演变为乡-都-图(保)制;至元代,又与村社制相结合,演变为都里正-都分主首-社长的控制体系。里、都、图、社,都是地域性社会管理单元。所以,此一时期南方地区乡村控制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地域控制。继而在地域控制的基础上,以期实行田亩控制。而田亩控制的根本目标,是实现赋役征发。
在明代建立之前,朱元璋就曾实行“给民户由”的制度。洪武元年(1368),诏令“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计,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得妄行变乱”。它规定民户要遵从元朝对其身份的界定,不得改变其户籍的性质。此后,更全面推行户帖制度,每户给以户帖,各书其户之乡贯、丁口、名岁、事产。“给民户由”与户帖制度重在掌握户口(“稽民”),其制度渊源显然是元朝在北方地区更为严格地推行的户丁控制制度。同时,为了征发赋役,从洪武元年(1368)起,首先从浙西开始,进而全面核查天下土田。鱼鳞图册就是在核查田亩的过程中编造的。“集里甲耆民,躬履田亩,以量度之,图其田之方圆,次其字号,书其主名,及田丈尺四至,类编为册。而所绘若鱼鳞然,故号鱼鳞图册。”核查田亩、编制鱼鳞图册,根据田亩以征发赋役,则显然是沿用南宋以来南方地区田亩控制的做法。
洪武三年(1370)前后,部分州县实行“小黄册”之法。“每百家画为一图,内推丁力田粮近上者十名为里长,余十名为甲首,每岁轮流里长一名,管甲首十名;甲首一名,管人户九名,催办税粮。”小黄册之法,按照户口编排里甲,十户编为一甲,十甲、一百户编著为一里;而一个里的民户所耕作田地的鱼鳞图,又编集为一本图册。这样,“里”是包括一百户的户籍编排单位和赋役征纳单元,而“图”则是包括一百户居住的村落及其耕作土地的地域。一百户编成的户籍单元的“里”,对应着包括一百户人家耕种田亩的地域单元的“图”,二者实际上是合一的。
洪武十四年(1381)所行黄册里甲之法,是对小黄册之法的继承与改进:规定每里一百一十户,选其中的十户作甲首,甲首轮流作里长。虽然有这些不同,但二者编排里甲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都是“以人户为主”。“国初编审黄册,以人户为主。凡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长之就役,以丁数多寡为次。是赋役皆以丁而定,丁之查覆,安得不明也。”赋役以户、丁为定,是元代在北方地区实行的制度。以人户之多少而制为里甲,以粮从户、丁,正是从元代北方地区实行的制度加以改动而来。所以,黄册里甲之制“以人户为主”,系粮于户丁,当本诸元代北方之制。同时,为了切实地掌握田亩,又沿用并改造南宋以来南方地区的做法,将耕地系于家户之上,编制鱼鳞图册。里甲制使官府得以掌握户丁,可以通过里甲征发力役;鱼鳞图使官府得以切实地掌握耕地,知道每户人家耕作的田地有多少、在哪里,可以根据鱼鳞图册,找到户主,征收田税。黄册里甲与鱼鳞图册相辅相成,构成完备严密的乡村控制与赋役征发体系。
总之,黄册里甲制以户丁控制为核心,主要沿用了元代在北方地区实行的制度;鱼鳞图册以掌握田亩为核心,主要沿用了南宋以来在南方地区的做法。明代政府将户丁控制与田亩控制相结合,将户丁固定在田亩上,田亩系于户丁上,实现对民户、田地的全面控制。所以,明代的乡里控制制度融汇了北南地区两种乡村控制的传统模式,使中晚唐以来分途演进的两条乡里制度演变轨迹又重新回归到一起。
明初设立的乡里制度看起来周密完善,但在实行过程中却发生了诸多“因地制宜”的变化,其后来的演变进程也各有差异。南方地区(秦岭-淮河以南的南宋故地)的里甲体系是在南宋以来乡-都-图体系的基础上改造、编组而来的。如浙江金华府浦江县在元时分为七乡、四隅、三十都(当沿自南宋制度),“洪武十有四年,定图籍,隶于隅都。民以一百一十户为一图,共图一百六十有六,每图设里长一人,十年一役。”其四隅及三十都各领有若干图,如一都,在县东十里,洪武十四年编为九图(嘉靖初并为五图)。显然,洪武十四年编排的黄册里甲是在宋元以来都-图制的基础上略加调整而形成的。同时,浦江县还实行了都保制:“县共三十都,每都设都长一人。每都各分十保,保设保长一人,专管田地山塘古今流水类姓等项印信文册,防民争夺。”都-保制与都-图制并行,但“保”并不与“图”相对应。实际上,因为保长负责丈量田亩、造作田土流水文册,其作用当比轮年供役的各图里长要大。《浦江志略·册籍》称:
洪武十有四年,造田土流水文册(共三百四十册,内开每都佥都长一名,保长一十名。每遇造册之年,照号挨踏入册,图画田地山塘段样,开载原业某人、今业某人及米麦科则数目,庶毋隐漏飞诡,查明,方上四截文册),田土类姓文册(共三百四十册,随流水编造,如一都一保,田土不拘另籍,或张姓李姓选作一处,以便考查)。
都长,当即宋时都保正长、元时都里正之延续;每都分为十保,也正符合宋时保甲编制的原则。所以,虽然实行了黄册里甲制度,但在浦江县,仍然是以田亩为主,而宋元以来一直实行的都-保制则在实际上发挥着主要作用。直到正德七年(1512),浦江县才全面造作赋役黄册,共一百零二册。“内开各图丁粮高上之家,编为里长;丁粮稀少之家,编为甲首。每一图共一百一十户,十年内一轮里甲,一轮均徭。”同时,造“田粮四截文册”,“共一百零二册,内开田粮旧管、新收、除、实在数目”;并重造田土流水及类姓文册,“各一百零二册”。显然,正德七年所造田粮四截文册、重造的田土流水及类姓文册,是与赋役黄册相配套的,诸种册籍各为一百零二册,说明它们是以“图”为单位编制的。因此,虽然明代的里甲编排根据制度规定是以户口为基础的,但在南方地区实际的编排过程中,仍然沿用了南宋-元以来形成的都-图体系,特别是以作为地域单元的“图”作为基本编制单位。
而在北方地区,明初编排里甲,原有的土著民户大都是以金元以来的“村社”为基础的;新迁入的移民,是按照屯地编排的。《明史·食货志》云:
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亩广,屯民新占亩狭,故屯地谓之小亩,社地谓之广亩。
河间府河间县新旧户3073户,编户二十七里,分别是东南隅、西北隅、尊福乡两图、青陵乡三图、儒林乡三图、安乐乡二图,以及柳洼屯、黄家务等十五屯。献县、阜城、交河、景州、东光、故城、沧州也都是乡—图编制与屯制并存。显然,乡-图(里、社)是“旧民”(土著)的编制,而“屯”则是“新民”(迁民)的编制。里社与屯分别是“旧民”与“迁民”的户口编排单位,却未必都是独立的聚落单位。有的屯单独建立聚落,从而与里、社分开;也有的屯所属的“迁民”散处于“旧民”居住的区域内,故与“旧民”的里、社交织在一起。霸州有三十一个里屯(在城三坊,辛店里等里十七个,瑞麦屯等屯十一个),其中瑞麦屯有栢木桥、丰台两个村,永义屯有双堂村、谭家庄两个村,临津屯有长屯、王家庄两个村,登家屯有长屯、沈家庄两个村,居住比较集中。而同样由迁民编排的丰盈屯在城中乡第三图,思贤屯在城中乡第二图;而城中乡第二、三图都是由旧民编排的。换言之,丰盈屯、思贤屯的移民,实际上是分散居住在土著居民的区域里的。在武城县迁民所编的十八屯中,大兴屯即“无屯,民皆散处”,也就是说大兴屯的“迁民”没有自己单独的聚落,而是分散居住在旧民区域。因此,在北方地区,无论里社还是屯都是编民单位,却未必就是聚落单位。换言之,明初北方地区编排里甲时,虽然“旧民”主要沿用金元以来的村社体系,但由于大量的“迁民”是严格按照户口编排并“插入”旧民居住的区域里建立“屯”,势必在很大程度上打破“旧民”固有的村社系统,户口归属于里或屯,意义远大于其居住所在的村落。
总之,虽然明初制定的乡里制度,将中晚唐以来分途演变的南北方乡里制度重新融汇为一体,建立起户丁控制与田亩控制相结合的乡里制度,但在具体的实行过程中,南方地区仍多“参验田粮多寡,不专论丁”,“不得不觭重田亩以佥派里役”,即“以田定差”“于是黄册之编审,皆以田若干为一里,不复以户为里”;而北方地区则多“以丁定差”,“故时诸州县唯籍丁为九品,而不计其田,里胥稍得狐伏鼠没其间,而贫弱不堪,往往因而亡徙”,直到嘉靖以后,北方地区“始仿以田准丁、以丁准田之法,相配行之”。
有关“唐宋变革”以及“宋元明过渡”的讨论,涉及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诸多重要领域,特别是人口的增长与迁移、经济发展及其结构变动和区域差异、政府组织及其功能的变动、政治与社会精英的转型,以及精英思想的转变、大众观念与文化的变化等。可是,对于同一时期作为中国及其社会经济体系之主体部分的乡村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却缺乏通贯性的研究。所以,迄今为止,仍很少有学者能够给出清楚的回答与阐释。本文在此前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中晚唐至明初600余年间乡里制度的变化展开讨论,试图去回答:在学者们讨论的“唐宋变革”或“宋元明过渡”中,乡村社会及其控制方式究竟是怎样的;在这一过程中,它们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学者们所揭示的诸多重大政治经济与社会以及思想文化变化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首先,中国古代北南方地区乡里制度及其变化,是以北南方地区乡村聚落形态的差异为基础的。当唐前期按百户为里、五里为乡编排乡里制度时,在北方地区,由于村落规模比较大,作为基层行政管理单位的“里”与自然村相对一致,一个村往往就设置一个“里”;而在南方地区,由于村落规模较小,一个“里”往往包括几个自然村,从而成为地域单元。中晚唐为始,止于明代,无论历代王朝制定怎样的乡里制度,当其实行时,在北方地区,村落都是编排其乡村基层组织的基本单位;在南方地区,无论设置怎样的基层管理单位,一般都包括若干村。换言之,北方地区的乡村基层管理单位具体落实在“村”,而南方地区的乡村基层管理单位具体表现为包括若干村的地域单元。从政府控制与管理的角度看,前者更易于实行集中管理,而后者集中管理的难度就比较大。所以,历代政府总是不遗余力地推行便于集中管理的北方模式。
其次,中晚唐至明初,乡里制度演变的基本轨迹是,乡里控制的原则,从户丁控制逐步向田亩控制演化,最后将户丁控制与田亩控制结合起来,“以田准丁,以丁准田”。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制定并实行乡里制度,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征发赋役,二是治安监控。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又主要有两种办法:一是掌握户、丁,控制民众的人身;二是掌握田地,以及其他民众生产与生活必须依靠的资源。前者官府可以按户口编排乡里,后者官府可以根据居住地、田亩征发赋役。具体而言,历代王朝的乡里制度原则上是以户口编排为起点的。这种编排原则及其实行策略必须以严密的户籍控制为前提。可是,受到民户逃亡、豪强荫蔽强占以及隐冒户口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王朝国家对于乡村民户、丁口的控制往往随着国家控制力的衰退而松弛。由于社会动乱、人口迁移等原因,越来越多的民户脱离原先生活的村落和居住地域(脱籍),使官府无法再依靠固有的乡里控制系统征发赋役。凡此,引发了乡里编排的基本原则由户口原则向居住地或田亩原则转变,即不再以户丁为基础,转而主要以居住地(村落)或耕种的田亩作为征发赋役的根据。由此,以户口控制原则为基础的隋唐乡里制,渐次向两宋以村落、田亩控制为基础的乡村制变化,是唐宋时期乡村控制制度变化的总趋势。这也可以看作“唐宋变革”在乡里控制体系上的表现。可是,田亩控制原则虽然便于征收赋税,但并不利于政府掌握人丁,征发力役和兵役,也不利于建立并维护社会秩序。所以,在明代建立过程中,即通过户帖制度不遗余力地强化对户丁的控制,并最终以黄册里甲制重新确立了户丁控制原则。明初的这一重大变化,虽然可以溯源至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统治下在华北地区的实行的乡村控制制度,但其变化方向与所谓“唐宋变革”的方向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宋元明过渡”,不应视作“唐宋变革”的沿续与发展。宋元明时期社会经济的演变,有着更为复杂的成因,各有历史根源并表现出不尽相同的发展方向,绝不是沿着唐宋以来的历史线索单向前进的。而在明代里甲制度实行之初,南方地区较多地沿袭南宋-元以来的“都-图”制,并“参验田粮多寡”、“不专论丁”,后来更渐变为以田亩作为佥派里役的根据,编审黄册里甲皆以田若干为一里,而不复按户编里;在北方地区,虽然在明前期唯重户丁,不计其田,但到明中期以后,也不得不仿行南方地区的做法。凡此,都说明虽然颇历波折,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仍然是从户丁控制向田亩控制演进。
第三,户丁控制不仅与北方地区集中居住的乡村聚落形态较为适应,更是“北族”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在此一时期内,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都将其固有的户丁控制制度引入北方汉地乃至全国的乡里控制体系,特别是金代以五十户为一寨的制度,编排华北汉地民户,建立村社制度,又为元代(蒙古)所沿用,彻底改变了汉唐以来以百户编为一里的制度。其村社置主首、在元代又增设社长的做法,均进一步强化了对村社民户的直接控制。辽(契丹)在汉地按户征发乡丁,金(女真)、元(蒙古)按户签军,以及按户丁征发税役等,都是以户丁控制为基础的。这些因素,均不同程度地被明代所继承。明代建立的黄册里甲制,实际上来源于元代北方地区实行的村社制和户丁制,故而可以将明代黄册里甲制的建立称作乡里制度的“北方化”,甚至是“北族化”。在“北族传统”影响下的乡里控制的“北方模式”,更重视对于民众的人身控制,以及对其劳动力资源的利用。这种控制方式既与北方地区集中居住的乡村聚落形态相适应,更与较强的政府控制力相配合。与之对应的是,乡里制度的基本原则由户丁原则向村落、田亩原则的演变,渊源虽是南方地区散居状态下掌握户口较难、掌握实际居住地与耕作田亩较易,但王朝国家控制力的衰退仍然是最重要的原因。正因如此,我们将乡里制度的基本原则由户口原则向村落、田亩原则的演变概括为古代乡里制度的“南方化”。显然,乡里制度的“北方化”意味着王朝国家强化了对民众的人身控制,而“南方化”则意味着王朝国家更重视对民众田产的控制,亦即财产控制。
总的说来,户丁控制与集中居住、集中管理相适应,可以看作乡里制度的“北方传统”,其对于乡村的控制更侧重于乡村的人力资源;田亩控制与分散居住、地域管理相适应,其对于乡村的控制更侧重于乡村的物力资源(应征的力役往往折纳为钱物),可以看作乡里控制的“南方传统”。在“唐宋变革”时期,南方传统逐步占有优势,乡里制度的变化表现为“南方化”;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的统治,使北方传统在“北族”的影响下增加了新因素,并在明初占据了主导地位,进而使元明间乡里制度的变化表现为“北方化”。北方传统与南方传统,北方化与南方化,分别代表着中国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和两个方向。中国历史的发展与演进,就是在不同的区域性传统(特别是北、南方传统)相互竞争、纠结、冲突、调适、整合过程中逐步展开的,并不表现为单一的路径和一致的方向。
原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作者简介:鲁西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北大医学部教授:如何活得长、病得晚、老得慢、死得快?
东亚巨变500年——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与现代世界的关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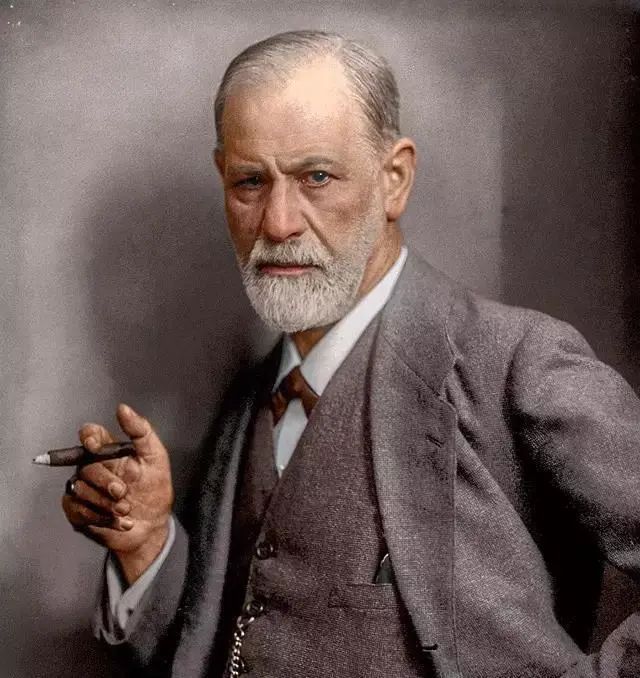
梦见坠落、掉牙、被追赶……这10种梦隐藏着你的哪些秘密?
| 
从《诗经》到《红楼梦》:10位复旦顶尖教授带你读50堂国学经典课 《统一与分裂》之后,葛剑雄又提供了哪种看懂中国史的方法? 葛剑雄:读懂人口,才能读懂中国历史 葛剑雄:读懂人口,才能读懂中国历史
西方政治史上最重要的 25 本书,都在这里了
诺奖得主揭晓背后,人类的终极问题是什么? 周濂·西方哲学思想100讲 
20世纪思想的启示与毁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