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阿信要为你带来一篇能让你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行深度思考的好文。
文章整理自1月份,《日常的深处》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王小伟
在一席所做的演讲,他说:
我时常觉得哲学就是如鲠在喉,持续地制造不适感、他者性和否定性。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主义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解决生活中全部的问题。但哲学可以使我们在当下的日常当中保持开放的向度,这一点至关重要。
以下,是王小伟老师《一个哲学视角的日常审查》的文字精华摘编。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在一所大学里讲
科学技术哲学
。

为什么要从技术哲学的角度来追问我们的日常呢?因为我们面对的是
一个深度科技化的时代
,
技术已经沉降到生活的诸多方面,我们的言谈举止各个方面都受到技术的中介和调节。这个时候去反思技术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现象,就变得尤为重要。
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技术现象:
通勤、外卖和手机
。手机大家一定会认为是一项技术,对于通勤和外卖,很多人会觉得这根本就不是技术。
实际上现代通勤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复杂城市建设系统,以及地铁、汽车等现代交通技术的基础之上的。外卖更是这样,依赖于精细的食品加工业,再通过一套非常复杂的物流系统,才可以送到大家的手里。
所以通勤和外卖都是一个复杂的技术系统,但因为它们都成为了日常,以至于很多人会认为它们不是一项技术。在我看来这正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很多技术沉降到生活的基层,以至于大家几乎忽视它们也是一项技术,正在改造我们的生活。
《日常的深处》
点击图片,一键下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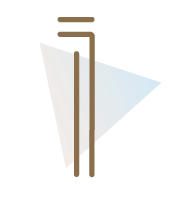
通
勤
:
一种无意义的损耗
这是
一个典型的北京早高峰的情况,
我经常就处于这样拥挤的人群当中。身处早高峰,我感觉人从来不是以一个个性化的形象显现的。一眼过去,看到的是乌泱乌泱的人群,个体性是完全被擦除的。

在通勤的过程中,我时常会觉得自己特别像一只蚂蚁。有时候我会停下来反思,我为什么会过上这种生活?
但是蚂蚁是不会反思自己的生活处境的。所以当我有时候在地铁当中排队发呆,检视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是一只不太称职的蚂蚁。
通勤对人的损耗是十分巨大的。首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通勤当中变得特别微妙,
拥挤和排队会让人处于一种敌视状态
。这个时候群体不再是一种温暖的存在,而是处于一种竞争状态,我们要和周围的每一个人比拼,以最快的速度钻到地铁里去。
另外,通勤把行走变得特别单调,
只有起点和终点是有意义的,而它的过程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损耗和需要去忍受的成本
,
我们要尽快地走完这段路
。
我最近看到一个2022年的研究,调查了北京1500多名通勤人士,虽然样本量不是太大,但是有一些发现我觉得是值得和大家分享的。这项调查发现,在一定时长基础上,每增加10分钟通勤时间,罹患抑郁症的比例就增加1.1%。

▲ 社交媒体上关于极端通勤的讨论
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通勤对一个人的情绪和生命的损耗是十分剧烈的,每个人每天都在付出巨大的精力和人格力量去对抗这种损耗。
那我们就要追问,通勤是如何成为一种可能的呢?一种回答是因为单位没有宿舍,郊区的房租比较便宜,市中心的生活成本实在太高了。
但是追问不能停在这个位置,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哲学提问:
在生存意义上,我们何以要忍受这样的通勤呢?
有一位法国哲学家叫
列斐伏尔
,他提出了“
日常批判
”的概念,
可以为我们理解人通勤提供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角。

▲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
列斐伏尔认为要更好地理解现代
社会人的异化,就不应该再在马克思所批评的工厂的语境里去观察。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工厂时代了,我们的时代已经变成了一个通盘的消费时代。
城市的核心不是工厂,而是消费场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注意力
从对工厂盘剥的批判转移对日常消费生活的批判
里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代通勤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整个城市的生活都已经充分消费化,现代城市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消费空间。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占据城市核心地位的东西,就会注意到我们全部生活的内容都变得消费化了,所有的关系都变得商品化了。原先属于日常生活的低货币需求,现在都变成了货币化的需求。
在七八十年代,如果你去问一个工人什么叫通勤,他是不知道什么叫通勤的,因为那个时候不存在通勤。
北京的城市区域过去聚集了很多生产性劳动场所,它们旁边通常会配套宿舍。而宿舍不是商品化的,它是分配的。所以那个时候,城市的核心是工厂和宿舍,它们没有货币化。
《日常的深处》
点击图片,一键下单
▽

而在今天,城市的核心是高档消费场所,是各种繁华的商圈。你可能会说,办公楼和住宅不是消费场所,但它们是大宗商品。办公楼需要租售,你买的房子叫商品房。
所有原来属于生存领域没有消费化的无需通过货币丈量的生存内容和生存空间,在整个城市变成消费橱窗的情况下,就变得货币化了,成本变得特别高。
同时,
科技和资本会形成一种共谋
。技术的进步使得社会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小商品和稀奇古怪的新鲜科技,每个人每天的注意力都在各种购物软件上。大家会觉得去消费这些东西就是过上一个好生活的指征,进而逐渐把自己的生活完全锚定在消费上,而忘了在消费之外,我们还有别的生活处境。
作为消费者的我可以每天出入这些场所,而作为真正的人,我回家的时候,我要走到城市的边缘,要走到郊区去。
但是我又没法真正地融入乡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乡村,它的田园、自然以及生机勃勃,已经完全被要素化,变成了农家乐,大家也需要通过购买才能获得这种田园体验。
乡村和城市都已经完全消费化了,用韩炳哲的话来说,本来乡村生活是作为城市消费生活的一种否定性、异质性的存在,它是一种关照。但现在乡村变成了农家乐,
从城市到乡村的过渡变得特别平滑,而这是一种有害的平滑。它会造成同质化,使我们丧失想象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维度,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狭窄。
当然大家可能会说,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不完全是列斐伏尔所批判的那种状态,只是有一些相似。现在的城市也在做一些对抗,我们有安置房、共有产权房、经济适用房。这些实践都是在和城市作为消费空间的现实进行一个非常有力的对抗,要把生存领域继续插入城市的中心,我想可能慢慢地会做得越来越好。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尤其是对我自己来说,每天在挤地铁的时候,我会知道道路可以不是用来通勤的,生活不一定非要消费。
通勤可以不是枯燥的成本,行走本身并不关注起点和终点,行走的过程也可以是一种生活。
我觉得这个维度还是要保留。
经过漫长的通勤,你到公司忙了一上午。到了中午,你可能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叫个外卖得了”。不是所有人单位都有食堂,也不太有精力自己带饭,大多数办公室的白领到了中午几乎就只能叫外卖。
而你叫的外卖大概率是一个料理包。料理包被工厂生产出来送到餐馆里,店员把这个料理包加热,由外卖员送到你的手里,最后你坐在工位上吃完这份料理包。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挺焦虑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老吃外卖不健康。或者有时候你会觉得外卖实在太难吃了,你就想出去吃改善一下伙食。
于是你跋涉到一个商场里,点了份糯米鸡和烤鱼。这个时候后厨会打开特定品牌的预制菜料理包,加热完之后端到你的桌上。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现代人有一种特别琐碎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在家、在公司或者在商场吃外卖,但本质上我们吃的都是料理包。
它是一种自由,却显得无关紧要,
这是现代人一个非常荒诞的处境。
我有时候会在
想,外卖这么难吃,为什么大家还要吃?当然生活性的解释肯定是时间不够,工作太忙了只能吃外卖。但
是我们还是需要去想一想,
外卖成为可能,那个最为一般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德国哲学家
马丁·海德格尔
对于技术的观点,我觉得对于我们理解外卖是有好处的。他说
现代技术的本质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存在方式,
这种存在是我们每个人要承受的。
▲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这种存在方式是把一切的存在者都当作一种“
持存
”。什么叫持存呢?简单地说,就是把持一个东西,然后任意地去取舍、摆弄它。把每个存在者都看作是无关紧要、没有内在价值的,可以被随意地摆弄的。
我们可以通过水车和水电站来更好地理解持存这个概念。海德格尔认为左边的水车也是一项技术,但它不是现代技术,是前现代技术。
这个技术没有把河流持存化,尽管水车也把小河当作动力,但它不会改变小河的流向和生态。从远处望去,小河仍然是富有诗意的存在。
但是水电站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水电站会把上游的水位抬高,会淹没千顷良田,会有很多人的家面临着搬迁,而且下游很多小的支流会断流。
这时候水电站就把小河完全变成了一种可以随意摆弄的东西,小河的内在价值和诗意完全丧失了。小河被持存化了,小河什么也不是,小河就是推动水轮的动力。
在现代社会,我们面临的就是
人的持存化
。在现代技术的逻辑下,人被看作标准件,在座各位还有我,我们随时都可以被替换。我们没有内在的尊严和价值,我们吃东西就是为了别饿着,不断地输出劳动力。
与此同时,
食物也变得持存化
。既然人都无关紧要,食物也就无关紧要了。食物只是填饱肚子的营养物质,只是卡路里。
食物的最高级持存化的形式是变成香精。所以大家走进一家饮料店,里面有很多瓶瓶罐罐,装着香蕉口味、菠萝口味、芒果口味的香精。你看不到这个味道的样子,你只能看到香精。
当人和食物都变得无关紧要的时候,食物才会显现为外卖。
每当你的母亲看到你每天吃外卖的时候,她会觉得你不爱自己,没有把自己当成人,你把自己当成一个无关紧要的东西,但是
吃饭这件事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
有一位哲学家叫
伯格曼
,他把我们生活里面的所有事物笼统地归为两类,一类叫
焦点事物
,一类叫
消费事物
。
▲ 美国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
消费事物就是吃外卖,焦点事物就是每个人应该投入巨大精力关注的事物,
它需要我们进行关系性投入,而不仅仅是个人消费
。
什么叫关系性投入呢?大家看这张照片,这是一张80年代家庭聚餐的照片。
桌子上的食物和外卖的差别不在于多寡,而在于这一桌一定有人付出了很多辛劳,有人买菜、择菜、洗菜、做饭,一家人有老有少,亲朋好友围坐一桌,所以这张桌子上有一种很浓郁的人情味。
人和人之间是通过特定的关系连接在一起的,这种关系性的投入是构成食物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这在外卖当中就被完全丢失了。
当然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坐在这张桌子上可能会感觉如坐针毡。这么多亲朋好友在一块,会有很大的社交压力,有时候这种关系性投入让大家感觉到的更多是负担。
▲ 春节期间,年轻人“断亲”话题再次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我自己要回家跟这么多亲朋好友一块吃饭,我肯定是不作声的那位。因为他们又会问我有没有评上某某奖,我会觉得压力很大。
讲到这我有点心虚,因为我知道会引起争议,但是大家注意,你之所以会觉得关系性的投入压力大,按照韩炳哲的说法,是因为你完全接受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承诺。
这个承诺有两句话,大家看着会非常眼熟,甚至会觉得很温暖。第一句叫“
你开心就好
”。当你遇到很多挫折,面对很多抉择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你开心就好”,你可能就会被暖到。
在关系性投入当中,之所以觉得别人的关心和问询是一种压力,是因为你买了这句话的账,你觉得自己开心最重要。你对这种关系性的交往没有兴趣,觉得它是负担。
但韩炳哲会说,如果你不断强调以个人欲望满足、以个体开心为主的这种生活方式,你就会滑向自恋,而自恋会导致焦虑、抑郁、空心、乏味以及倦怠。
这个承诺的第二句是“
只要你努力就会更好
”。这样我们才能容忍每天吃那些无关紧要的食物,因为我们脑子里想象着一个更好的自己。在你内心深处可能会觉得,如果我今天不把自己当个人,那未来我就可以成为人上人。
但是韩炳哲提示我们,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老觉得“只要你努力就会更好”的话,你就掉入了新自由主义的暴力陷阱。
暴力的拓扑学大概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你不服从消灭你,这是暴力赤裸裸地展开。第二个阶段,你不服从监视你。
而第三个阶段就是你不服从,我就告诉你“只要你努力就会更好”,让你
自我规训
。你可以,你行,你只要忍受当下的无关紧要以后就可以更加成功,而我们都是买账的。
可能大家听到这段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么多年可能你听到的更多是“你开心就好”。所以我刚才不断地在强调这些是韩炳哲的观点,因为我不想让大家觉得这是我的观点,我压力非常大。
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承诺在今天一定程度上是破产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感觉到那么幸福,甚至有时会感到抑郁、焦虑和空虚。
我时常觉得
哲学就是如鲠在喉,持续地制造不适感、他者性和否定性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主义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解决生活中全部的问题。但哲学可以使我们在当下的日常当中保持开放的向度,这一点至关重要。
《日常的深处》
点击图片,一键下单
▽

吃完外卖,忙了一下午,回到家里后,你可能会遭遇第三种技术现象——手机。手机在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绑缚。我们老觉得手机在挟持自己,有的时候有很强的粘滞性,我们没法摆脱它。
伯格曼提出一个概念叫
装置范式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概念来审视一下手机。伯格曼认为现代技术和原来的技术之间是有巨大差异的,100年前的技术的核心状态是机器在工厂里轰鸣,而现代技术的特点是小巧化,全部变成了微小的装置。
手机是一个典型的装置范式,
它是一个黑箱,把复杂的功能都隐藏在背后,排斥人对它的凝视。手机仿佛是一个幸福世界的开关,只要你拨动它,所有的便利就会涌入你的现实生活当中。
有时候我问我家的小朋友,食物从哪里来?他说,食物是从冰箱里来。我又问他,暖气从哪来?因为我经常用手机交地暖费,所以他说,爸爸,暖气是从手机里来。
伯格曼认为,
虽然手机这种装置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是它丧失了一个身体性的向度,它割除了生活当中所有的操劳。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刚才说的用手机买暖气和用壁炉取暖的区别。
我们没用过壁炉,但应该都用过炉子。用壁炉取暖是非常麻烦的,你要走到幽深的森林当中去选择合适的树,然后你需要劈砍、堆垒、晒干、引燃。
经过一天的劳作,你把壁炉引燃之后,坐在沙发上,妻子在旁边打毛线,孩子在地板上玩具,家猫蹲在旁边取暖。看着炉子里的火,再看着外边漫天的白雪,它们互相加持,寒冷更加寒冷,温暖更加温暖。在那个空间,人和人之间是联系起来的,围绕这个炉子我们可以构建非常丰富温馨的家庭情境。
但是如果你用手机交地暖费,然后全家人一起在地上玩手机。这个感觉就不对,肯定是哪出了问题。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
手机这个装置正在让整个世界完全地地暖化
,所有的幸福快乐都可以通过手机来购买和调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