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真。原题:谁来重建检察院的“男厕所”?——反贪反渎并入监察委员会后的民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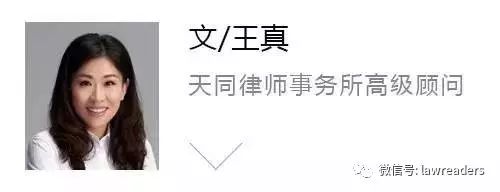
前段时间网络疯传一篇《据说检察院以后会拆掉男厕》文章,讲的是随着改革向深水区推进,检察院反贪部门并入监察委员会似已成定局,几个试点省市在春节前就要完成职能交割和人员全部转隶。
检察院内部无疑会将更多目光投向民事行政检察,学界也将检察发展的视野投向这一领域,马怀德教授称“我认为检察院在民事行政检察、公益诉讼等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很多事情。”
一、悲观还是乐观?
系统内部,对民行的发展甚至“存亡”,一直有悲观和乐观的两极估计。
笔者对此有三个估计:第一,历史的看,民行检察监督是中国法治进程“过渡期”的特殊产物。第二,长期的看,这个过渡期会持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第三,短期的看,民行职能会进一步加强,真正发挥诉讼监督与维护公益的双重作用。这些估计来源于两个基本判断:
1.事关“法治”进程
该标题并非托大,在此轮《民事诉讼法》修改中,有关民行检察的修改条款多达八条,立法加强民行监督的“意图”明显。这一修改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三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一是将信访纳入司法程序。司法改革是中央对现行法律制度反思的结果,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信访制度的反思。将社会矛盾主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亦成为此次司改的指导思想,立案登记、加强监督,都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产物。信访纳入司法,要求司法程序有充分有力的纠错保障,否则回流信访体系即成为必然。民行检察作为现有法律框架下的可依赖的一条纠错与息诉兼备的途径,为“信访终结”提供了“调解器”,也因此得以强化。据悉,中央政法委正在牵头草拟有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中检察监督作为再审后的救济机制,可能再次被强调。
二是审判体系自身纠错的局限。内部监督广受诟病,是自侦部门“被迁移”的理论依据之一。而同样,审判体系内部监督的纠错能力亦在波折中行走了几十年。也因为始终存在再审难、纠错难的问题,2007年、2012年两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均将重点内容放在审判监督程序的调整上。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法院成立立案二庭、出台《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再审程序法定化,使再审纠错功能得到一定发挥。但近年来,因为审判资源配置不能适应陡然增长的再审案件,部分法院不得不对再审制度再次调整——取消立案二庭,再审案件由审判庭自提自审,客观上又将再审纠错功能弱化。现阶段,囿于考核制度、内部关系、司法政策等多种因素,将审判监督程序作为“矛盾化解”的唯一路径,尚不具备现实条件,亦存在较大风险。
三是检察监督权的不断优化。民事诉讼法赋权后,检察院出台了《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与《行政诉讼监督规则》,《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也明确了审理抗诉案件的程序,制度层面的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制度环境的稳定为职权优化提供了契机,目前全国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办案人员,开始显现出逐年提升的纠错能力。
因此,检察监督的强化与法治进程的阶段高度匹配。在审判权威尚未完全建立、民众法治观念尚在构建、员额制对审判质量影响尚不明朗等现实背景下,保留并长期保留和加强检察监督制度,似为必由之径。
2.事关“检察权”定位
(1)监督权“保卫战”。自侦部门转隶后,检察权如何定位再次“被讨论”,保留“监督地位”将可能成为检察部门守护的“底线”。如果监督权性质动摇,检察院被纳入司法行政体系,就“指日可待”。
学界与检察实务界关于检察权是否应有监督属性、监督权与诉权的矛盾冲突等问题,一直未停止争议。甚至于为了回应争议,部分检察院通过机构分设的方式,将立案监督部门分设为审查逮捕部门与侦查监督部门,将公诉部门分设为公诉部与刑事审判监督部。检察院的监督权性质系宪法定位,也是一元化领导体制内,必须建立内生型监督体系的必然要求,检察监督在诉讼监督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检察院监督权属性与我国政治制度密不可分,长期保留检察监督权可以说是深层的制度和现实需要。
(2)民行是“碉堡”。检察院的诉讼监督地位或一般监督地位,都依靠民行这个碉堡的巩固。民行检察部门在被赋权开展公益诉讼试点之前,是唯一的“纯”监督部门,最可代表检察监督权的属性。三大诉讼中,民商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体量占到了90%以上,没有对民商、行政诉讼的监督权,谈不上“诉讼监督部门”。而失去民商、行政诉讼监督权,刑事监督权的“撼动”亦会轻而易举。同时,行政检察部门根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在开展对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探索,这是检察院享有对行政权进行监督的唯一入口,也是检察院从诉讼监督走向对行政权监督的唯一路径。职务侦查部门并入监察委员会后,检察院集中力量进行诉讼监督,探索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对维护司法公正和规范行政行为,必将起到更加显著的作用。
可见,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事关法治进程的发展阶段,事关检察权的属性与定位,不可轻言“存废”,这项职能具备长期存在并进一步强化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条件。
二、坦途还是荆棘?
回顾民行三十多年历史,如今立法相对完善、制度更加健全,是发展的最好阶段,也是开拓的最好时代。但不论是坦途还是荆棘,都只有自己做好了,才会有人给你搬把椅子。可见,是什么不重要,做些什么才重要。
1.打“组合拳”。
综观法院应对改革的动向,一是速度快,二是体系化。当年民诉法修订加强再审职能,法院马上设置机构、人员到位、钱物匹配、出台规范,一系列配套措施来匹配。如今,有风向执行局要剥离,法院马上宣告“用两到三年时间解决执行难问题”,紧跟出台《纲要》、人财物保障、完善网络查控、密集出台规定。“组合拳”一打,职权也在此番系统努力下悄然巩固。
法院快速反应和系统性的强化措施,颇为值得借鉴。组合拳通常着力于制度完善、机构建设、人员匹配等方面。制度层面,似需从比较薄弱的检察建议入手。目前同级监督、执行监督、违法行为监督均依赖“建议权”的强制力,制度层面争取一定的强制效力方能使这项职能真正“活”起来,并真正发挥作用。机构方面,民事检察、行政检察的机构分设迫在眉睫,民事与行政系两套完全不同的诉讼体系,各自发展路径需要单独考虑,需要有单独的机构承担。人员方面,目前人员匹配的不足导致力量主要扑在公益诉讼领域,传统申请监督案件审查似力有不逮。更加灵活的培养、补给和留住人才机制,是民行检察发展之最大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