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歌的相遇,是一场意料之内的惊喜


余秀华是诗人,钟立风是音乐诗人。他们或许前世是知音吧,因而唱出来的诗,字句之间,音符之外,分外动人。
——今日编辑阿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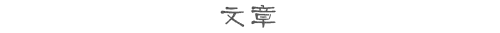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艺术是通过语言来表达,那就是诗歌。这种文体用最精炼的语言和极饱满的情感,表达写诗人的情欲和精神世界。而对读诗人来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或欢喜或哀怨,或明朗或寂寥。
诗人写诗,几行字,把世界和春天一同歌颂,把雁过两行的不经意彰显于纸上,把万千情爱摊开在你眼前。于是你知道,
你胸腔里的洪水猛兽有人安抚,你夜里惴惴不安的情绪有人感同身受。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庭庭如盖矣。”
孤坟已然,无处话凄凉。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你不知我爱之深浅,归根到底也像是一场我的独角戏。从
“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之偕老。”
的相爱誓约,到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的情深意切。

钟立风
如你所见,诗歌从来不是一种身处高阁的文化,而是富有生活气息甚至包含了每一个小角色喜怒哀乐的艺术。
而在诗与民谣这两个介质之间,总是有共通点的。诗歌与民谣,仿佛两颗孪生粒子,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它们会被一首曲调,一把吉他融合在一起,再让你触摸到生命真实温暖的质感。
《我爱你》,由钟立风作曲演唱的这首民谣,原是诗人余秀华发布在她的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里的一首作品。被唱成民谣的诗歌,除却诗人营造的意境外,又多了歌手的情感。把一首诗歌放进音乐里,显然,在诗歌本质所传达的思想和情感上,又增添了许多新的东西。
余秀华在北大演讲时,钟立风到场为她弹唱《我爱你》。镜头好几次转到会神听小钟唱自己诗歌的余秀华脸上,她笑意盈盈,眼睛里带着异彩光芒。仿佛也在惊奇着,自己的诗歌从民谣这个渠道,散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钟立风为余秀华弹唱《我爱你》
钟立风唱,
“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
巴巴地活着,做重复的事,过无味的人生,看似生活里已经尽是平淡和庸常了。但巴巴地过着生活的时候,我还是更希望至少天气是很好的,不会下雨我得去收衣服,不会打雷我蜷缩在被窝里。我更愿意在阳光好的时候,把身体和灵魂都晒在温暖里。我就像是一块陈皮,在四五月的阳光底下舒展身体。
“茶叶轮换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柠檬。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所以
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雪,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
”

花茶
菊花茉莉玫瑰柠檬,这些美好的事物,如心底里快要溢满出来的爱意。而这词,也印证了在任何一个女人心里,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田间农妇,只要心里拥有着爱与被爱的期冀,世界永远是可爱而年轻的。
“在干净的院子里读你的诗歌,这人间情事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
剧作家汤显祖在《牡丹亭里》写,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异曲同工,这人间的情事,也不能确切的找到来头,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
“而光阴皎洁,我不适宜肝肠寸断”
光阴是美好的,一遍一遍对自己说,所以一切都没有关系,你来不来,没有关系。
“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
知乎上一位朋友这样解读,
“稗子是一种生活在农田里的恶性杂草,它们与农作物争抢养分,它们不像水稻西红柿一样有人们保护,如果农人看见稗子,会第一时间除掉。水稻受人欢迎,稗子却遭人白眼。余秀华诗中的稗子就是她自己。她只是一个农妇。农妇要烧火,要插秧,要除草,要施肥,要耕地。她应该学着像一个真正的农妇一样生活,而不是在那里一首一首的写诗。她在诗中淡淡地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

麦田里的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