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keyword)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年头,一篇文章,一部著作,或者一项活动、一个展览、一件产品,都有关键词作为指引,带领浏览者认识其核心意义。作为指引,关键词的意义是帮助我们把握作者想要表达的核心,带领我们去认识作品的全部内容。因此也是日常阅读中较为受到重视的部分。
我们曾经一度担心电视、网络的进步会将人们传统的阅读习惯赶尽杀绝,所幸的是,新媒体时代把握住了新技术、新载体作为传播手段的定位,不断鼓励人们用新的方法展开阅读,碎片化阅读风靡一时。宋代文豪欧阳修曾记录了古人利用零星事件展开阅读思考,即著名的“马上、枕上、厕上”,与现在常说的地铁里读一本书、睡前读一本书并不不同。伊始,碎片化阅读的鼓励大家利用生活中零星时间,将完成的内容化零为整展开阅读;其后,阅读内容也逐步碎片化,介绍性、功能性的短小文字受到欢迎。碎片化阅读的最大意义在于“知悉”,传统阅读模式中的报纸、杂志阅读,内容上与碎片化阅读亦十分相似。
碎片化阅读在唤起国民阅读热情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因为基于连接网络的一块电子屏幕,伴随着搜索功能的不断强大,似乎每个人都可以迅速成为一个学养深厚的文化人。但网络提供的即时搜索服务,常常让我搜索的关键词从“丝绸之路”到“中印交流”,再到“印度香料”,接着读到“桂皮的植物属性”,最后搜到了“如何做好一道红烧肉”,等自己一面对着美食的烹饪指南垂涎欲滴,一面跃跃欲试,这一次阅读的初衷已然不知所踪。
搜索式阅读让人多知,但离开那块电子屏幕,脑海中除了搜索的关键词,又会觉得一无所获。伴随着关键词的搜索阅读,我们究竟是在搜索,还是在阅读?
应时而生的搜索式阅读
“信息爆炸”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随着人类知识水平的进步,各领域的研究成果百花齐放, 同时网络的发展,实现了全球的信息共享与交互,使得信息的采集、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的水平,我们所能接触的信息呈几何式增长。信息爆炸之下,我们知道的越来越多,同时也觉得自己的所知相较信息的全部越来越少。在这个几乎人人有话说,处处可传播的时代,传统的全面阅读越来越难以实现,我们总需要某种形式,去筛选出有效信息。把握“关键词”,成为信息爆炸背景下寻得有效信息的切入点。
搜索技术应运而生,搜索引擎整合了超越人脑认知极限的信息内容,让人们以关键词的形式进行搜索,获得相关信息。书本、刊物的电子化发展,伴随着搜索技术的运用,使搜索式阅读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提供的不仅是搜出一本有用的书,更是细化到搜出书中具体的一段文字,一句判断。我相信,很多人都爱死这个功能了。
曾经,读完一整部《史记》后,如果想回头找出“纸上谈兵”的故事原文,光记得赵括是不够的,还需要记得事件发生在秦国与赵国对峙时期,并准确记住事情的发端是赵王将原本的守将廉颇换下——因为这个故事记载在了《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如果对故事原本记忆不够准确,往往就得从头把书翻过。而有了搜索技术之后,我们只需要记得赵括是主人公,搜索他的名字,就能很快找到原文。搜索技术成熟
后,我们似乎不再需要记住一本书、一篇长文的所有细节,才能提取出有用的部分,我们需要的,仅仅是这本书的电子版。
《阅读的战略》
作者:
顾晓鸣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11月
不再去熟悉、记忆一本书的全部,不仅是受限于我们要读的书籍、要学习的知识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也是基于当下很多读者的阅读动机已经发生的变化。阅读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它既需要认知、思维、记忆、想像等智力因素参与,也需要动机、兴趣、情绪、意志、性格等非智力因素提供保证。可以说,阅读动机,最大程度上决定了阅读内容和阅读方法。获取知识是阅读的一项重要任务,但不是阅读的全部。
很多人的中学时代,明明背着许多知识充盈的课本,却更愿意读上一些充满豪侠之气的武侠小说,或者几本写满温情软语的言情小说,还有若干带着忧郁气质的青春散文。那正是因为,
阅读不同于学习,除了获取明确的知识点,更有自我满足,自我提升,自我修养的重要功能。从碎片化阅读带来的风气看,阅读自我满足、自我提升、自我修养的层面被忽视了,“功能性”成为首要议题,关键词的搜索,恰如其分地满足了我们了解具体知识点的需求。
搜索式阅读的产生还依托于当下的一个现实,科学研究开始对研究者有了成果的产出规定。尤其是人文学科,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著作,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要依托这些文献著作创造出自己的见地和观点,很难做到全面阅读。于是,搜索关键词,精准找出与研究相关的材料,把搜索阅读的功能发挥到淋漓尽致,成为辅助研究的重要手段。
潜伏在搜索式阅读后面的问题
搜索阅读的优势是精准、迅速,能快速达成阅读获取信息的目的。然而,通过关键词搜索获取的信息,依旧不是全部。
阅读行为基于写作行为,写作是连贯思维的表达,所以阅读的本来面目也应该是连贯的。阅读获得的信息,是从写作内容整体中获得小于整体的部分,这个部分获得应该依托于整体。但依靠关键词搜索完成的阅读行为,并不基于写作行为的连贯性、整体性,因此,虽然获得了阅读目标,但阅读目的未必能很好地达成。譬如,搜索“太阳”,固然能获得与“太阳”相关的全部网络信息,但太阳还有“白驹”、“金乌”、“赤轮”等别称,以这些称谓为核心的信息,就不能体现在“太阳”的搜索中。简单信息尚且如此,复杂的知识、问题搜索,则更容易挂一漏万。
《阅读的至乐:20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
作者: [英] 约翰·凯里
译者: 骆守怡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5年12月
进一步来说,基于关键词的搜索式阅读没有完整的阅读背景,让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机会。很多时候,通过关键字搜索阅读看到的内容,是经过前面的阅读者加工的观点,离原著本身尚有距离,在此基础上的阅读理解,离原著作者的观点会更加遥远。同时,源于内心对二手观点的质疑,我们只能在关键词之下多看一些二手观点,去总结主流观点,最后自己得出的结论,也不过是很多人观点的折中而已。
当前,一些推荐阅读、辅助阅读甚至可以成为替代阅读的手段,层出不穷。譬如逻辑思维团队就出品了一款叫做“得到”的读书APP,提出“提供最省时间的高效知识服务”,推出了“每天半小时,搞懂一本书”的专栏。我当然不否认这类手段的指引之功,但作为一个文科类博士,对半小时能不能真的搞懂一本书持极端怀疑的态度。好的介绍分析,能够成为进入一本书的好途径,但不可能成为读懂一本书的替代品,不然,我们读前言、读摘要、读目录就好,为什么还要读书的内容呢?萨特就认为,“当词儿在作者笔下形成时,他无疑是看见这些词的,但是他看见的与读者看见的并不一样。”这与我们熟悉的莎士比亚的“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同样的判断。如果离开原著,只取碎片,就看不到哈姆雷特;如果只看别人怎么描述哈姆雷特,最终,也只能看见别人眼中的哈姆雷特。
我们常常能听见一种抱怨的声音,当代文、史、哲学科,出色的研究者与研究都不多。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搜索式阅读造成的。纸质书时代,研究者需要对原典、著作进行整体阅读、全面阅读,对原典风貌,著作内容和前辈学人的研究状况全面把握,理清脉络。
但现在基于搜索阅读的“研究”越来越多,今年三月,北京大学宣布停止购买知网数据库,引起轩然大波,“堂堂北大竟买不起一个数据库”的控诉背后,既包含着重要数据库在搜索式阅读研究中不断自抬身价的事实,也透露出大家对全面、可搜索数据的依赖。而近期北大图书馆整修,只有少数老师表达了忧虑和不满,这充分说明阅读功底的基本要求没有得到重视。记得曾经参加过的几场研究生面试,老师问,某位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什么,学生滔滔不绝答了很多条,老师再问,这些观点分别出自这位学者的哪几本著作,此时能回答清楚的寥寥可数,如老师再追问,讲一讲这位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原本论述和你的看法,则多数人开始支支吾吾。缺乏全面、整体的阅读背景,导致此后的研究视野、关怀、能力都不足。
再加上超前的科研要求,使得很多研究成果都建立在搜索阅读之上,显得细碎,隔靴搔痒。
手段不是全部,阅读应有深意
搜索阅读如同看剧情梗概,让阅读失去了其本真意义,也体会不到阅读的乐趣。关键词和内容介绍如同骨架,书籍如美人,有内容才有血有肉,顾盼生姿。一本好书的创作,不是简单的理性追求,而是带着艺术追求,在给出理性判断的同时,体现出文学、文字的韵味。本雅明解释过“韵味”,那是“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又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现象。”这不是通过几个关键词和一篇摘要或介绍能体会的。
几乎所有多媒体和新媒体应用的社会研究,都会提到新的传播手段对传统文学阅读的冲击。新媒体在重拾阅读关怀的同时,也难以替代传统阅读对语言赋予文学阅读的那种无可替代的审美意义。在阅读电子化的时代,能够利用好搜索的强大功能是我们的优势,但如何重视和培养完整阅读的习惯、享受阅读过程,又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我并非要批判基于网络的电子阅读。一些阅读行为实验研究表明,在正常阅读速度下电子屏幕阅读会有更好的理解水平,而在正常阅读速度下,花更长时间停顿、有更多光标滑动次数的读者,对文献有着更高的理解能力。这说明电子阅读是有优于传统阅读之处的,同时搜索功能也确实为延展阅读提供了广阔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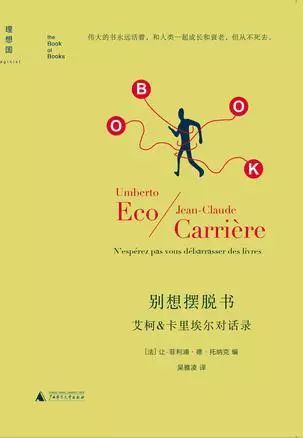
《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
作者:[法]卡里埃尔 [意]艾柯
译者:吴雅凌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
但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的差异研究也明确指出,超文本阅读时间成碎片化发展趋势,相较于直接阅读纸质文档,读者很容易受到网络信息干扰而无法集中注意力,对文本的理解更肤浅,缺乏更具体的理解和感情投入。数字阅读对于复杂信息的认知加工效果略差,内化阅读材料的能力较弱,长期记忆表现逊于纸质阅读。说明即便我们只是想要从阅读中获得知识,也应该注重传统阅读“内化知识”和“长期记忆”的优势。
除去获取知识,其实消遣阅读也是一种以追求精神文化享受为主要目的阅读类型。在阅读类型的分类研究上,它是相对于学习型、研究型而独立存在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只看教学课本。
就像我们坚持锻炼未必是为了别人称赞一句好身材,而是为了拥有健康的体魄,坚持吃饭未必是为了填饱肚子维持生存,而是为了体会食物与味蕾的碰撞,得到愉悦的体验。同样的,阅读也未必是为了知道一项确切的知识或者告诉别人我读过什么、知道什么,而是能够体会阅读的快乐。
在阅读过程中,我们的视野不断打破又不断形成,不断修正又不断扩充,不断更新又不断提升,这比从书中获取某种具体知识更为重要。阅读需要理解,而我们所能理解的,都是与自我有关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对书籍的兴趣,也就是对自我的兴趣。
翻一翻每一年的畅销书书单,就能知道这阵子人们需要什么,从九十年代的经济类解析到世纪初的青春文学,到近些年的商界自传和心灵鸡汤,这些畅销书映射着时代和人的问题与追求。看一看书房的书架,就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旧书和新书的不同,往往也说明着生活、工作、思想的变化。
在接触、阅读一本书时,我们不是暂时地被移人文本的世界,而是我们就在其中;彼此相遇,彼此对话,一个意义世界由此生成,这是阅读让我们即便身处荒原亦不孤单的能力,是几个关键词所不能给予的深意。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苏敦复;编辑:张婷。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