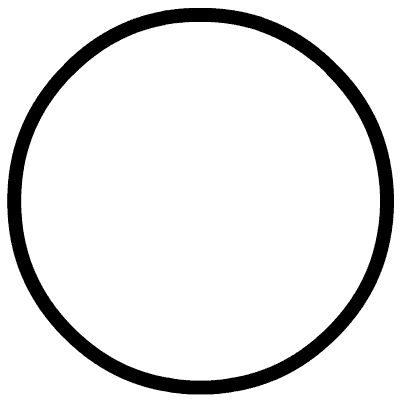
点击上方关注我们


当代艺术就是当代的宗教
文 | 振昇
正如涂尔干在其宗教社会学研究中指出的那样,澳大利亚土著的宗教并非所谓迷信,也不能被归为偶像崇拜。出于相同的逻辑,我们也不是在迷信或偶像崇拜的消极意义上将当代艺术指认为当代社会的宗教的。恰恰相反,当代艺术作为目前最流行的宗教之一(另外两种宗教是金融行业和互联网行业,而不幸的是,哲学早已被剔除出此列,因为哲学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形而下的现实问题,即失业),乃是一大值得关注的有趣现象。
今天,一件作品(尤其是多媒体作品)可以有无数显灵,同时存在于不同的空间之中(目前,我们就可以同时在西岸美术馆和多伦美术馆看到同一件声音作品,就如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在不同的教堂看见同一个耶稣一样)。这完全颠覆了经典物理学中对于物质微粒的定义(而这一定义首先依赖于我们的日常感官,正如分析哲学家们乐于指出的那样):时空中的同一性或轨迹的连续性。这是当代艺术的量子时刻,它的出现遵循的是法国科学哲学家米歇尔·比特博尔(Michel Bitbol)所说的量子逻辑:对同一件作品的两次观看恰恰是一前一后在两个不同语境中观看了两件作品。比如,一件多媒体作品以不同的解码方式,呈现在不同的展馆中;或者,一件作品,在同一空间中,却由于不同的展陈方式而成了两件作品(更不用说其他的装置,它们的每一次展出都是一次新的组装,但展览介绍毫无疑问会将其指认为同一件作品)。这也是当代艺术遇到的当代泛神论问题:同一性/身份(identity)的概念变得可疑了,尤其是在计算机和互联网出现以来。这一点已经由格罗伊斯无数次地强调过:文件的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解码,不可见的编码保持不变,但编码的呈现则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它取决于显示器的分辨率,取决于解码的软件版本等)。正如互联网的网站,时刻处在再次编写和在显示器上显示的流动之中。这是当代的泛神论处境:用户的个人数据可以存在于远离人烟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之中,当代艺术作品可以同时出现在不同场馆之中。只有基于此种关于同一性/身份的游戏,我们所说的具体的身份政治和身份艺术才能真正指向身份——无论是种族身份、性别身份,还是阶级身份。
与之相应的是,艺术工作者也在像黑特·史德耶尔所观察到的那样变得日益身心分离。肉身出席已然成为艺术劳动的标准,而开幕式上的艺术家和策展人脑海里可能已经开始盘算下半年的展览计划和项目。在这一点上,哲学界的学术活动也是一样的:比如研究者可以下午在上海开会,而第二天一早就得在北方某省会出席另一个开幕式。可以说,艺术项目,而非艺术品,尚未出现,就已经过时了。当代艺术必须以超越历史时间的方式来组织:想要最当代,就得以最当代的方式介入当代,那就是比当代走得更快。因此,后工作时代,不是首先表现为由于演化的自组织机器人和AI所导致的各种脑力和体力劳动的边缘化,而是一开始就表现在了当代艺术的活动中:不间断的肉身在场,但同时又早已走神。然而,恰恰只有通过这种灵魂出窍的方式,艺术人士才能真正进入作为当代艺术的宗教之中,这是艺术的出神(l’extase),是当代艺术的神秘主义时刻。
这一判断同格罗伊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他也认为现代以来的艺术和古代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有着密切关联:面对上帝,信徒和修士需要雕琢灵魂,好让自己不像骆驼穿针眼般困难地进入天堂;面对公众,艺术家们必须雕琢身份,以便自我设计为一件进入公共领域的作品。宗教时刻必须是一个公开的时刻:澳大利亚土著在仪式性的集体活动中,朝彼此呕吐,相互殴打;北美印第安人把所谓“财富”当众毁灭,或拿出来招待他人大吃大喝。甚至可以说,当代艺术作为宗教,比一神论的宗教更加宗教,因为相比于修士在山顶修道院中的单人小室(cell),当代艺术选择了更加公开的场所。不要忘记,在布努埃尔的极具幽默感的电影《沙漠中的西蒙》里,柱头修士正是因为孤身一人,才在荒漠里见到了化身为各种形态的魔鬼。于是,就如福柯指出的那样,只有引入他人的全天候无死角的监视(上帝之眼在19世纪的巴黎侦探小说中就已经是一种常见的“监视”形态),才能保证对每个个体的治理。疯狂是集体的,癔症才是个人的。
当然,作为一种当代宗教,当代艺术也必然是金钱快速流动的交易所,正如古代的寺庙等宗教场所也常常保管钱财和账簿一样(其中大部分是香火钱和功德簿,但也真的有在世俗世界中流动的货币,就像大卫·格雷伯在《债》中提到的那样),或者货币也可以以虚拟的方式(即在道德说教的掩盖下)在教堂中兑换和流通,基督徒们正是借此才能谈论原罪(作为欠上帝的债)和救赎(欠债还钱)。在宗教经济学方面,尼采、巴塔耶、格雷伯作了最惊人的分析。因此,当代艺术成为一门能吸引大量资金的行业也就不足为奇。真正的商人如刘益谦,玩股票和炒房地产已经不够,他的终极金融产品就是艺术。反过来说,在人类历史上,真正能搅动大量资金的行业都如宗教一般了。为何?因为这些行业的参与者必须如西伯利亚的萨满一般,精熟于调动各种不可见的力量。在亚马孙雨林中,在巴拉圭的土地上,瓜亚基印第安人就喜欢谈论这些不可见的力量:“美洲豹就是森林中的猎人,他们会吃了你!”然而,据民族志记载,甚至许多人一辈子都碰不到美洲豹——印第安人谈论的实际上是森林中不可见的力量,死亡的力量,为了避免这一力量带来的灭顶之灾,他们宁愿食人(对待死去的同伴,可以是直接切块然后烧烤,也可以是将其腐烂后剩下的骨头磨成粉末,拌在木薯粉中食用)。
当代艺术、金融业、互联网为何能相提并论,并共同成为当代的宗教,就是因为它们的从业人员都喜爱谈论不可见的力量。他们的工作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他们调动了这些使其合法化的肉眼看不见的东西,而且,也正是这些不可见的东西创造了一切,正如《旧约》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耶和华用言词创造了世界(“旷野中的呼声”)。在外人看来,金融投资、程序编写、艺术品的存在都是以神秘、不可知的方式制造了惊人的物质产品和财富。
因此,艺术人士,理财专家,程序员虽然谈论的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不能再世俗的东西(项目、资金、出席、业绩等等),但实际上都是最不讲求现实的唯心主义者。相反,高谈理想、情怀、理念、本质的理论人士才是最现实的。因为搞金融的人都信仰金融,搞理论的人士都不信仰理论。前者真诚地认为他们手里掌管着天文数字般的资金,决定着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命运,而后者常常只能看见C刊数量、各种“帽子”“本子”、青年基金。理论人士(尤其哲学研究者)的虔诚有时只是迫不得已,单是为了模仿金融,他们才一拍脑门想到要发明自己对理论的虔信。
因此,我们不难看到,金融人士就如同教会人员一样,热衷于兜售赎罪券给大众,也就是给每个人弄上贷款。顶级的金融梦想是彻底无产阶级的,就是贷款给每一个穷人。换言之,终极的宗教是民众的柏拉图主义(如尼采所言),终极的金融是贷款给每个信用评级为E的穷人,终极的当代艺术也就是博伊斯数十年前就号召过的“人人都是艺术家”。而现在,正是彻底实现这一口号的时刻:每个人都成了社交媒体上的自拍者,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小红书网红,每个人都是自己身份的总设计师——朋友圈就是每个人自己的策展。就连召集一场学术会议,也必须如策展一般(但这绝不是什么需要指责和批判的事情,因为情况反倒是,在当代所做的一切,都需要依照当代艺术这样的宗教来进行:学术活动在当下最紧急的问题不是过于宗教,而是太不宗教了!):必须要有大牌的肉身出席,需要有盛大的开幕和讲话,最好有媒体在事后进行学术报导,有惊人数量的隐形学术劳工(通常是些处于学术最底层的硕博研究生),需要精美的茶歇来对标特展开幕上的酒会。我们还可将这一切看得更透:通过社交网络实现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当代艺术,最终也让这些互联网平台成功上市,于是,每个人的自我设计也就为依托于分布式基础设施和大量海底光缆的金融流作了一份贡献。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