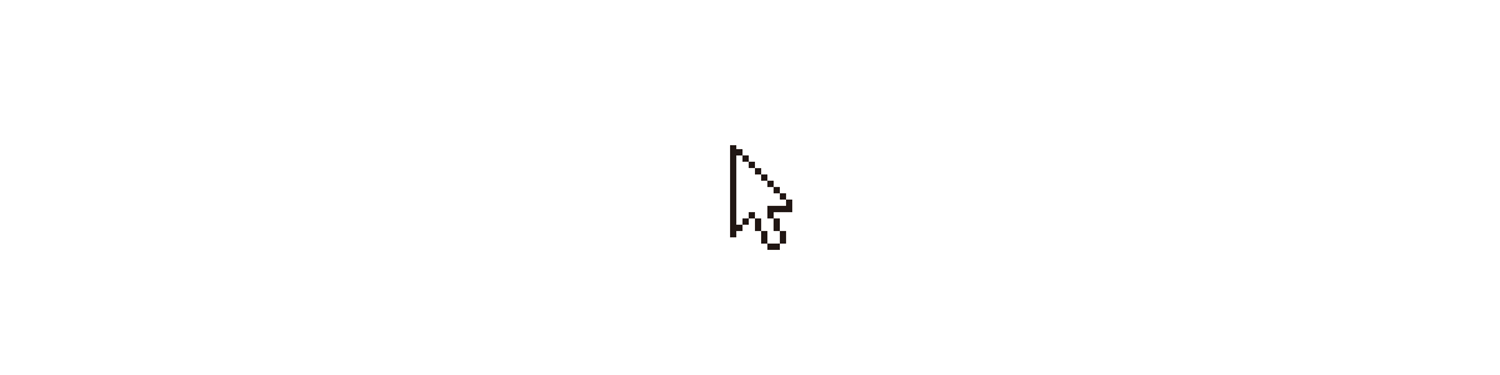她
15级新闻1班 戴霞
“我是1971年农历五月初十生,年份属猪,月份属马,时辰属马,我有两匹马。算命的说如果我是一个男的那就走南闯北,飞黄腾达,可惜是个女的。”她嘿嘿地笑着对我说,带着些许骄傲的神情,同时又有一丝无奈。
一双小凉鞋
1975年,她四岁,二哥把她交给大哥,然后去做事了,大哥感冒了要打针,她见了针头害怕,于是,就一个人走开了,远离了大哥的视线。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沿着铁轨慢慢地走,走到太阳下山,不知身在何处,迷路了,辛亏一个好心人家收留了她。等到大哥打完针,才发现,妹妹不见了。
于是乎,家里人全部出动,三个哥哥三个姐姐走街串巷,到处贴传单,问人。那段时间,父亲随身携带了一个锣,吃饭也不拿下,走到哪里,敲到哪里,喊到哪里,连续找了几天,没有一点消息。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问到一个关键性人物,有了一点眉目,打听到浒口(小地名)好像有一家人收留了一个孩子。于是,快马加鞭地找到那个人家,大哥走进去,一眼看到她,冲上去抱着她痛哭。自责,愧疚,连日来的辛苦、劳累化成泪水“一泻千里”。哭过,抱着她,回家,走了一小段,她对哥哥说“鞋子,鞋子。”大哥一低头才反应过来她还没穿鞋,他的确太心急了。于是,只好又回到那个人家给她穿上走丢时穿的那双小凉鞋,这次,才是真正的一去不复返。
临近家门口,“妹妹回来啦!”“妹妹回来啦!”此时,父亲正在楼上,听到了,三步并两步,冲下来。自此以后,别人就叫她“浒口妹几”。
“我在那个人家住了两三天哦,也真是的,丢了就丢了,干嘛要把我找回来,家里八姊妹还不够嘛!(她还有一个妹妹)”她露出有点不满又不解的表情,“那个人家好像只有三个小孩,说不定在那个人家我会更有出息也说不定哦。不过,虽然家里姊妹多,可能父母觉得就是条件再艰苦一家人也要在一起,找回来其实也挺好的。”她对我笑了笑。重提这件事,她忘不了大哥抱着她痛哭时的情形,“啊,现在大哥已经走了,我想他。”
一笼猪草
她的童年离不开猪草。
上小学时,她每天早起去割猪草,割满满满一笼,双手使劲压笼子里的猪草,减少空隙,直到无论怎样压也压不下了,再也放不下时才结束,等提回家时汗水浸湿了衣服,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再去上课。“那时候猪可比我们重要得多,全家就盼着过年杀猪卖钱,即使上学,也要把猪料理得好好的,喂得饱饱的,这一天的学也上得踏实安心,不然的话就会挨骂。”
小学毕业,她就再也没有读书了,为什么不上学?她的回答是:还能是怎样,没钱呗!学费只要五块钱,可家里连五块钱也拿不出,问我哥要,他叫我先赊着。(她哥比她大很多,她读书时他哥已经掌握家里的财政,父母根本就没有钱在身上。)每年开学的学费几乎都是赊,后来实在是赊不下去了,也就没读了。
“想着不读书了,自己就能赚钱了,也就再也不用赊学费了。”
1984年,那年她13岁,便跟着邻里附近的泥水匠(帮别人建房子的)手艺人出去做小工(小工意即帮泥水匠打下手,挑灰担石),一天只有 1~1.1块钱。
“那个时候还那么小,怎么会有力气?”我问。
“我有力气,他们也会来叫我的。”她边说边对我点点头。
一堆黑碗
1990年,她嫁了。
1991年,她生了一个男孩。那个年代计划生育查得很严,村里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不定期地来到每家每户查人,于是,怀第二个的时候,她不得不四处躲藏。
去过湘东(地名)的姐姐家,住了一个礼拜,趁着夜幕回到自己家中,一进厨房,灶台上到处都是乌黑一片,碗筷堆积成山,她一个个碗洗好,放好,把灶台抹干净。收拾完备后,害怕有人告密,于是又趁着夜色,回到自己的娘家,第二天由妈妈领着又到自己的姨妈家住了十几天。
“真是的,不会洗衣做饭也就算了,连碗也不知道洗一下吗?那个场景真是脏的没法看啊!碗边上都是黑的。”她埋怨地对我说,“真是‘圆手掌’(方言,意即什么家务也不知道做,也不会做的人)啊!”
生第二个的时候,她从下午就开始痛,一直痛到晚上十二点才生下来,那个时候生孩子不用进医院,都是在家里生,医院也很少。“真是辛苦了接生婆,她也是从下午一直守到晚上,哪里也没去,就守着我!”
生了一个女儿,十斤半,本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可妯娌之间又有一些流言蜚语。“这么重的宝宝,她肯定偷吃了什么好东西!”“哼,我就知道,还不承认偷吃。”等等之类的话。“那个年代,有啥好东西吃啊,左右都是一口饭,也没啥其它吃的”她说。
一辆小四轮
2003年,花光家里所有的积蓄,她丈夫买了一辆小四轮车用来运货。什么都运,石头,石灰,土,砖块,只要能赚钱,只要有单,干活也不分白天黑夜,可是,四轮车的照明灯没用。于是,她提着个大型手电筒,坐在副驾驶位置帮丈夫照明探路。夜深了,眼皮不自觉地合上了,身体侧倾着靠在旁边的车门上,可手却依然紧紧地握住那个灯。
“大半夜的,所有人都睡了,我们依然在开车运东西,一个人的时间更难熬,更容易瞌睡,有我陪着他,时间过得也快一点,也不那么难熬。”
后来,运着运着就没有货可运了,他们决定卖了那辆小四轮。
有人上门看车,围着车子转了几个来回,东问问,西问问,终于谈到了价钱,问还能不能再少一点,她说不能。于是,那人走了,下午又来了,再一次绕着车子东看看西看看,一再要求再少一点,她坚决地说不能再少了。日薄西山,那人还在磨蹭,直至天完全黑下来之后,问真的不能再少了吗,她说不能。于是,那人拿出钱,成交。
她丈夫当面点清了,又交给她,她再点了一次,数量没有问题。于是,她回家,拿出手电筒,一张一张地核查辨别真伪,一张一张的钞票从墙上划过,留下一道又一道红红的印记,点到中间一张,她无论怎样都看不到隐藏在图案里一百的数字,在墙上划过也没有红色的痕迹,她慌了,赶忙叫她的丈夫,跟他说有一张假钞,可她丈夫说去找买车的那个人他肯定不会认,他也已经把车开走了,算了吧。她气不过,语气强硬地说他不肯认也得认,这些钱就是他给我们的。在那个年代,她家没有摩托车,于是他丈夫拜托一个家门口买了摩托的人载他俩追赶那个买车的,在半路上,拦截下来了。
买车的人当然不肯认,“你都已经进家门里了,我当然不会认!”他理直气壮地说。“我都还没把钱放下,这些全是你给的钱。哦,你故意等到天黑,以为这样我们就不会发现有假钞了是吧。好啊,你不承认可以,车子不能开走。”声音提高了几个度,她把钱扔给买车的人,站到四轮车面前,伸出双手,做出要走就得从她身上踏过的架势。
局面僵着,持续了很久,最后,买车的人妥协了,不好意思地说:“我现在身上也没有一百块钱,等我有了钱再给这个钱可以吗?”“这倒可以,以后给没有问题,你承认就行,你说不是你的那我就很气愤。”她说。
“那个年代,一百块钱不算小数目,那可是几天的工钱呢!”她眼神坚定地告诉我,“现在,那个买车的人在路上碰到我都要绕道走的,更不好意思同我打招呼,就是因为这件事。”
一场牌局
2004年,小四轮卖了,卖了四千多块钱。
揣着一大笔钱,她丈夫高高兴兴地在别人家里吃饭,饭桌上当然少不了白酒,她丈夫逢酒必醉,醉了,又聚众打牌,醉醺醺的,逢赌必输。
那一天,吃过晚饭,她一直等她丈夫回来,等到晚上11点,还没回。“我心里很着急,他身上带着那么多钱,要是这些钱都输掉了,那可咋办啊!”她说到这,依然很急,气得直跺脚。
终于,她再也坐不住了,于是,拿着那盏重重的大型的手电筒出门去找他,在他“好兄弟”家中找到他,果不其然,他在打牌。
她径直朝他走去,嘶吼道:“你回去么!你是不是要把这些钱都输掉才肯罢休!”她边说边用手扯他的衣服,使劲往外拽。
他丈夫也是好面子之人,哪能忍受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吼他,“我不回去!”说完若无其事地继续打牌,对她熟视无睹,看也不看她一眼。她不甘心,用尽全身的力气拽他,他踉跄着,离开了他的位子,转身又回去坐下了。她一怒之下,用手电筒狠狠地往他的手臂砸去,也许是因为看见她发火了,又或许是因为手臂疼,他乖乖地跟着她回家了。
回到家,她转身,看到了他的眼泪,后来经医院鉴定是骨折。他大半夜的,拿着手电筒,走路去找她的娘家人评理。
第二天,她的哥哥和姐夫来了,说她打人是不对的,“我也知道是不对的。”她不好意思地对我笑了笑。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她婆婆早就对她不满,这次逮到机会,于是在她娘家人面前申诉。“怎么可以这么狠心,把老七(她丈夫排行老七)的手都打断了。哈,这么歹毒,这么恶。”自此,她婆婆愈是对她不满,看她不顺眼。
一份蛇鱼汤
2004年,下了一场大雪,纷纷扬扬了好几天,她儿子还不满14岁,上初中,在骑自行车回家途中摔了一跤,摔出路边好远,左腿膝盖摔伤了。前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家耽搁了好长一段时间,情况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糟,这下她着急了,带着他到萍乡(地名)医院检查,医生说需要动手术,这里医院吃不消,建议去长沙的大医院。
她生平第一次出远门,坐火车来到长沙。经检查,儿子需要动手术,否则会终生残疾,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说什么也不能要他残疾,可当手术同意书递到她和她丈夫面前时,丈夫犹豫了,他不敢想也不能承受手术所带来最差的结果,最终,她坚定地写下了她的名字。
手术成功,她和她丈夫还要在医院待十几天照顾儿子。她买了一张长椅,可收缩的,白天用来当凳子,晚上用来当床,医院里的床位需要额外收费,她就和她丈夫轮流在长椅上睡觉。
听到同病房的人说蛇鱼汤有利于刚动完手术的病人伤口愈合,于是她下定决心花了二十几元买了一份,自己却在医院周围的小摊贩上花一元钱买了一塑料杯的霉豆腐。“可以吃好几天,这样每天只要打点饭就行了,一元钱不算贵的。他(指她丈夫)每天吃霉豆腐,最后吃到“拉长了脸,嘴嘟得老高了’。”她笑着说,“那个时候凑齐手术费已经是倾家荡产,还借了亲戚许多钱,怎么不要省着点用,我当然也知道霉豆腐不好吃,可是没有办法啊!”
一套老房子
2005年,因为修建高速公路,她婆婆和公公住的老房子要拆了,拆迁自然就会有一笔拆迁费,她三哥(她丈夫的三哥,她婆婆生了四个儿子,她丈夫最小)跟她婆婆说钱给他,让他的房子建得大一点,以后她婆婆和公公就跟着他,在他那吃住,不用去其它儿子那里吃住了。
“哼,我还不知道他的小心思,那时候公公身体很好,还可以种田,自己也可以赚钱,他当然想公公跟着他,等到他们老了,生病了,有什么毛病,要照顾了,到时候他就会说你不只一个儿子和儿媳,怎么不叫他们也来照顾你啊。他这个人很恶,只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
四个儿子儿媳以及公公婆婆在门口坪上商量这件事情,所有人都不吭声反对这个提议,她站出来说,公公婆婆跟着你老三可以,等他们老了,有什么不好。要照顾了,你就别叫我们这几个来照顾么,到时候就别说不只一个儿子儿媳之类的话。
于是,这件事没谈成,她三哥到处跟人说她很坏,并给自己的儿子灌输这种观念,“钊钊(她三哥儿子)长大了还到处说我要不得,他很坏。”她说。
事情还在发酵,怒火还在滋长。
那件事情后的某一天,她三哥喝醉了酒,大半夜地跑到她家敲门,她不开,“你给我开不开门,信不信我把门弄坏,你给我开门!”门外咆哮着。她丈夫很害怕,打算开门,“你不要去,我就不信他能咋的。”她喝住了她丈夫开门。
那时她家的门还是老式的木门,关门只用两个门栓,不知咋的,竟让他三哥给打开了,冲到她在的房间,一脚踹开房门,进去就拼命砸东西,连脚带踢地,她忍无可忍抓住一旁的凳子往他的身上砸去。
伴随一声响,她三哥离去,她也不甘示弱,大半夜的,跑到她三哥家,坐在他家门前要求赔偿她的缝纫机,最终得到三百元的赔偿。
“二哥曾悄悄地对我说,说你这一凳子砸得好,当然啦他也只敢悄悄地在背地里说,不敢明说,其它兄弟都怕他啊。”她凑过头来,身体往我这边微微倾斜,边说边用眼睛往外瞄了瞄,生怕被别人听见。
不出意料,她婆婆又说了她,“你怎么可以打人呢!”“哼!跑到我家来,‘关门打狗’听说过没有啊。”
她,就是我的母亲,也是那个时代千万母亲中的一个,这些经历都是她在不经意之间说给我听的,鉴于这次写作,我详细地问了其中的经过、缘由。当然,四千多字也只是她汪洋故事中的点滴,过往的经历如今都已刻在她的脸上变成皱纹,有深有浅,有长有短,经过岁月的沉淀,再面对时,一切释怀,莞尔一笑,同样,她的故事还在上演,还在继续,那又是些怎样的故事呢?
春运·检票口的故事
15级新闻2班 周子欣
天色微明,漳州市动车站空旷的候车大厅里,十几台橙色的机器整齐地排列在通向月台的几个入口处,透过玻璃穹顶射进来的光线稀疏地洒在地上,点点光影映衬着半空中大屏幕上滚动的班次信息。
渐渐地,进站口的安检通道前队伍越来越长,急促的脚步声和行李与地面的摩擦,伴随着嘈杂的人声打破了沉寂。一张张形色匆匆的脸庞、肩扛手提的行李,夹杂着不同方言的吆喝和一股股涌动的人潮——春运,这一项世界上最大的周期性运输高峰期间,这样的场景每天都会在天南海北的各个角落上演着。
套上代表着春运志愿者的红马甲,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在不同的检票口来回跑动协助维持秩序,于我个人而言,是一个锻炼自己,服务社会的过程,也是一次近距离观察春运,观察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难得机会。
沉甸甸的泡沫箱
“你好······这趟车······往哪走呀?”在一拨人刚刚从检票口潮水般通过后,这个带着怯生生口气的苍老声音听起来是如此突兀。循声望去,一对老夫妇正孤零零站在大厅中央,老人一手举着车票四处张望,另一手紧紧攥住了什么东西。老太太紧紧依偎在他身边,微微发着抖左顾右盼。
“您好,爷爷,我们能做些什么吗?”我和另一个小伙伴迎上前去。老人看到我们衣服上的“志愿者”字样,像见着了救星一样把车票举到我们眼前:“孩子,帮爷爷看看,这趟车该去哪里等哇?”拿出动车时刻表查询之余,我的目光落在了老人紧攥住的右手和身后——原来,老人身后拖着一个被麻绳紧紧绑住的泡沫箱,麻绳的另一端落在他刻满岁月风霜,微微颤抖着的手心里。
“您这泡沫箱里装的是什么呀?”在查询班次的时候,同伴好奇地问起老夫妇。
“嗨,就是咱们这里的一些海产干货——这回去和孩子过年,带些过去给他尝尝家里的味儿。”
原来,两位老人的大儿子在上海工作成家,这一次两人前去深圳过年,就想着给儿子儿媳带去些家里的海产干货,“过年得吃到点家里的味道,他们那没有我们就自己带过去。”
经过核对,老夫妇所乘坐的动车在一楼检票,这意味着他们还要把辛辛苦苦提上楼的泡沫箱再一次顺着几十级台阶运下。看着老人一咬牙拖起麻绳套上肩膀的吃力,我们忍不住走上前一把抬起了泡沫箱:“爷爷,您放下休息会吧。我们帮您抬下去。”
“哎,不用不用,爷爷自己能拿动······”老人虽然摆着手婉言推辞,最后还是看着我们帮他扛起了箱子,自己还是不放心似的,攥着绳子跟在我们身后慢慢踱着。
泡沫箱不大,但是被装得满满当当,两个人扛起来还觉得有些吃力。可以想见这对瘦弱的老夫妇究竟花了多大力气,才把箱子扛上了几十级台阶。
到了检票口,老夫妇说什么也不肯让我们再帮他们搬一程了。老人颤巍巍地将麻绳在右肩膀上绕了两圈,空出的左手牵起了老太太,两个佝偻着的背影伴随着泡沫箱在地板上发出的刺耳吱嘎声,渐渐消失在了通往月台的道路尽头。
哭泣的小男孩
在五湖四海的游子们心急如焚归家的路上,检票口的闸机带来的小麻烦时常会让他们心烦意乱:一个不留神行李或身体的某个部位超过红线,就会引发警报器的一阵急促铃声和检票口的封闭;好容易挤到了检票口前,刷了半天身份证愣是没有一点反应;或是干脆在车票卷入检票口后卡顿许久,悠悠地跳出一行字“本机故障”······当然,这些问题其实无伤大雅,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大都能得以顺利解决。只是在归心似箭的群体中间,任何一点微小的火花都可能激发极大的负面情绪。
事情的开始,不过是一件平常的小事:离发车检票还有半个多小时,小男孩离开疲惫不堪坐在长凳上休息的父母四处玩耍,看着检票口下面的小空隙跃跃欲试,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钻过去后,发现爸爸妈妈已经不在身边,一时也没想起如何钻回另一头,就站在检票机器边上嚎啕大哭起来,这一闹,就吸引来无数人的目光。
偏偏这个时候,把守检票口的工作人员不在眼前,闻声赶来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大眼瞪小眼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隔着栅栏劝慰男孩“乖乖的别哭,马上就把你带到爸爸妈妈那里”,但孩子嚎得更加厉害了。
这时围观的人群开始越来越多,冲着哭闹的小男孩和手足无措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指指点点。一些听得不耐烦的,已经开始凑在一起窃窃私语:这又是哪家孩子没看好?这么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干什么吃的?怎么还不见拿钥匙的来开门······嗡嗡的议论声响起许久,终于有个大嗓门嚷嚷起来:“嘿,这是谁家的小孩?快点过来看看!都哭成这样了!”
过了许久,一对衣着简朴的年轻小夫妻才匆匆赶来。丈夫一脸抱歉地冲着众人点头赔不是,妻子蹲下来,隔着栅栏柔声细语哄着孩子:”不哭,不哭啊,等会叔叔阿姨就过来给你开门······”听见妈妈熟悉的声音,小男孩渐渐止住了哭声,爬起来睁着黑溜溜的大眼睛张望着四周观望的人群,脸颊上还挂着几滴没干的泪珠儿。看见孩子停止哭泣,人群也安静了下来。反而是小男孩开始好奇地打量着这么多陌生的面孔,那股憨憨的样子让人油然生出了几分怜爱,原本那些不耐烦的目光也开始柔和起来。
一个老奶奶慢慢走近栅栏,蹲下来从袋里掏出一颗芝麻糖隔着栅栏递过去:“吃吧吃吧,吃了奶奶的糖不哭不闹乖乖的。”男孩怯生生瞅了瞅妈妈的脸色,这才伸展开手心接过了芝麻糖,一把撕开塞进嘴里。边上的妈妈焦急尴尬的神色这才舒缓了下来,连忙递过水壶:“慢慢吃,别噎着。”
看着小男孩带着心满意足的微笑咀嚼着,年轻妈妈长舒一口气擦了擦脸上的汗珠。这时,老奶奶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以后可得用心看着点孩子呀,这样到处跑可危险得很!”
“嗯嗯,谢谢您······”年轻妈妈的声音里还带着些惊魂未定,“以后注意······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儿了。”
“各位旅客请注意,本次列车即将开始检票······”伴随着检票口传来的提示音,一条秩序井然的队伍开始出现在检票口前。绿灯亮起,栅栏放下,年轻夫妇跑过去紧紧抱起了小男孩,一家三口紧紧依偎的身影在人流中越走,越远,最后幻化成月台尽头的一个小黑点,消失在茫茫人海里。
绿军装下想家的心
火车站川流不息的人群中间,总能看见在安检通道和检票口熟悉的绿军装。当许许多多的人们满怀欣喜踏上归途的时候,武警战士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守护着游子们归乡途中的安宁。
开始的时候,武警战士给我留下的印象多带着沉默和冷酷:身形始终笔挺,眼睛平视前方,即使在回答问题时也基本保持了这样的姿态;面对着旅客的递烟递水,他们一概礼貌抬手谢绝;换岗累了,也顶多倚着栏杆闭目养神······无数人来来去去,唯有军装的一抹绿在行走的色彩中巍然不动。
直到那天,我看见一位武警战士帮着几个民工把他们小山般的行李扛到了检票口。民工们连声道谢,忙不迭地递上一条烟来,武警战士一贯礼貌地表示自己正在执勤,摆摆手婉拒。这时离检票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接着发生的事情让人一时竟有些惊讶:站得笔挺的武警战士和斜倚着行李风尘仆仆的返乡民工,在人头攒动的检票口队伍里小声地交谈起来。
“老哥家是哪里的?这回一趟家需要带这么多东西啊。”武警战士看着民工行李堆成的小山,悄声问。
“安徽的······哎,家里七八口老小,全靠着我打工养活。这不,过年回趟家,多带些吃的用的玩的,让他们开心过个年。”民工憨憨地笑起来,站起来拍拍裤腿上的尘土,“兄弟,那你是哪里的?大过年的回不了家也挺辛苦的。”
“武汉人。”武警战士自嘲地笑笑,“嗨,当了四年半的兵,过年不回家这事······早习惯了。”
“都是各自有各自难处啊······”民工悠悠点起一根烟,火光里,沧桑的脸庞透出些许无奈的微笑。
过了许久,检票口亮起绿灯,两人挥手作别。民工继续和兄弟们吃力地搬起行李,通过检票口走上回家的路。武警战士依然站得笔直,警惕注视着四周的动向。刚才短暂而温情的一幕,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表面上,春运无非是一项规模庞大的人口迁徙。但其中所展示的,却远不止于电视镜头前在售票口和车厢里涌动的长龙。置身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生命有情感的完整个体。诸如拖着沉重行李的老夫妇,哭闹的小男孩,背负着全家期盼的民工兄弟和坚守岗位的武警战士,他们在眼前停留的瞬间都是如此之短,留下的印象却是这般的深刻长久。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许许多多这样的故事依然在上演着。那些遍布天南海北的游子们,依然怀揣着一个最原始最朴素的梦想,奔波在漫漫旅途,奔向故乡温暖的怀抱。
以上文章为我院“新春采风万里行”活动“春催桃李”系列二等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