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普鸣的学术力作。揭示中国古代思想围绕“继承 vs 创新”“述 vs 作”的漫长论辩,以及“创新”为中国历史进程带来的文化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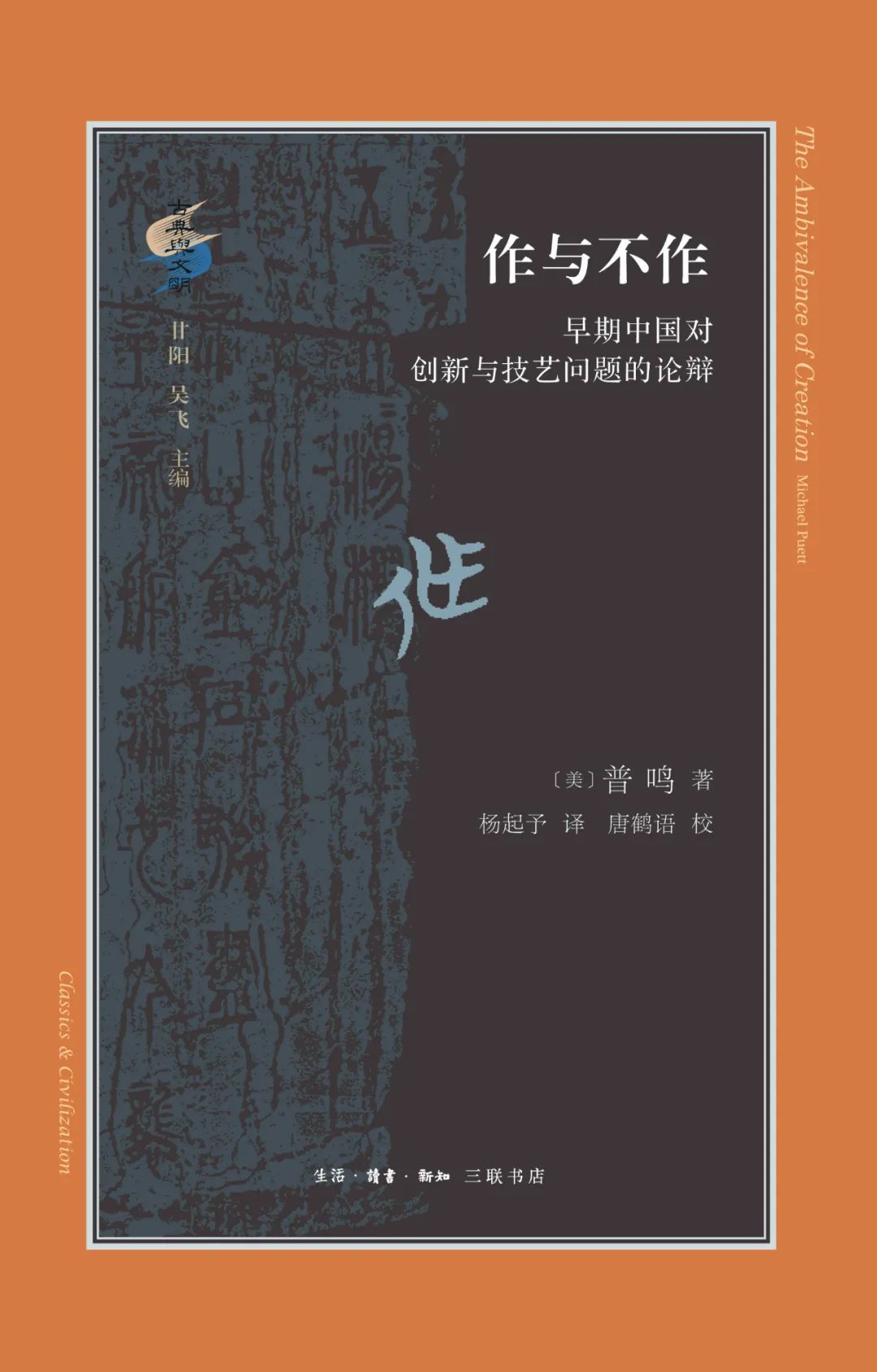
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 Debat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nd Artifice in Early China
[美] 普鸣(Michael Puett) 著
杨起予 译 唐鹤语 校
“古典与文明”
精装,360页,49元
ISBN:978-7-108-06592-6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年1月
作者,起也。“作”有兴起、创新之义,但孔子却讲“述而不作”。是“述”还是“作”,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中围绕“创作”“人为”观念展开的一场历史悠久的论辩。“述作之辩”不仅是哲学层面上自然与文化关系的呈现,其核心在于大变革时代人们对新制度——中央集权帝国——合理性的阐释,体现出“创新”为中国历史进程带来的文化张力。
此书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普鸣的代表作,由他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作者追溯并分析了商周卜辞、战国文献及秦汉政论中有关“创作”的叙述,不仅延续了西方汉学对“关联性思维”的探讨,也为考察中国古典文明提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视角。
普鸣(Michael Puett),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院教授、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尤其是早期中国的道德、礼仪与政治,兼备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与哲学等多学科视角。他为本科生开设的“中国伦理与政治课”是哈佛大学最火爆的课程之一,以此为基础出版的《哈佛中国哲学课》也在国内外大受欢迎。普鸣的学术代表作有《作与不作:早期中国对创新与技艺问题的论辩》(
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
)和《成神:早期中国的宇宙论、祭祀与自我神化》(
To Become a God
),两书中文版均将在三联书店出版。
致谢
译者例言
绪论
对中国文化的分析
研究方法
研究架构
第一章 御疆辟土:青铜时代对祖先与创作的看法
青铜时代的《诗》与卜辞、铭文
周之衰亡
结论
第二章 人之技艺:战国时期对自然与文化问题的论辩
论辩之始
修正对“自然”的定义
文化的本质:战国后期论辩的发展
结论
第三章 圣人、臣下与乱贼:叙述国家起源
早期中国神话研究的症结
叙述国家起源
结论
第四章 创作帝国:帝国统治的兴起与巩固
创作帝国:秦朝
帝制的衰落
汉代对帝国的再造与巩固
结论
第五章 创作的悲剧:司马迁对帝国兴起的重构
司马迁的规划
司马迁笔下的国家历史
引申
结论
附录 “作”字探源
参考文献
索引
从利玛窦到黑格尔:
17-19世纪欧洲对中国文化的分析
公元前221年,秦王创作(created)了中国历史上首个统一帝国。据汉代史家司马迁记载,秦王自称“始皇帝”,此后立石琅琊附近,辞云: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匡饬异俗,……功盖五帝。
碑铭称颂始皇一统中国,借法度、规纪与原则为天下创立秩 序。然而,这种创制并不仅仅是对往圣秩序的又一次贯彻:在碑铭的赞颂下,始皇以一煌煌作者之身,开辟了全新的历 史,功绩超迈五帝这类古圣先贤。
秦亡以后,在汉代人的描述中,这类主张代表了自恣、傲慢。可他们却也接受了一个既定事实:“帝国”实是一新近发明,前所未有。而倘若创作帝国之人实非大圣,这一创新如何合法?除此之外,能否另辟蹊径,赋予新制度合法性?或者,统治者是否应该拒绝帝国这一创造本身,重返往圣所作的制度中去?
汉代前期的人们对帝国制度的合法性聚讼纷纭,这些问题乃是首要问题。然而,这些聚讼脱胎于早期中国的另一场论辩,相较之下,这场论辩远为古老。早至战国时期,一些国家创立了前所未有的制度,人们便开始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以怎样的方式、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合法地创制新的制度?然而,讨论很快超越了此类变法是否合法的层面,关于创造、创新的深层问题迅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圣人可否创新?在怎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创新?人类文化(culture)源自何处?它乃是为圣人所作吗?若确为圣人所作,文化乃是一种人工造作,还是在某种意义上基于自然之文理?且有无可能会有新的圣人出世,创作出更好的文化?
本书英文版
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
,2001
本书考察了这场从战国至汉代前期的论辩,梳理其来龙去脉。论辩诸家立场不一,本研究则剖析不同立场之历史影响。笔者的讨论细究了以下几点:诸家就创新问题的论辩如何展开?叙述国家最初的兴起之时,他们笔下的叙事何以相互矛盾?在最初帝国的形成过程中,这些观点、叙事又是以怎样的方式,为意识形态目的所操纵?
笔者希望,本研究能够提出中国历史成型时期的一些新问题。最起码应该深化我们对早期中国哲学和宇宙观的认识,使我们以更复杂的眼光看待这一时期的叙事,厘清早期中国帝国文化的诸多面向。
不仅如此,本书理应被视为一次尝试,去凸显早期中国文明中的另一些议题,如当时人们对人工(artifice)、创作、创新问题的看法。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当今学界不时将早期中国描述为一个预设自然和文化相连续(continuity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的文明,这一文明否认文化出于人为,认为圣人从不创作,仅仅效法自然世界。然而,本研究的结论之一是,这一预设兴起于早期中国的特定时段,绝非不言自明。直到漫长论辩的末期,人们才普遍承认,人类文化仅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至圣从不创制,而仅仅效法自然世界中的文理。本书并不把这类观念视为早期中国的普遍预设,而意在追问促使这类观念成型的论辩本身,解释何以“连续说”在汉代前期终成主流。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会从相关二手文献入手,展开研究综述。或有意或无意,相当一批提倡此类“连续说”的文献皆奠基在对中西之别的理解之上:中国强调自然与文化的连续性,西方则强调二者之间的断裂性。追溯学术史,笔者试图解释这一分析框架何以长期存在,流衍至今。
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学术史,可上溯至17世纪的欧洲。原因不难寻觅:正是在17世纪,早期中国文献的最初译本被引介至欧洲学界,似乎使许多欧洲思想家为之一震。彼时学者试图重新阐释古希腊和基督教中人与自然分离的观点,借以发展一种文化演进(或退化)的观念。而他们惊讶地发现,大量正统中国文献宣称,文化仅是自然过程的一部分。这一发现使得大批学者把中国放入与古希腊和基督教观点对立的框架中研究。
自17世纪晚期起,一些学者开始迷恋中国文明。在他们的想象中,中国人对自然、创作、人工的看法尤为令人神往。这种想象始自早期耶稣会传教士。他们着力于阅读中国经典,以确定中国传统在基督教教义中的位置。
当时,官方持“退化”(degeneration)立场:自流散始,所有的社会皆遗失了对上帝和上帝律法的理解,因此人们需要皈依《圣经》给予的启示。因而,传教士亟须确认中国文化是否保留了人们在流散前已然知晓的真理。虽然在18世纪,教皇的一系列诏书全盘否定了中国礼仪,这种否定在1742年本笃十四世《自从上主圣意》(
Ex quo singulari
)臻于极致,但起码在16 世纪晚期至18 世纪早期,耶稣会士多半坚信,中国传统中实包含了对上帝律法的理解。下一步任务在于:如何解释这种理解的存在?异说频出,有人主张这种认识源自过往残存,有人以为流散之后,上帝又对中国有所启示。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的观点是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观点之一,他认为,中国人的这些认识源于自然理性。正如古希腊人运用理性,重新学会了人类流散后遗忘的部分真理,中国人同样运用理性充分认识了自然法:“同我们的国家一样,从一开始的古代,他们(中国人)就忠实地遵循一种自然法……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本,会发现很少有异于理性之光的表述,他们合乎理性,其自然哲学不比任何人差。”虽然中国人明显缺乏启示宗教教育,他们依然发展了先进的自然哲学。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与之相反,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相信,所有古文明都有一位原初的制法者。虽则此制法者在不同文明中称谓不一(中国的伏羲,古埃及和古希腊的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希伯来的以诺,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人,而此人所传正是上帝的律法。因此,所有的古文明都从造物主那里得到了启示。
但最终,利玛窦的观点影响更广。其间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的著作起了关键作用。学者多据其与白晋就《易经》卦象的长时间通信,认为莱布尼茨与白晋的观点相合。实际上,他的想法更接近时代远较白晋为早的利玛窦。与白晋不同,莱布尼茨将中国文明的产生归因于自然理性,这点很接近利玛窦。然而,此处他比利玛窦走得远得多,以为中国人借重返自然已经克服了堕落(the Fall),也解决了堕落之后与自然的分离问题。诚然,在莱布尼茨看来,正是这种与自然的深厚关系使得中国思想瑕瑜互见:
在知识的深奥程度和理论学科方面,我们更胜一筹。我们不仅在逻辑、形而上学以及无形之物的知识方面更为擅长——这些知识完全可以说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下,而且相较于中国人,我们更易理解那些用心灵从物质材料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比如数学。若将中国之天文学与我们相较,以上观点确然成立……因此,如果说在工艺上,我们与他们不相上下,在沉思科学上,我们位居前列,然而毫无疑问,他们在实践哲学上的成就足以使我们汗颜。
西方思维更具抽象能力,源于它与中国文明的不同出发点。中国人从自然中汲取知识,所以在实践哲学上著有成就;欧洲人从启示中获取知识,因此站在抽象的、概念化的根基之上探索无形世界。“中国人似乎仅以为我们只有‘一只眼睛’,我们还有‘第二只眼睛’,这就是第一哲学,而中国人对此尚未全然领会。通过这只眼睛,我们甚至可以理解无形之事物。”由此,莱布尼茨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中国人必须皈依基督教,欧洲人也要向中国人学习关于自然的知识。
在18世纪,这类观点影响甚巨。然而,为了更好地厘清这些观念在时代中的位置,概括当时更大的思潮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对此,孔多塞(Antoine-Nicolas de Condorcet)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Human Mind
)便是一把进入当时思潮的钥匙。这本书近乎是对此前的启蒙思想的一次总结。与同时代的人一样,孔多塞认为,技术文明(artificial culture)的发展使得科学进步得以可能:“(人类)对额外的奢侈品的猎奇刺激了工业发展。这种猎奇心正促使人们贪婪地撕开自然界用以遮蔽自身的面纱。”然而,这种技术确实可以促进科学进步,但也导致了道德退化。
然而,“从一种社会的原始状态,向一种享受着自由、启蒙国度的文明程度迈进,必然会历经艰难困苦。但这条道路绝不意味着人类的衰退,而是人类走向绝对完满进程中的必由之难”。在这一进程的尽头,人类终将完全回归自然,与之合一。其最高表现是创造出一种“普世语言”,这种语言“或能用符号表达真实事物本身,或能用符号表达定义明确的集合体。这些集合体由简单、通用的观念构成”。
许多研治思想史的学者指出,从许多方面上看,这种历史观重新阐释了古希腊和基督教传统下的神话与历史叙述。18 世纪的思想家强调,欧洲文明脱离了自然世界:西方文化的创始也是人类专断(arbitrariness)的开始,狄德罗所谓“人造的人”(artificial man)自此诞生。人们相信,唯有如此专断,如此脱离自然,欧洲文明所特有的进步才得以可能:唯有突破自然,才可能如孔多塞所说“撕开自然界用以遮蔽自身的面纱”。然而,突破自然可能让人进步,也可能导致退化——比如,人类已然开始的“专断之专制”(arbitrary despotism)正是退化的具体表现。为了避免退化,人们当然要回到自然法中,却也不能放弃原先突破自然所获得的知识。
在如此背景之下,我们才能开始理解人们视中国为“比较对象”(或者说,中国更常被视为欧洲的“对立面”)的原始动机:中国似乎代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对自然的态度。从许多方面看,莱布尼茨对此问题的见解在思想史上承前启后。与18世纪后期思想家相似,莱布尼茨的构想建立在各个社会对自然的态度之上。可与其后继者不同,莱布尼茨认为,不论中国西方,堕落已然发生。因此问题在于,不同文明是怎样摆脱了野蛮状态的?是通过理性研究自然,还是通过上帝启示?然而,对18世纪的一些思想家而言,恰恰因为欧洲人脱离自然,开始专断,创造出无法满足的欲望,西方才真正成为西方。相反,从没有人这样定义中国。此外,大多早期耶稣会传教士的观念早已过时,时人不再认为人们遗失了对原初知识的认识,故转而视“停滞”为中国历史的主要特征之一。他们相信,技术之引进带来了欧洲人对进步与退化的焦虑,既然中国从未突破自然,他们对此种焦虑便是闻所未闻。中国没有进步,无法专断,社会一成不变,陷入了它所顺应的自然之泥沼。
然而,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文明与自然相合的方式显得独特。中国人不仅与擅长抽象思维的西方人不同,而且与依据自然法生存的原始人也有显著差异。原来,中国已经进步到了对自然法有真正理解的程度,可不知为什么,即便如此,也并未脱离自然。此后,顺着莱布尼茨的思路,一些学者逐渐认为,与西方的成就不同,中国人缺少用技术控制自然的能力,可正因如此,他们更有道德感。
伏尔泰的作品将这类主张推向极致。从学术生涯的相对早期开始,伏尔泰已对此问题抱有兴趣。例如,其早年作品《咏自然规律》(
Poéme sur la loi naturelle
)的基础即为自然与启示宗教之别。与莱布尼茨不同,伏尔泰果断地将天平偏向自然一边。在附于该诗的一则笔记中,伏尔泰赞美孔子的教诲,将之视为自然宗教的典范。1776年,在《简明圣经》(
La Bible enfin expliquée
)中,他深化了这一观点,说:“似乎唯有中国人接受了世界的本然……中国人并不像我们拥有启示,他们放弃了创造。”根据伏尔泰的说法,中国之政府依据自然法进行统治,他们依靠父权而非专断命令。他在《风俗论》(
Essai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
,1756)中指出:
道德和法律,乃是中国人最为明晓、最精心培育与最臻于完满之处。儿女对父亲的孝敬乃是中国政治之根基所在。父权从未被削弱……文官被视为县和郡之父,而皇帝又是帝国之父。这一观念烙印于他们心中,构成了一个广大的帝国家庭。
然而,与莱布尼茨相似,伏尔泰也以为中国与自然的关系暧昧。原来,在他看来,这种关系同样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发展。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无法进步发展,并非因为缺乏启示,而是由于太过亲近自然。因此,这种亲密关系致使中国文明起步极早,此后却全然止步不前。相反,欧洲远离自然,苦于起步之慢,此后却日进千里。在《风俗论》中,伏尔泰强调:
人们或许会纳闷,既然中国人在远古时期已如此先进,何以始终停滞于此限制之上……这一族群与我们迥然不同,似乎自然赐予他们的感官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所需的一切,可正因如此,他们却无法走得更远。与此相反,我们获取知识很晚,但却迅速使自身甄于完善。
自然无法满足欧洲人的需求,却给予中国人所需的一切。最终,作为“自然宠儿”的中国人并不如西方一般为需求所驱:“中国地大物博,得天独厚,他们并无必要如我们一般,向地球尽头求索。”
总而言之,启蒙文化的特点是它对理解“机械论”的兴趣。它既导向欧洲科学的进步,也导向道德退化,致使人进入专断的专制境地;既带领人们撕开自然的面纱,也致使人类与自然法渐行渐远。理解这一点,就明白何以在此框架之中,中国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人们借由中国这一绝佳反例,既得以批评欧洲人以专断为治,又得以赞颂西方与日俱进之力。据称,中国文化始终坚守自然,也正是因此,它从未撕开自然的面纱。对18 世纪欧洲思想家而言,中国逐渐成为了绝佳的“他者”。
同样,可在19世纪的文献中得见大量类似论据。然而在这些文献里,面对停滞的中国,进步的西方常常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就本书的分析议题而言,黑格尔对中国的理解属于最为耐人寻味的理论架构之一。在其《法哲学原理》的描绘下,中国——实际上是整个“东方王国”,存在于精神自我意识成长的最初阶段(希腊、罗马、日耳曼王国分别存在于其他阶段)。与前人观点相似,黑格尔在此强调东方王国缺乏对自然的抽象,这种缺乏与宗教和文化领域的混沌有关:
东方王国的世界观产生于家长统治下的自然社会,这种世界观是实体性的,尚未从内部分化。根据这样一种世界观,政府的世俗样式就代表着神权,世俗统治者亦由高级祭司担任;宪法和法律同时即是宗教,而宗教和道德律令(更确切地说——习俗),同时也是自然法和实定法。
中国不存在自然法与实定法之别,也不存在人神之别。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在本节的补释中,黑格尔本人强调东方精神植根于自然,这种根于自然的品质处于国家历史的开端:“国家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时刻表现为一种静止的、实体性的自然心智,这一时刻是任何国家在历史上的绝对出发点。”同样的观点,在其对历史哲学的讲演中有所重复:
精神尚未取得主体性,在表面上,仍然受到自然限制。外在与内在、法律与道德意识尚未区分——它们仍然是一个未分化的整体——宗教与国家亦然。政体通常就是一个神权政体,神的国家在同等程度亦是世俗国家,反之亦然。
中国被描述为一个缺乏外在与内在之别、法律与道德之别、宗教与国家之别的国度。
继而,黑格尔认定中国植根于自然之上,缺乏人性与神圣之别。然而,他在截然不同的背景下讨论这些特点。在此,中国(或者更宽泛地说“东方”)没有被用来扮演一个进化/ 退化框架中的“他者”,而被转化为国家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黑格尔并非视中国为一个可资借鉴的、与西方相比瑕瑜互见的文明,而将其牢牢钉在国家历史的开端、欧洲演化兴起的前夕。
这些观点在黑格尔关于历史哲学演讲的“绪论”部分得到进一步深化,彼处,黑格尔讨论了作为“精神呈现的最初形式”的东方。他所强调的是东方国家的停滞,这种停滞奠基于一种“缺乏对峙与理想”的家庭宗教。“东方国家无法自我改造,所以它们会始终处于停滞状态。这就是远东的特点,中华帝国尤为典型。”黑格尔继续说道:
战斗与冲突要求自我镇静与自我理解,但这一觉醒仍然相对微弱,尚未自觉,植根于自然之中……一切替代僵死之物的创新必然会重新陷入自然之泥淖;人们不能创造进步:所有不停息的运动导向了一种停滞的历史(unhistorical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