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 虹膜翻译组
主要根据Michael Jon Stoil(特洛伊大学)的一篇文章翻译,有改动。
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是好几代中/东欧作家、哲学家热衷的主题。
二十世纪前期的伟大作家托马斯·曼、卡夫卡、迪伦马特,还有哲学家尼采关心艺术家个体在物质第一日益扩张的官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突如其来地占据统治地位,强调工人、农民和政党的社会角色意义,暂时使这种倾向沉寂下来。
不过,在1956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弗拉基米尔·库欣宣称这种变化的催化剂是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库欣还认为年轻一代彼时正经历着「意识形态疲劳化」。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控加上战后十多年的斯大林主义连篇累牍的宣传,让人们将注意力投注到非政党话题上。不管怎么说,1956年确实标志着中/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在作品中对自己个体角色的关注的猛然爆发。
但在东欧这次文化变革最终是失败的,艺术家重新回到严酷的意识形态束缚下,所有关于创造性个体的讨论都转入地下。再次公开谈论这些问题得等到60年代中期,伴随着所谓「捷克新浪潮」的一批导演的电影出现。
在国家意志主导的捷克,最早对艺术家个体通过作品发表意见的却是一位「旧浪潮」老导演:复出的伊利·唐卡。

伊利·唐卡
60年代,已经退休的唐卡重新回到创作第一线,带来的是木偶片《仲夏夜之梦》。直到1965年,他平均一年推出一部新作,包括迷人的《Obsession》和《Cybernetic Grandma》,这两部作品都被看作是对当时捷克社会的批评。

Cybernetic Grandma(1962)
1965年,唐卡执导了他最后一部影片,对艺术家在一个压抑社会中的处境作出清晰陈述。这部《手》只有两个「演员」:一个小木偶,人的一只大手。
片中小木偶代表着艺术家,他打扮老派,看上去是个乡村艺人,正全神贯注制作黏土罐,这时一只手闯入,逼迫艺人照他自己做一个英雄雕像出来,艺人断然拒绝,于是大手将店铺毁掉。当艺人修复了铺子后,大手再次出现,重复上次的要求。艺人被逼无奈,只好应承,但进度缓慢。

《手》(1965)
后来又有一只女人的手前来拜访艺人,最后艺人发现自己被囚禁,只是一个牵线木偶的现实。电影结束时,傀儡-艺术家被折磨得病死,象征权力的大手「衣冠楚楚」地又一次出现,给艺人小小的棺材上盖上体现荣誉的勋章,赞颂他「为国操劳而死」。
唐卡融会运用了数十年功底的电影、木偶戏来表达反独裁的主题,没有比这更恰当的艺术形式,结果这部深刻感人的短片令当权者恼羞成怒。在捷共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下,「布拉格之春」的到来,加上唐卡的多病之躯,使他没有遭受当局过多的迫害。但《手》之后,他停止了创作。
被称为布拉格的「电影良心」的Evald Schorm,1964年完成了第一部长片,从此开始和当权者过不去。他的《平日的勇气》主人公是信奉斯大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赫鲁晓夫打倒斯大林后还不愿改旗易帜,于是被封杀。

《平日的勇气》(1964)
Schorm当然并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他却对这些依旧追随斯大林主义的老知识分子寄予了同情,他误以为通过反传统的观点批评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会免遭党内意识形态保守派(秘密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攻击,但事实并非如此。
Schorm后来的电影同样致力于反映个体对抗社会的主题。在《House of Joy》中,他分析了两个官员要求一个生活原始的民间画家注册人寿保险的故事,那个画家倍感困扰并且对劝说无动于衷。
1969年《Pastor's End》是小镇中艺术教师与牧师冲突的喜剧。Schorm在苏联坦克源源不断开入布拉格,政治春天结束后不再活跃。

Pastor's End(1969)
《Martyrs in Love》的导演杨·南曼奇是Schorm的亲密盟友,他对个体作用的悲观看法与Schorm颇有相似之处。这鲜明地体现在南曼奇的超现实主义影片《一个都不能走》中。
此片情节怪异:一组穿着入时、循规蹈矩的人受到威胁,他们参加了由一个险恶的主人举办的户外餐会,每个人都不得离去,其中有个人逃脱了,主人派出猎狗和守卫将他追回。

《一个都不能走》(1966)
这部电影的象征意义在于,南曼奇暗示餐会代表着社会提供给个人的安全生活,但个人必须接受施加于己的权威,那个主人自然就是政府的化身,逃跑的客人意味着不愿接受赐予的安全,企图追求个性自由的人,但逃无可逃,结局仍是失败。
因《大街上的商店》为人熟知的导演扬·卡达也通过「反英雄」来挑衅般地表达自己对个体与社会冲突的理念。
1965年的这部影片讲述平凡的木匠托诺在纳粹占领捷克后便接管了一家犹太裁缝店,原裁缝店的女主人又聋又老,甚至不知纳粹坦克已开进镇上,天真的以为托诺只是她的新助理。正当两人逐渐发展出相依为命的感情时,纳粹却开始将犹太人送进集中营,托诺面临了生命中最困难的抉择。

《大街上的商店》(1965)
导演融合了喜剧和悲剧、幽默和残酷,来呈现人性和道德上的两难命题,超现实的结尾更是感人至深。这部笑中带泪、触动人心的佳作,也是捷克电影史上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作品。
卡达与同胞导演Schorm与南曼奇的区别在于,他倾向于深深的自省,因为在片中明确表达了主人公在遵从法西斯命令与作为捷克人内心拥有的基本人道主义精神之间的煎熬。卡达给电影安排的结尾是当他决定拯救老妇人时,纳粹却意外地杀死了她。
这个情节剧式的收场淡化了影片传达的政治含义,这可能是导演有意为之。我们不能说,卡达像伊利·曼佐在《严密看守的列车》中那样,将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国家比作法西斯占领下的战时捷克。然而,卡达的反英雄动机也可以看作是坚定的捷克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相同哲学困境的证据。

《严密看守的列车》(1966)
尽管南曼奇、Schorm和唐卡等人的艺术创作遭到了重重困难,特别是政治上的压力,但他们仍然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拍摄出大量有关个体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境遇的作品。
自那以后,阻力日益增加,这些作品或被禁止上映,或被禁止出口,来自西方世界的发行商却对这些电影大感兴趣。由于严格的政策限制,波兰导演瓦依达的《一切可售》与Schorm的《平日的勇气》都一时无法在美国等地公映。

《一切可售》(1969)
捷克导演大胆敢言的特点实在是很具争议的话题,他们在意识形态的严控下一度说得太多了,所以受到的政治报复非同小可。这些经验与教训对稍后的波兰、匈牙利导演都应该有很大启发,他们需时刻铭记于心。
譬如,瓦依达等导演虽然在后来的电影中也讨论了类似捷克同侪关心的话题,但都不得不更加小心地将自己对社会、政治的观点深深埋藏起来。寓言和象征的手法运用得也愈加巧妙、广泛,从而规避来自有关方面的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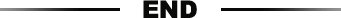
往期
精彩内容
所有玩长镜头的导演,都得叫他一声师父
他将是欧洲未来十年艺术电影的核心人物
这是日本电影历史上最生猛的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