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越南广治省在引爆美军埋下的炸弹。越战后,许多越南平民因不小心引爆炸弹受伤或死亡。摄影/Sam Sweezy
“所有战争都会打两次,第一次是在战场上,第二次是在记忆里。”在非虚构作品《不朽:越南和战争的记忆》(以下简称《不朽》)的开头,46岁的越裔美籍作家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这样写道。这本书曾入围2017全美书评人协会奖和2016美国国家图书奖。最新消息是,它的中文版将在中国推出,目前正在翻译中。
阮清越现为美国南加州大学美国与族裔研究系教授。2016年,他因反映越战和战后越南移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同情者》获普利策小说奖。4岁时,阮清越就以越南难民的身份随父母和哥哥来到美国。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难民营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时光,后来被一家美国人收养。3年后,阮清越和全家团聚,前往美国西部的圣荷西市生活。他的父母盘下了当地的一家杂货铺,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阮清越常在店里帮父母算账。他曾表示:“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写不出《同情者》和《不朽》。”
《不朽》分“伦理”“工业”“美学”三部分,分别讨论了民族中心主义、作为战争机器的艺术与商业、是什么阻碍了人们铭记战争的残酷与真实。阮清越认为,在美国,官方和电影工业只关注美国士兵的越战经历,忽略越南人的处境;在越南,与越战有关的纪念场馆不被重视,越战越来越为人所遗忘。在书中,作家试图挑战上述主流意识形态,呼吁建立一种更加公正的记忆伦理。他也提醒人们,在思考战争时,除了认识人类所共有的人性,还要认识那些不光彩的非人性——这是与对手、与自己和解的惟一方式。不这样做,战争的真相就不能被铭记,伤口也永远无法愈合。
2017年3月17日,谷雨对阮清越进行了电话采访。以下为采访内容。
普利策奖得主阮清越:越战伤口如何愈合

文/崔莹
《不朽》探讨的是记忆的二重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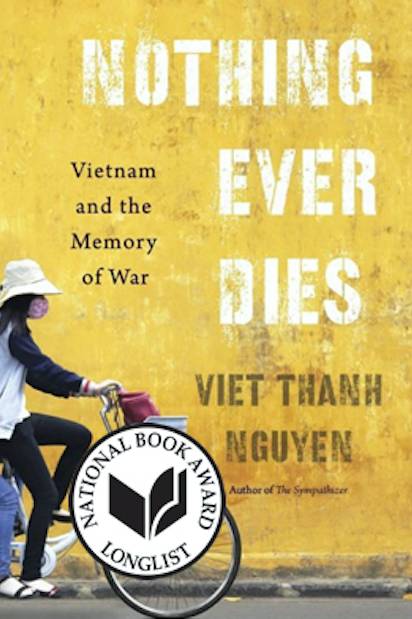
▲《不朽》
谷雨:《不朽》从酝酿到完成,用了约11年。为什么这么久?
阮清越:因为它包括的内容太多了。我在书中分析了越战对美国、越南、老挝、柬埔寨、韩国及遍布世界的东南亚难民的影响。去这些国家采访和考察都需要时间。我也研究了大量和越战有关的文学作品、电影、纪念场馆,这也需要很多时间。
谷雨:在写《不朽》的同时,你创作了《同情者》,它获得了2016普利策小说奖。《不朽》和《同情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
阮清越:2002年,我开始为写《不朽》收集资料和做准备,到2011年,资料收集的差不多了。那时我已经写了一部短篇故事集,但图书代理说纽约的出版商很少出短篇故事集,要想把它卖出去,我最好先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同意了。之后的两年里,我没有教课,全力写作《同情者》。可以说,假如没有之前为《不朽》收集的资料和有关越战、记忆和遗忘的思考,我不可能写出《同情者》。
完成《同情者》后,我开始写《不朽》。在这本书里,我借鉴写《同情者》的经验,用讲故事的方式重新叙述我在一些学术文章中的观点。
谷雨:你选择以“不朽”(Nothing ever dies.)为书名,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吗?
阮清越:是的。我很喜欢这句话,它来自托妮·莫里森的《宠儿》,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所有东西都不会凭空消失,一个人可能会被过去的人和事困扰。另一层含义比较乐观:所有的人和事都是不朽的,可以复活。我很喜欢这句话的二重性。《不朽》探讨的也正是记忆的二重性问题。
已经适应了非虚构与虚构之间的转换
谷雨:你指出:“这本书是关于战争和身份的。它源于这样的想法:所有战争都会打两次,第一次是在战场上,第二次是在记忆里。”历史也是如此,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国家叙述”中。应该如何避免接受片面化的历史?当两方、三方、多方的叙述不一致的时候,该如何甄别?
阮清越:大多数人都不怎么想知道真相,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如果想知道越战的真相,你就需要去寻找,去看相关的书,或者上网找资料。很幸运的是,这些信息都不难找到。但在美国,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好奇心和时间。而在越南,寻找真相就更难,尽管那里的人迫切希望知道它。
当人们了解了一个版本的历史,也很难再接受另一个版本的历史。因此,改变人们原有的思维方式会很难,也会很慢,可能需要历经好几代。

▲位于河内的越南军事博物馆,展出的被毁法国和美国飞机。摄影/Sam Sweezy
谷雨:那么你的作品如何试图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呢?
阮清越:最主要的是通过讲故事。这种方式非常重要。我感觉我有写作的才华,所以试图以此改变人们对越战的理解。无论美国人还是越南人,“如何看待越战中的自己”影响着他们如何讲述关于越战的故事。实际上,我是以越战为例,去挑战美国和越南的主流意识形态。
谷雨:除了作家,你也是学者。学术训练对你的小说创作有帮助吗?反过来呢?
阮清越:我的学术训练对小说创作很重要,因为我花很多时间去思考理论、文献和政治。包含了这些元素,我的作品变得复杂、深刻,充满批判性。在美国,文学作品通常不怎么涉及政治,作家对哲学、政治问题也不感兴趣,所以像《同情者》这样涉及政治的小说并不普遍,但学者身份促使我将两者结合。
小说创作也让我更深入地思考它与理论、哲学的融合,并具有更多批判性的视角,因为在美国,没多少老师在教授写作时引导大家思考这些。我还打算写一部涉及这些问题的非虚构作品,分析写作如何成为一种形式的批判,而批判如何成为一种形式的写作。我不会把它写得很学术,而是会使用我掌握的小说写作手法,以故事来驱动它,尽量充满创意。
谷雨:穿行于真实与虚构间,你遇到过困难吗?
阮清越:过去的14年里,我同时写虚构和非虚构作品。最初在两者之间转化的确很困难,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已经适应了这种转换,甚至在同一天里,我可以写一会儿虚构作品,再写一会儿非虚构作品。
即使我对美国有归属感,美国并没有完全接受我
谷雨:你在越南出生,在美国长大。你第一次意识到身份认同问题,是在什么时候?
阮清越: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我甚至在自己父母家都感到不适应和无所适从。他们对我有些期待,认为我是越南人,但我无法满足这种期待。在父母的家之外,我也不能融入美国社会。上大学后,我才明白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我是越裔美国人,是在美国生活的亚裔。我去了解亚洲人到美国的移民史,去了解越战历史,通过这些学习,我终于能说清楚自己的来龙去脉。
在美国生活了这么久,我的英语非常流利。我也适应了美国社会,对美国有种归属感。但同时我也很清楚,我不属于美国社会的任何部分。我生活的地方文化很多元,我不觉得有任何恐惧,但即使这样,我也能感觉到自己的特别,比如在开教学会议时,在一些文学聚会时,经常只有我不是白人。我依然感觉到某种排外,甚至觉得在大城市之外,在走出美国文学界之后,会有大量美国人认为我不是美国人。这让我感到,即使我对美国有归属感,美国并没有完全接受我。
谷雨:对于少数族裔作家来说,这种特殊的身份是不是一种苦涩的幸运?
阮清越:对于少数族裔,对于来自曾被殖民国家的人而言,过去的历史和文化都是苦涩的幸运。战争、殖民……我们无法改变那些塑造我们的历史,即使我们知道它们不应该发生。但也正是这些不公正的苦涩历史塑造了现在的我们。
想到越战,想到那么多伤亡,我感到的更多的是苦涩,但因越战成为难民的经历促使我成为作家,并能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审视过去和现在。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写不出《同情者》和《不朽》。因此,我感谢这段历史,也会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它。
谷雨:写一本不那么脸谱化的有关少数族裔生活的书,容易吗?
阮清越:对任何少数族裔的作家而言,写这样的作品都不容易,对欧洲的少数族裔作家也是如此,因为人们对他们的作品有种千篇一律的期待。这些占据主流的期待也弥漫于整个出版界。作为少数族裔作家,假如你写的作品不能符合这种脸谱化的期待,出版就会变得很难。
我很清楚哪些东西是脸谱化的,比如美国人对越南人的期待、美国出版商对越裔美籍作家的期待,因此我故意写了《同情者》。它和任何脸谱化的作品都不同。我联系了14家出版社,被13家拒绝。幸运的是,终于有一家认可了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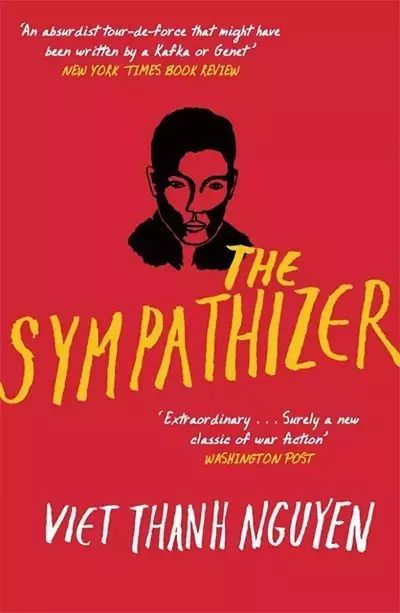
▲《同情者》
谷雨:听说你现在有意让儿子多接触越南文化,这是为什么?
阮清越:我的儿子在美国出生,毫无疑问,他首先是美国人。但我要让他知道,他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是在越南出生的,而他之所以在美国生活,是因为越战,因为我们作为难民来到了美国。他需要知道这些历史。至于他以后怎么看待这些信息,由他自己来决定好了。我希望他不仅仅在美国文化中成长,也能接触其他国家的文化和语言,并了解美国历史的复杂性。
好莱坞对越战的理解确实有些改变,但有些晚了
谷雨:你在《同情者》和《不朽》中多次分析电影《现代启示录》。你十来岁时就看过这部电影,并说它“真的伤害了你”。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对它的理解改变了吗?
阮清越:当我作为成年人重新审视《现代启示录》时,情绪化的感受少了很多。和小时候比,我能更加客观地评价它。从电影艺术的角度讲,它很有感染力,但越南人和柬埔寨人群体在其中显然是失声的。一部颇具艺术性的电影只以越南人和柬埔寨人为背景,实际上是在利用他们。我至今仍这样想。
谷雨:你也分析过其他和越战有关的电影,它们大都有美国中心主义倾向。这样的局面近些年来是否有改变?
阮清越: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美国拍了很多和越战有关的电影。大部分人将这些电影拍成了关于美国的故事,越南人在其中只是背景。
后来关于越战的电影就比较少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几部也与之前的大相径庭。以梅尔·吉布森主演的《我们是士兵》为例,在这部电影中,越南人有了自己的声音。2008年上映的《热带惊雷》则是关于越战的喜剧片。好莱坞对越战的理解确实有些改变,但有些晚了,相关电影也很少。
谷雨:你觉得一部好的战争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
阮清越:它应该令观众兴奋。我自己也喜欢这样的电影。但假如这种兴奋是建立在让敌人不出声的基础上,那就危险了。《美国狙击手》就是这样。好的战争电影要认可敌人的存在,比如《来自硫磺岛的信》就是从日本人的视角讲述二战的。此外,一部好的战争电影要让人感到对任何社会而言,战争都是有问题的。但很少有电影这样做——大部分电影只关注士兵的经历,而非战争本身。
在所有关于越战的电影中,有一部纪录片很棒,它是1968年上映的《猪年》。《猪年》很有感染力,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谷雨:你是否对比过有关一战、二战和越战的电影?它们的最大差异是什么?
阮清越:在一战和二战电影中,美国和欧洲士兵通常被塑造的相对正面。但在越战电影中,美国士兵通常被塑造的很负面。他们或者人格分裂,或者在实施暴行。
这也是关于越战电影的悖论之一:以美国人物为主人公,却展现他们所做的可怕之事。如同我在《不朽》中指出的,很多美国演员乐此不疲。他们为做明星,不在乎是否出演恶魔。

▲ 位于越南中部的美莱博物馆,在展示美军屠杀越南平民的立体塑像还原图。美军曾在美莱村杀死许多平民。摄影/Sam Sweezy
美国的越战经历影响了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书写
谷雨:电影之外,你也分析过很多与越战有关的小说,它们有些是由美国人创作的,比如罗伯特·巴特勒的作品。美国人写越战和越南作家写越战,有哪些明显的不同?
阮清越:因为美国人和越南人在越战中的不同经历,美国人关于越南的文学作品主要在写美国士兵的经历,主人公都是男性,很少有关于女性和平民的内容。
对越南人而言,越战发生在他们自己的家乡。北越的文学作品通常表现的是当地老百姓的越战经历,其中有男性,也有女性。有一些重要作品是由女作家创作的——很少有美国的女作家写越战故事,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南越的文学作品通常表现的是越战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因为实实在在的战争发生在南越。

▲越南广治省的废品交易商 。他们将引爆的炸弹从土里挖出,卖掉其中的金属。摄影/Sam Sweezy
谷雨:在众多关于越战的文学作品中,你比较认可的有哪些?
阮清越:北越的文学作品中,鲍宁的《青春的悲怆》和杨秋香的《没有名字》最具感染力。南越的文学作品主要由已经离开越南的越南难民创作,代表作是越裔美籍女作家莱莉·海斯利布的自传小说《天与地》。这本书马上要出25周年纪念版了。
还有一部重要作品,是美国退伍老兵蒂姆·奥布莱恩的《士兵的重负》。它被认为是战争文学的经典之作。而我最喜欢的是拉里·海涅曼的《肉搏战》。我十多岁时读到它,书中的美国士兵暴行细节令我心惊胆战。很多读者仍然排斥这些文字,但作为成年人再次读这本书时,我觉得这样的描述是必要的。
谷雨:在写作上,哪些作家给过你启发?
阮清越:除了托妮·莫里森和拉尔夫·埃里森,美国的非裔作家对我影响也很深,因为他们大都在作品中直面政治和历史。美国的华裔女作家汤婷婷和多米尼加裔作家朱诺·迪亚斯也对我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谷雨:就你观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和越战有关的文学创作呈现怎样的变化?
阮清越:我认为,很多美国作家已经意识到越南人的视角,并一直尝试在作品中加入这一点,尽管他们并不怎么了解战时或战后越南人的生活。这些努力对文学作品产生了影响。
美国的越战经历影响了后人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书写。你会发现,很多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退伍老兵的作品和越战退伍老兵的差异很大,因为这些新近退伍的老兵会花更多时间思考如何呈现美国人之外的人。

阮清越,作家、南加州大学美国与族裔研究系教授。他的长篇小说《同情者》被《纽约时报》评选为畅销书,并获2016普利策小说奖、戴顿文学和平奖、爱伦·坡奖和安德鲁·卡内基文学奖等。他的非虚构作品《不朽:越南和战争的记忆》入围2016美国国家图书奖、2017全美书评人协会奖。他的新作是短篇小说集《难民》。

投稿给“谷雨故事”,请发送文章至 [email protected]
点击以下「关键词」,查看往期内容:
仿真枪 | 分享会 | 和唱 | 米兰往事 | 罗布泊
遗物 | 对看 | 陆元敏 | 远征军 | 小卖店 | 南瓜花
九国监狱 | 红卫兵 | 关军 | 冲天 | 老北京 | 矿工
挖冬笋 | 海上火焰 | 赵涵漠 | 空巢老人 | 赶海人
父母爱情 | 野味 | 同志母亲 | 工人大学 | 祭祖 | 剪辑
潘庄 | 换肝 | 跨性别者 | 江阴弃女 | 太平洋大劫杀
工人大学 | 细菌战 | 王久良 | 南香红 | 韩磊 | 莫毅
同志 | 泰国妻子 | 越南新娘 | 人民广场 | 草根网红
高三 | 冷血 | 抑郁症 | 古村 | 厂区生活 | 后海八爷
三峡 | 缅甸 | 白银 | 丰都 | 唐山 | 汶川 | 黄土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