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诺贝尔文学奖从连读书人都不一定知道的文学孤宴变成了读与不读书的人一起的狂欢。稍微了解一点石黑一雄的人或许都是通过村上春树的一句“近半世纪的书,我最喜欢的是《别让我走》(石黑一雄的代表作,获英国布克奖提名,2010年翻拍成电影)。”但文学终究是文学,只有回归文字本身才彰显其意义。
对于写作者而言,我们应该从每一位伟大的作家身上,寻找关于创作的一切可能,并最终发现自己的母题,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叙事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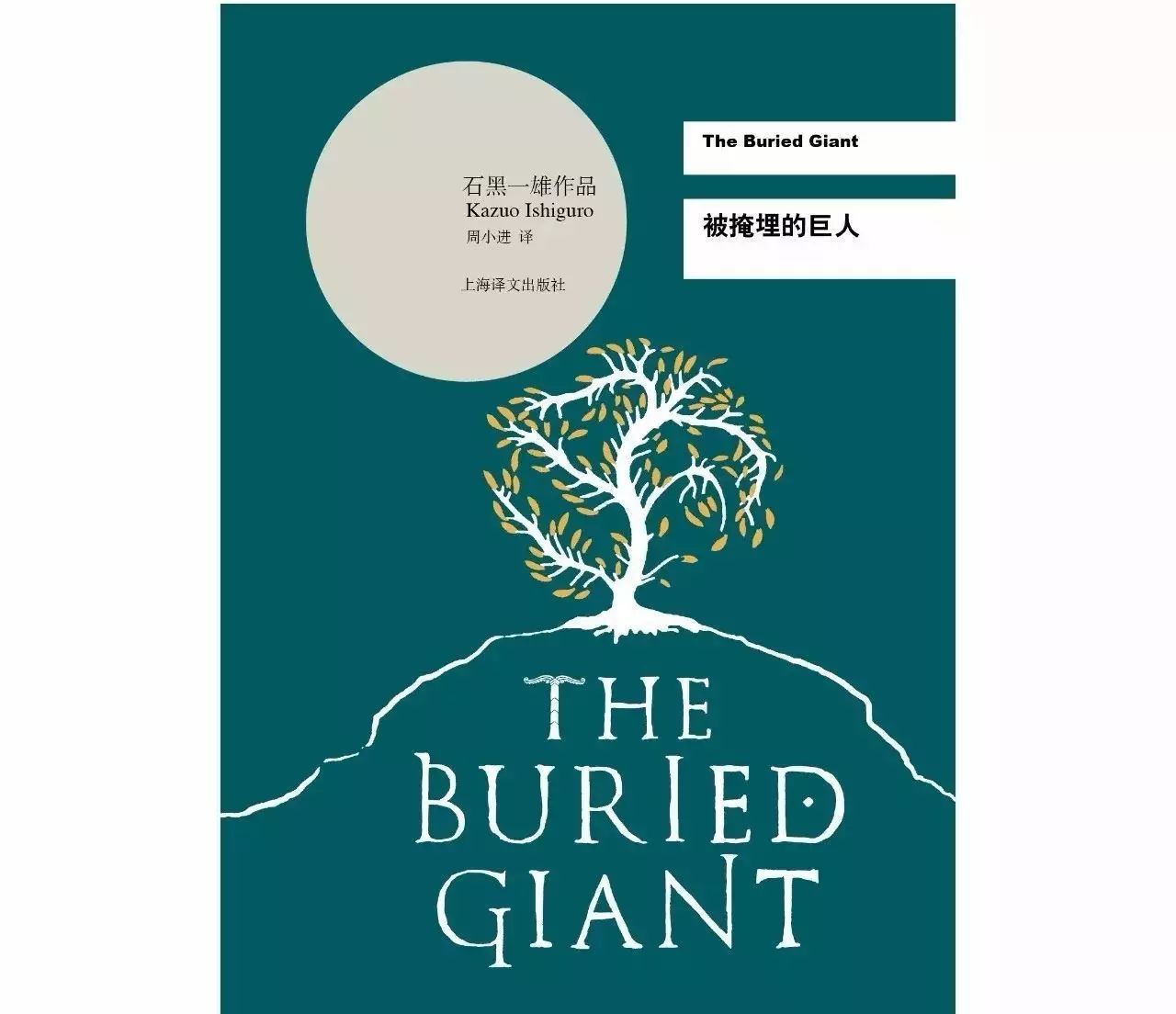
作家通往伟大的门票是他发现的母题,而石黑一雄的母题是记忆。他努力用七本小说敲打记忆的方方面面,就好比为水做一尊雕像。而到了《被掩埋的巨人》中,问号再一次执着地悬挂在空中,最后变成石黑一雄最擅长的一种氛围,一个淡影,一种无可慰藉的心情。
十多年以来,他一直想写一个探究集体记忆的故事,关于社会和文化如何通过失忆的方式,从历史的暴行中振作过来。他想到了二战后的法国、当代美国或日本,又担心“写实的历史笔法会削弱主题的效果,让它过于狭窄”(他的前三本小说便遭遇历史、文化角度的过度阐释)。
出于“去政治化”的目的,他开始寻找一个更抽象也更抽离当代的背景,这时他读到一首写于14世纪的骑士诗歌《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讲述了亚瑟时代的英国。
“我对亚瑟王、戴尖帽子的女人们之类的题材并不感兴趣,但我觉得这种荒芜诡谲、文明尚未诞生的英国可能会相当有意思。”
石黑一雄说。

石黑一雄终究还是遇到了所有作家在老年遇到的问题:在记忆渐渐褪去,阅历压弯背脊的冬季,应该走向哪里?为了寻找答案,他翻开菲利普·罗斯的浓缩、含蓄的小说《复仇女神》(Nemesis)和科马克·麦卡锡的反乌托邦小说《路》(The Road);同时也听鲍伯·迪伦的晚期作品,那种温暖、丰茂的风格是另一条蹊径。
他的妻子说,“你最后会选哪条路呢,真有意思。”
“常见的一条路是衰退。”他回答。
然而或许他不会衰退,而只是一直沿着一条水平线滑行。
他渴望抵达一种普世的广域写作,让每一个人在书中读到自己,因此他在挑选故事背景时那么刻意地用力地“去历史化”“去社会化”“去私人化”,尽管他的前六部小说都是第一人称,我们对作家本人的观点还是了解地那么少。
他故事里的迷雾隔离了他和读者,也隔离了小说与当代生活的距离。
他的小说里没有福楼拜式或曹雪芹式在后世不断轮回重生的艾玛、夏尔、贾宝玉、刘姥姥,只有石黑一雄式的缄默内敛、如同英国天气一般、如同黑泽明武士电影一般的叙述者,欲说还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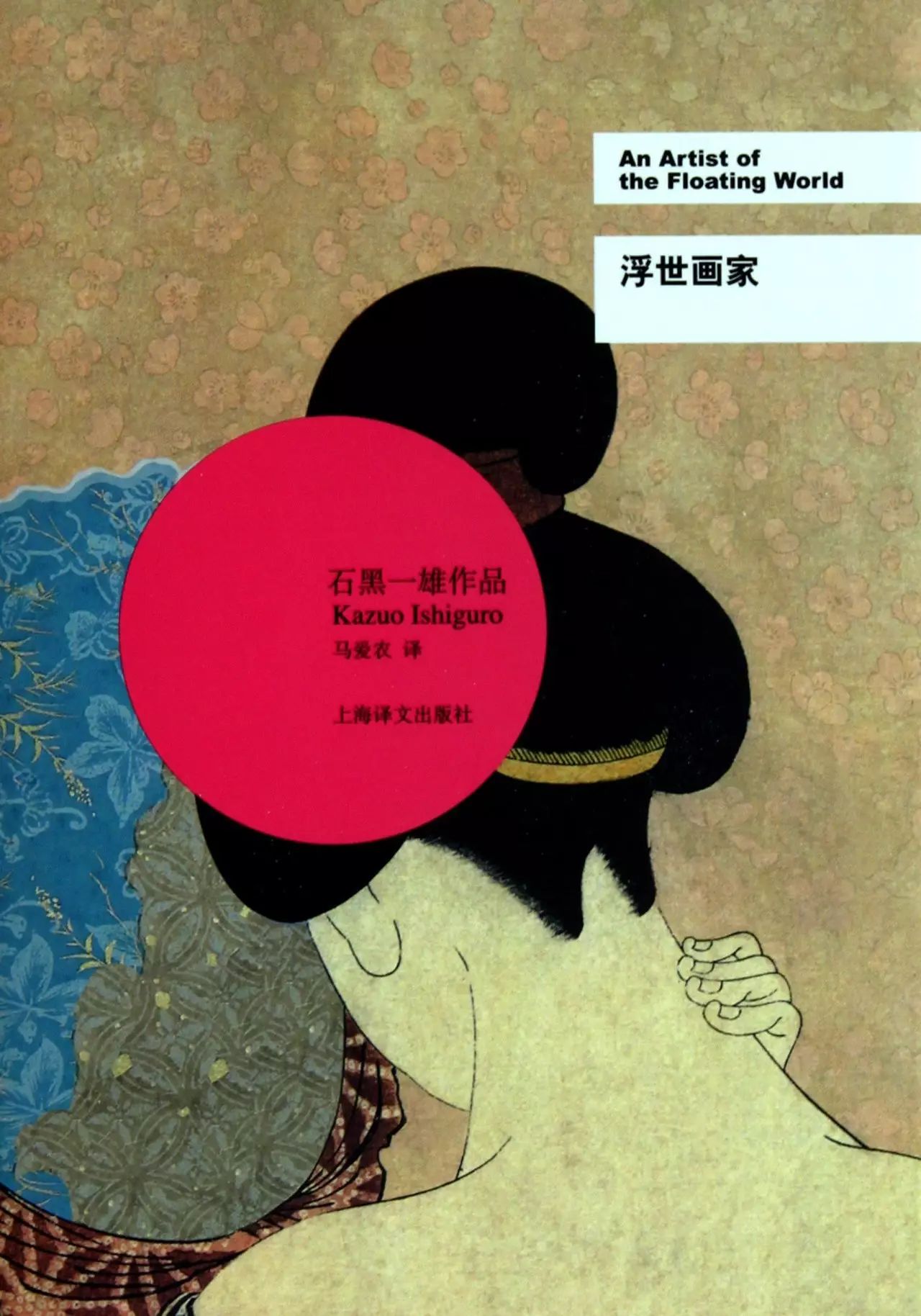
在我创作《浮世画家》时,我发现自己开始热衷于将我的电视剧本——主要是对白走向——与我已出版的小说比较,不断自问:“我的小说是否与剧本截然不同?”而糟糕的是,《远山淡影》里大段大段的内容都很像一出剧本——对白沿着一定的走向铺开,连接着更多的对话。我开始感到泄气。如果小说创作只能给我提供与写电视剧本大同小异的经历,我何必要去写小说呢?如果无法提供独一无二的东西,小说这一文学体裁,要怎样抵御电影和电视的力量?(我需要指出,在1980年代初,当代小说看起来比今天要孱弱得多。)
当时我在生病,卧床休养了几天。一旦我状态略微好转,或者不再困倦,就得找本书来看。藏在我羽绒被里的是基尔马丁和蒙克里夫翻译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或许它为我的病榻营造了一种不错的创作氛围(我从不是普鲁斯特的书迷,我觉得他的很多段落都太无聊了),但是《序幕》和《贡布雷》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两章。除了行文的极致优美,我也为普鲁斯特“运动的方法”——普鲁斯特从一个情节转移到下一个情节的方式——感到震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