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的
「BFI经典电影细读」
丛书,本套丛书已出六本,包括《教父》《美国往事》等多本还在陆续引进中。每一本书相当于一部经典电影的长篇专论,非常精彩。
早期的左翼批评家佐藤忠男的《当代日本电影》(Currents in Japanese Cinema)中,有两篇文章是关于黑泽明的:“黑泽明电影中生命的意义”(The Meaning of Life in Kurosawa’s Films)和“黑泽明的父亲们”(Kurosawa’s Fathers),其中没有一句话提到《七武士》。

《七武士》(1954)
在诺埃尔·伯奇讨论黑泽明的发展的一章中,关于《七武士》,他只是给出了一条注释,称其为“黑泽明的不重要的时代剧中最好的”。他忽视这部影片的原因和筱田十分相似,筱田谴责黑泽明只是怀着“简单的人道主义”。
伯奇在对《天国与地狱》的讨论中给出了解释:“这部影片忠于那种从一开始就统治了黑泽明作品的意识形态,影片告诉我们‘我们的周围有很多苦难,但是警察的能力是很棒的’,还有‘或许司机比资本家赚的钱少,但是在善的意志和人类的休戚与共面前,阶级分划将不复存在’。”

《七武士》(1954)
因为黑泽明在这部影片中没有表现被压迫者的反抗,所以就被认为是“简单的”,无论《七武士》在描述阶级社会的不公正时是多么独特,伯奇还是因此贬低它。
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er)对黑泽明也怀有相似的反感,唐纳德·里奇认为黑泽明是“日本电影界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塔克不同意,他反驳道:“其他的一些电影制作者更明显地关注日本社会中那些脱离了封建关系约束的个体。”在这里,他想说的导演是市川昆和小林正树。

《七武士》(1954)
在日本,一种伪马克思主义观点由一个相同的前提——扭曲黑泽明的看法——进入电影界。
1972年,我在京都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会上,批评家们和导演大岛渚(他也参加了会议)普遍不喜欢黑泽明。(我曾经在一次以外国人如何看待日本文化为主题的征文中获奖,然后作为唯一一个美国获奖者,受《每日新闻》报社的邀请访问过日本。)批评家多田道太郎指出,因为《七武士》中的一切都是被放在某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来进行观察的,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影片中没有心理冲突”。

《七武士》(1954)
大岛渚赞同他的观点,认为集体斗争没有深化到个人斗争的层面。他更严厉地批评了《七武士》及黑泽明其他作品中存在的一种模式,他称之为“超人斗争”——领袖杰出的智慧和能力使其他人物相形之下全都显得逊色,这种模式在那会儿已不时兴。
在此,令人惊讶的是批评家们故意否定黑泽明对发生在武士和农民身上的转变的处理。“在我的作品中,”筱田告诉我,“我试图通过过去和历史来表现当下,并且相信一个事实——所有的日本文化都源自帝国主义和皇室系统。”大岛渚同意他的说法。看来,黑泽明的精英主义似乎是倒退的,并且冒犯了很多人。

《七武士》(1954)
多田认为,因为社会动荡,武士们被迫“放弃一些他们的传统”,这对他们而言是件好事。《七武士》中,他欣赏的是“武士们作为人而自由地去抵制传统”,虽然这和影片没有什么关系。
他给出的例子是勘兵卫为了救孩子而假扮和尚,因此剃掉了顶髻。他没想过,黑泽明通过这六位武士所表达的并不是对武士传统的拒斥,而恰恰是这种传统的理想表现形式。

《七武士》(1954)
在对黑泽明的种种批判中,最愤怒的是多田和佐藤忠男的谴责,他们斥责黑泽明面对农民“傲慢”的态度。他们认为黑泽明将农民描绘成脆弱愚蠢的人,这是不可原谅的。农民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他们只能求助于一个等级更高的阶级,在此,黑泽明抛弃了一个信念——被压迫者有能力打倒压迫他们的人。
佐藤认为黑泽明的巅峰之作是《活人的记录》,这部紧随《七武士》之后的作品讲述的是一个老人总是担心又一颗原子弹将被投向日本,他饱受困扰,坚持举家迁往巴西。

《活人的记录》(1956)
佐藤也欣赏《生之欲》《用心棒》和《天国与地狱》,因为这几部影片“挑战了西方文化”,虽然黑泽明对《天国与地狱》中警探户仓的赞美显示了他的浅薄,虽然它们的主题——在不公正和混乱的社会中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努力”——并不足取。

《天国与地狱》(1962)
对佐藤而言,《七武士》根本不值一提,它只是证明了黑泽明的错误见解——“只有少数人是伟大的”。“这是错的,”筱田说道,“在中心人物和其他人之间有一道太深的鸿沟。最糟的是,农民太愚蠢了。”
我将这些批评转告给黑泽明,他为自己辩解道:“我想说,一切过去之后,农民才是更强大的,他们牢牢地扎根在土地上,武士才是脆弱的,因为时间之风吹拂着他们。”然而,黑泽明也是稍稍有些虚伪的。
农民强大不是因为他们可敬、美丽,或是具有令人羡慕的品质,而是因为他们野兽般的能量、坚定的决心和顽强的坚持。他们强大也是因为他们是有用的,因为他们为社会提供食物。

《七武士》(1954)
虽然很隐晦,但黑泽明还是暗示我们,纵然武士是高尚的,但他们也带着战争和杀伐的气息,这最终对社会没有好处。
他对武士的同情和对农民的同情显然是不平等的,为了捍卫这种明显的不平等,他曾经评论说,在很多作品中,他已经显示出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甚至对《天国与地狱》中的绑匪竹内,他都表现出同情,“我很自然地就对被压迫者产生同情”。他如此说,这也揭示了为什么他会选择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Trout Quintet)作为附竹内这个角色的音乐母题。

《天国与地狱》(1962)
佐藤的文章中还有一些地方提及《七武士》,但只是批评黑泽明以及由这部影片推出的结论——赞扬军事力量。
佐藤写道,如果对《七武士》做一个挑起争论的引申,那么它“论证了日本重整军备的合法性;1954年,保安队(National Safety Force)和海上保安厅(Maritime Safety Board)重组为自卫队,明显违反了1947年宪法的第九条”。他的观点和一个有相同倾向的美国人的看法一样,都并不奇怪。

《七武士》(1954)
弗里德里克·卡普兰(Frederick Kaplan)在《影者》(Cinéaste)杂志上写道,《七武士》中的火枪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象征。卡普兰想当然地认为,农民和武士的共同努力是“革命的团结”的例子。平八死后,菊千代将他的战旗插在屋顶上,就在山贼出现在地平线上之前的那个静止的瞬间,卡普兰发现了“舞台场景造型”,“令人想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他得出结论,《七武士》提醒我们,如果武士(战斗的人)与农民(劳动的人)之间的联盟不能前进和发展,他们所取得的成果终将化为乌有。

《七武士》(1954)
然而武士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因为他们是武士,所以他们和农民之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联盟。历史和日本社会的结构使武士与农民之间的联盟不可能存在,黑泽明在《七武士》中讲的故事——落魄的武士有时会像护卫或保镖那样为了混碗饭吃而为农民工作——仿佛是以历史的细节为基础。
但其实,在日本历史上,这样的事是非同寻常的;如果农民和武士为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理想而奋斗,那么,这只是预示着武士的衰落,而绝非一条希望之路。
卡普兰也承认,《七武士》的结局是开放的:“胜四郎是否和志乃一起留在村子里,武士和农民之间的联盟是否继续下去,我们不知道。”其实,关于这一点,卡普兰只需看看电影就会明白;志乃和胜四郎擦肩而过,虽然她转身回眸,但最终还是加入到播种的村民中;他目送她远去,但是却并没有真的追上去。

《七武士》(1954)
一位年轻许多的批评家吉本隆明采用了大岛渚对黑泽明的评价。黑泽明选择了时代剧,因为在日本,时代剧是一种耳熟能详的类型片,这使得他在“建构一个作为民族国家的日本以及当代日本自产的帝国主义”时,能够让观众成为“同谋”,尽管他本人的政治观点是反军国主义的。
在贬低黑泽明的过程中,这些批评家同时也忽视了反讽。《七武士》的伟大之处,一部分就在于它重点表现的反讽悖论。影片中,六位武士的无私和善良遇上了这个阶级走向衰亡的历程,这个阶级良莠并存,其中邪恶势力的代表就是四十名山贼。三位武士暂时的幸存与历史性的失败带来的痛苦相遇。

《七武士》(1954)
导演的悲伤就在于一个悖论:珍贵的事物必将和邪恶的事物一起逝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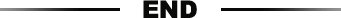
往期
精彩内容
这个人在印度,就等于成龙+刘德华+梁朝伟+周星驰啊!
祁同伟是《人民》成功的最关键,三十年往事从头说
黑泽明喜爱的二十部日本电影
《彭浩翔电影剧本集》
套装十册,一座电影档案馆,
尽窥电影鬼才的创作秘密。





